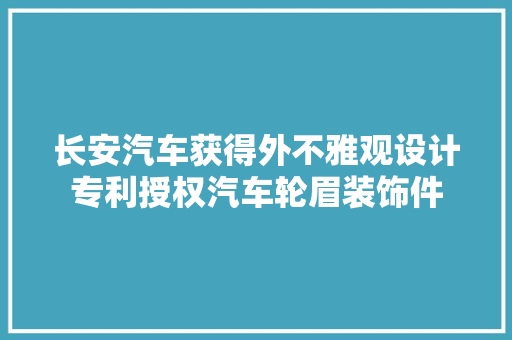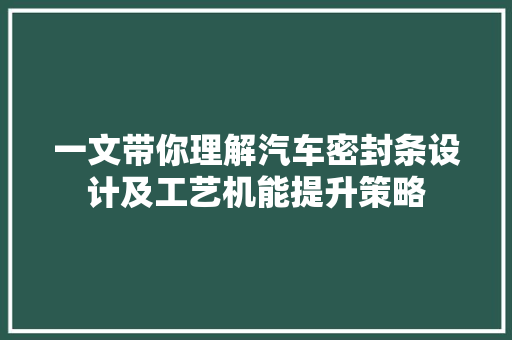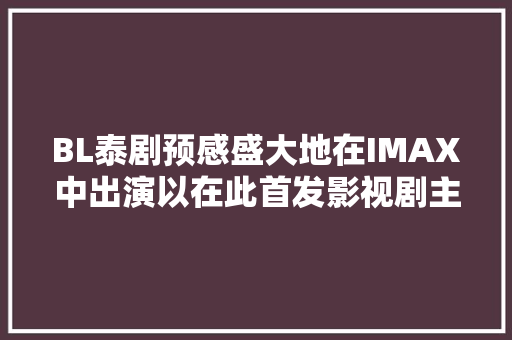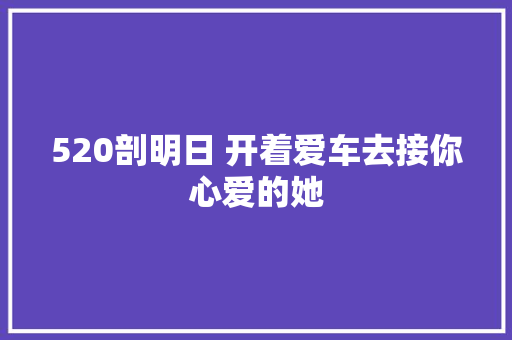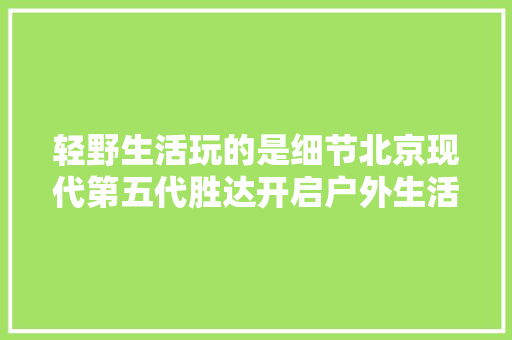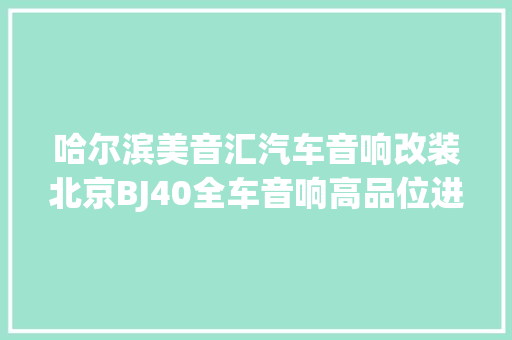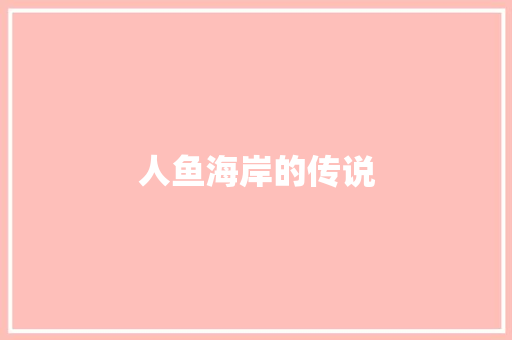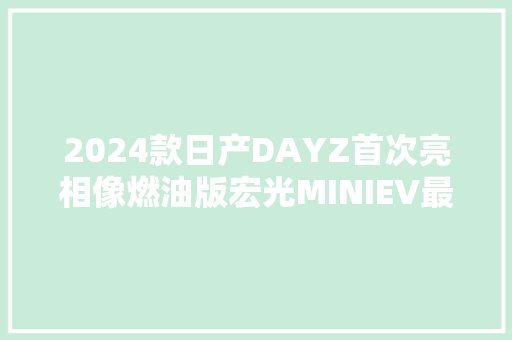这位双奥场馆的设计师,从2003年到2021年,主持设计了两届北京奥运会的7个竞赛场馆,个中包括著名的国家拍浮中央“水立方”、国家拍浮中央冰壶赛场“冰立方”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赛时的33天,这些场馆成为运动员创造奇迹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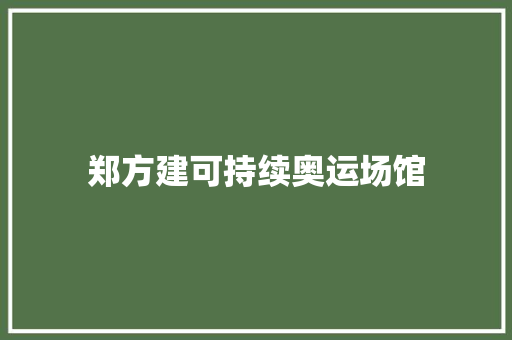
2008年8月,拍浮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天下记录。2022年2月,12个设立天下记录或奥运会记录的速率滑冰项目中,10个项目冲破了奥运会记录,1个项目冲破天下记录。
由此,“水立方”被称作“天下上最快的拍浮池”,“冰丝带”被誉为“最快的冰”。
除了为天下最顶尖运动员打造最利于竞赛的环境,每天数万人往来的奥运场馆,还要知足不雅观众、媒体、志愿者等各种职员的利用需求,同时考虑场馆好看、可实现、高效率的凑集,“光好看没有用,但不好看说什么都没用。”
单从“繁芜几何建构”、“大跨度空间构造”、“建筑立面效果”、“室内空间和材料”、“奥运功能运行”、“大空间室底细况与掌握”这一个个术语,就能窥见设计的繁芜性。用郑方的话说,“奥运场馆是职业生涯中主持设计的最繁芜的项目,没有之一。”
郑方碰着过的困难不胜列举,但他说,“我更乐意称为是在科技上面的寻衅,在应对寻衅的时候,用科学的办法去占领。”
郑方,双奥场馆设计师,从2003年到2021年,主持设计了两届北京奥运会的7个竞赛场馆。受访者供图
小城青年走出清华“综体”
郑方的职业生涯,是一部新中国建筑发展的个人史。
1970年,郑方出生于山东省宁阳县,县城里的建筑与其他北方小城没有什么不同:城市规模小,只有几条街道,建筑密度不大,多是平房。一个偶尔有演出的戏院,算是地标。他就读的宁阳一中,两层高的实验楼,在一众平房中鹤立鸡群。
学校有个特殊小的图书室,书很少,桌子也没几张。郑方对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印象深刻,小说中关于巴黎圣母院建筑的描写,让他得以看到与自己生活的地方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天下。
“正面那三道尖顶拱门,那镂刻着二十八座列王雕像神龛的锯齿状束带层,那正中巨大的花瓣格子窗户,两侧有两扇犹如助祭和副助祭站在祭师两旁的侧窗,那用奇丽小圆柱支撑着厚重平台的又高又削的梅花拱廊……”
郑方说,“只能想象出一种画面感,这是远在巴黎的建筑。”
1988年,郑方高中毕业。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请哈尔滨工业大学念土木出身的同事充当“智囊”。彼时,改革开放已有十年,这位父辈的一番话,锚定了郑方的职业航向,“中国在接下来的年代里,会有一个非常繁荣的培植期间。”
这一年,郑方以山东省高考理科第一名的成绩来到上海,在同济大学读建筑学。
三十多年后的本日,郑方鬓角冒出几根白发,自我打趣已成了“中老年建筑师”。
今年10月末,与他约在北京中关村落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周围高楼林立。秋意渐浓中,他捧着咖啡暖手。戴一副眼镜,背着玄色的双肩包,说话斯文。镜片没有任何灰尘和水渍,像他设计建筑那样一丝不苟。
在2018年《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郑方写道,“1988年我到同济读建筑学专业的时候,并不真正理解建筑学是一个若何的专业,建筑师又是若何一个行当……那时候也没有各处的新城和刺目耀眼的房地产楼盘,建筑设计的实验还远没有当今的花样繁多。”
当年,郑方对建筑仅有的认识,更像是教科书式的定义——“它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和地点。”后来他认识到,建筑中还包含了每一个时期的技能创造,再后来又多了饱满深邃的人文意义,“建筑包含了我们生命里特殊主要的体验和活动,承载了很多期待。”
1996年,郑方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毕业,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事情。1999年,郑方跟从庄惟敏院士参与设计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这是他第一次与大型运动场馆结缘。
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主体建筑采取两根108米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大拱,而常日的建筑,两根柱子间距只有八九米,“每隔八九米放一根柱子,和一百多米才有柱子支撑,是非常不一样的建筑。”
当时郑方硕士毕业才三年,他笑着回顾,“所有的点都是寻衅。”他和善于大跨度构造的工程师互助,开始探索体育建筑设计的真正意义。
绿色建筑的理念尚未在海内实践推广,但在谈论屋顶时,庄惟敏敏锐地提出在两个大拱之间利用玻璃天窗。自然光芒倾泻而下,减少场馆运行照明韶光,以实现低碳节能。绿色节能的理念,也在此后成为郑方设计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核心。
当时还没有打算机仿照技能赞助,在大面积利用玻璃天窗后,场馆内部时有阳光直射影响比赛和电视转播。因此在运营时,玻璃天窗加上了柔和的遮光帘幕。
这座位于清华大学北区主楼中轴线、建成于2001年4月的综合体育馆,见证了一代代清华学子入学报到、开学仪式、毕业生招聘会等大型活动,清华人亲切地称它为“综体”。
2009年郑方重回清华校园,攻读博士学位。五年后,他也在“综体”参加了博士毕业仪式,“能在自己参加设计的一个地方,经历对自己来说特殊主要的庄严时候,这种体验是忘不了的。”
在博士学位付与仪式上,每隔一下子,他就举头看一眼。阳光透过帘幕,柔和地洒进场馆。
夜幕下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受访者供图
“要适应所有人”
郑方参与设计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的经历,就像种下了一棵蒲公英。花托上长出白色的绒球,一阵风吹来,种子随风飘散。落到适宜成长的地方,种子就会萌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与郑方相识近20年,最早见到郑方是在北京金融街的一家房地产开拓企业,“那时他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不久,刚进入地产企业。我以为他一定会像他的许多师兄师弟那样,在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有所造诣。”
但2003年8月,郑方又回到设计行业,在中建(北京)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从事体育建筑设计。公司时任卖力人找到他,“现在有个大项目,估计能做成。”一听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场馆,郑方绝不犹豫地加入了项目组。
同当时海内民众一样,郑方对奥运会的认识也有限,“奥运会的场馆,这该是多繁芜的一件事儿。”履历见告他,作为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载体,参与者越多,参与者的水平越高,场馆的设计就越繁芜,“它要适应所有人,供应一个最佳的环境。”
郑方说,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更是科技创新的舞台。
水立方是我国第一次利用ETFE充气膜构造,也是天下上最大的ETFE围护构造工程之一。郑方将它称作只有0.2毫米厚、身分更繁芜、化学性子更稳定的“超级塑料布”,其可见光透光率高达94%,覆盖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这使得水立方内部充满自然的光芒,“像在室外拍浮一样”。水点状的视觉效果,让所有人犹如置身水的天下。
郑方和设计团队的同事们一起,设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研发运用了大量创新的打破性技能,最大可能保障运动员的比赛发挥。
拍浮池采取了石英砂过滤加臭氧消毒的池水循环技能,让池水清澈碧蓝,ph值始终掌握在7.2至7.6之间,这也是国际泳联和国家标准哀求的最佳生活用水ph值。
通过自动化监测和逆流式的水循环设计,不同水深、不同部位的池水温度稳定在26.5℃至26.9℃间;喷口送风等气流组织的办法,将充足的室外新鲜空气直接送到比赛泳池池面,将二氧化碳和余氯及时排走。
为了避免不雅观众在看台上的震撼扰动池水,竞赛池混凝土构造采取双层独立池体,让泳池构造与看台等建筑主体构造分开。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拍浮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天下记录,“水立方”被称为“天下上最快的拍浮池”。拍浮名将菲尔普斯在水立方夺得八枚拍浮金牌,夸奖“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奥运会”。
在郑方参与设计的5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场馆中,除了水立方和国家网球中央是永久性建筑,射箭场、曲棍球场和沙滩排球赛场都是临时场馆,在完成比赛后拆除。
郑方说,拆除的命运决定了设计的方向,在优质完成比赛任务的条件下,尽可能做到经济可靠。终极,设计团队发展了轻质的装置式构造搭建场馆,“这种办法就像我们工地上用脚手架一样。”
来到北京的国际箭联主席说,“射箭是一项专注的运动”。高水平的运动员,把稳力越集中,越随意马虎取得佳绩。设计组用不雅观众看台包围射箭园地,“让运动员感想熏染到被周围的不雅观众环抱,同外界阻隔开。”不雅观众也有了更佳的不雅观赛体验。
落成的看台高度,在工艺打算的数值根本上增高并实现标准化,郑方通过设计实现一个完全、亲密的比赛气氛,“虽然它只是脚手架构造搭建的临时举动步伐,但仍包含了展现体育魅力的巧思。”
2022年2月5日,北京冬奥会速率滑冰首场比赛在“冰丝带”举行。受访者供图
设计“最快的冰”
北京夏季奥运会闭幕七年后,2015年7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告:中国北京得到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
2016年7月26日,郑方依然记得这个日子。
北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设计竞赛开幕,曲棍球场和射箭场即将拆除,为速滑馆腾空园地。他和12家国内外设计机构的建筑师,在奥林匹克塔眺望园地。那天有雾,曲棍球场和射箭场依稀可见。
与环球顶尖的建筑师竞争,“完备没有信心”。但郑方在奥林匹克塔上想,“这两个赛场是我做的设计,现在立时要拆了,我要连续在这里做设计。”
北京冬奥会前,郑方并没有设计过冰场。
从前陪女儿到冰场滑冰,他对冰只有最初的印象:洁白、坚硬、冷、冰面上会有镜像。在设计国家速滑馆时,更多模糊的直觉冒出来:冰是透明的、纯净的,在坚硬的同时也可以优柔。
这些模糊的碎片,像胶片一样逐步显影,“就像刚出生的小朋友,你不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子。”郑方将设计视作一种探险,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设计创造的形式是开放的,可能去到任何地方。
终极,郑方将国家速滑馆的设计观点定名为“冰丝带”。
他在《设计可持续的未来:从水立方到冰丝带》一书中写道:在自然界中,冰给人的觉得透明、寒冷而且坚硬。但在特定的景象条件下,水蒸气由缝隙的毛细浸染呈现丝带一样的形态。建筑设计具有刚柔并济的力量,水成为立方,冰也可以成为丝带。冰和速率结合,呈现动感、轻盈、透明的建筑效果。
2017年4月,“冰丝带”在12个国际竞赛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
但要用玻璃实现丝带一样优柔的形态,还须要探索工艺的极限。
很多层玻璃波折,小小的偏差,都有破碎的可能。很多资深建筑师都不愿这样干,“建筑里面没有这么做的。”郑方将此看作“形式的冒险”,20多年的设计履历给了他本能的判断,“波折的玻璃工艺能够实现”。
“冰丝带”表面的玻璃幕墙,至少考试测验过五种完备不同的设计方案。就在郑方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接管了更常规的方案时,冰丝带的初始设计观点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干系各方同等认同:“曲面玻璃加上速率线条的效果多好,别改了。”
终极,集成小半径波折、钢化等工艺的3360块曲面玻璃单元,拼装而成17896平方米的幕墙,营造出22条丝带,就像速滑运动员在冰上划过的痕迹。
“冰丝带”建成后,“速滑女王”张虹前来试滑。银色的屋顶下,400米周长的冰面洁白无瑕,“这里像太空舱一样,我看着就想在这比赛,在这拿到金牌。”
在郑方看来,为天下顶尖运动员供应最好的园地,正是奥运场馆的义务。他会在关键问题上不断问自己和团队成员,“极限能做到哪?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
高海拔冰场空气稀薄,空气阻力小,有利于速滑运动员滑得更快。
郑方乃至和空调工程师谈论,“有没有可能把赛场的空气,变得像高原那样稀薄?”工程师回答他,“场馆空调的基本事情事理是保持大厅正压,如果负压就不事情了。”郑方这才作罢。
不过,一串数字仍能表示设计“最快的冰”时对极限的寻衅——冰面温度精确掌握在零下10.5℃,偏差不超过0.5℃;冰面上方1.5米处温度16.5℃;冰层厚度25毫米;混凝土冰板平整度偏差小于5毫米;园地风速小于0.2米/秒;顶棚发射率低于0.3……
2022年2月5日,北京冬奥会速率滑冰项目第一个比赛日,郑方也在现场。
400米的赛道,运动员从面前滑过,瞬间消逝。冰面像是镜子,短暂地留下一个线条,像是“冰丝带”上动感的丝带。
2022年冬奥会期间的“冰立方”赛场,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冬夏场景转换的园地进行冰壶比赛。受访者供图
从永久性到可持续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在曲棍球场和射箭场原址建筑的。
临时场馆的设计给了郑方信心,“无论多么严格的奥运会体育竞赛标准,都可以通过工业化的临时办法办理。”
在冬奥会历史上,冰壶比赛一贯都是在混凝土构造的基层上铺设冰场举办。天下冰壶联合会也在冬奥会场馆需求中提出,“方向于采取混凝土制冷地板。”因此,北京在申办冬奥会时表示,国家拍浮中央“水立方”将永久性改造成冰壶园地。
这让郑方扼腕,“一个曾经创造21项天下记录、未来菲尔普斯们的拍浮殿堂,要永久消逝了。”
2016年初,郑方和“水立方”总经理杨奇勇走在泳池边上,商榷冬奥会改造方案。他对杨奇勇说,“我用工业化妆配式构造设计了夏奥会的三个临时赛场,我们国家建筑工业化经由这些年的发展,一定有办法办理冰壶赛场的问题。”
这年4月,郑方和杨奇勇赴瑞士巴塞尔不雅观摩天下男子冰壶锦标赛。一方面是稽核冰壶比赛,其余一个目标,是向天下冰壶联合会提出保留“水立方”泳池,实现冰场和泳池冬夏场景转换的可能性。
郑方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是建造大国,我们完备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把拍浮池填上混凝土。现在离冬奥会还有5年多韶光,我们要求天下壶联支持做一个实验。如果实验成功了,对冰壶运动是一种推动。如果实验失落败了,我们立即将‘水立方’永久性改造成冰壶赛场。”
天下壶联时任技能代表特殊犹豫,“冬奥会不能涌现任何闪失落,要交付最高水平的冰场,我们很难冒险。”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此前全天下只有日本相模原银河体育馆转换冰场和泳池,且仅用于社区娱乐,无法承接高等别比赛。
天下壶联主席凯特·凯斯尼斯理解这种担心,但同时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天下壶联会派最好的制冰师为冰立方制冰。”
此后,郑方和杨奇勇带领团队,开始同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科学家研发、仿照、测试。
终极的系统像是一套坚固的拆装式钢框架构造,把拍浮池的空间添补变成平地。在框架上铺设1米见方的高精度混凝土预制板,利用模块化的制冰系统,20天就能实现泳池和冰场的转换。
2019年底,中国青少年冰壶公开赛在“冰立方”举行。比赛时得到的数据验证了这套系统,与传统的冰壶园地具有同等的稳定性和平整度,能够形成最高质量的冰壶赛场。
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在“冰立方”举办。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冬夏场景转换的园地进行冰壶比赛。
郑方曾说,“建筑要回答时期的问题”。主持两个奥运会的地标场馆设计,郑方亲自感想熏染到国家从全面发展的期间,过渡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期间。“水立方”到“冰立方”的转换,便是一个例证。
随着奥运会根本举动步伐的培植本钱越来越高,可持续性成为当代奥运会的支柱之一。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鼓励最大限度利用城市现有场馆、临时场馆和可拆卸的场馆举办奥运会。只在有明确的赛后需求,且该需求得到财务上可行的遗产操持证明的情形下,才可新建永久性场馆。
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既有场馆的改造利用成为核心策略。利用竞赛和非竞赛场馆39个,北京赛区的9个竞赛和演习场馆中,利用2008年的遗产场馆6个,郑方主持设计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唯一一个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
时期的发展决定了举办奥运会的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庄惟敏说,“这次冬奥会的设计,无论是新建场馆,还是改造既有场馆,都更自觉地着重为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做长久打算,同时我们和当前的环境和国情相结合,这是一个理念上的进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并且自觉地把场馆的可持续利用作为非常主要的事情内容,是建筑师的社会和历史任务。”
今年7月初,“冰丝带”面向公众年夜众开放,完成了由“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的转变。
郑方重访“冰丝带”,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赛场滑冰,这最让他欣慰:“来到‘冰丝带’的小朋友,有机会和那些创造天下记录的运动员在同一块地上滑冰,这个场馆达成了自己的义务。”
2003年,郑方第一次到奥林匹克公园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近20年后,奥林匹克公园不仅有名天下,更融入了周围居民的生活,不少人习气在那跑步磨炼。郑方自己也是跑步爱好者,时常途经那里,望着奥运场馆和磨炼的人群,“这让我们建筑师的事情变得特殊故意义。”
参考资料:《设计可持续的未来:从水立方到冰丝带》
新京报 杜寒三 编辑 袁国礼 校正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