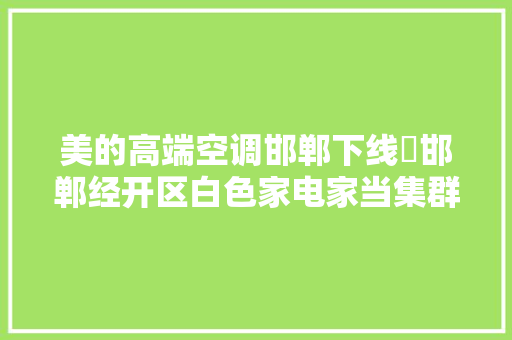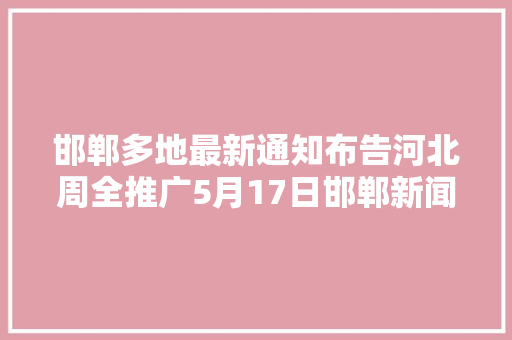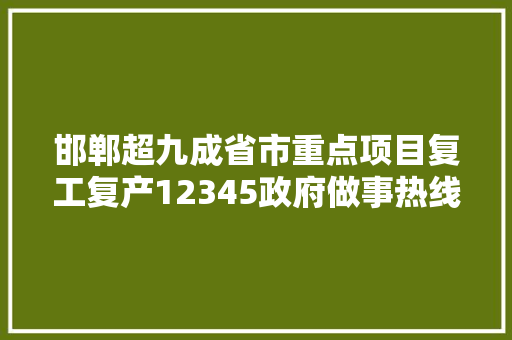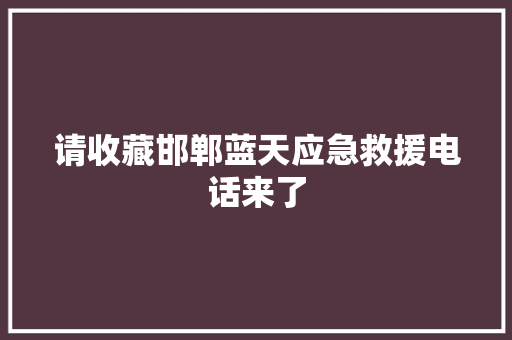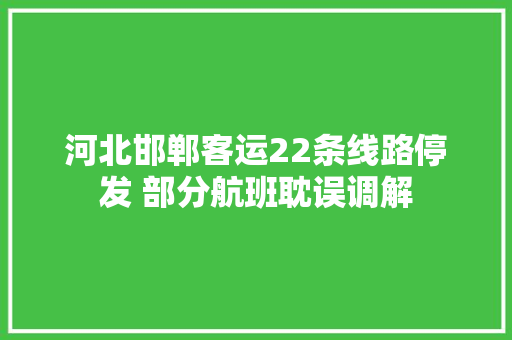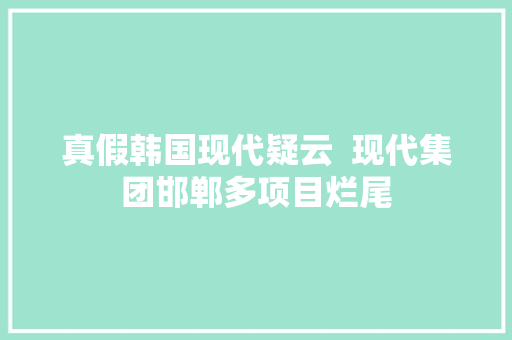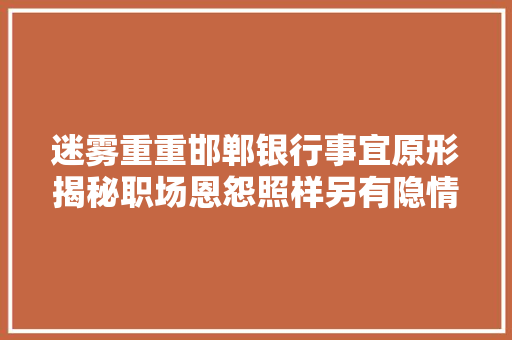学步桥因邯郸学步而众人皆知。但多年来,此桥背后的故事却不为人知。今日本刊特殊推出我市赵文化研究专家侯廷生教授的文章,对学步桥的历史逐一解读,以飨读者。
明清邯郸城,号称“三辅锁钥”“京畿保障”,城内中街贯通古城南北,行走在串城街,从南头行进到出北门(今丛台路),往北前行,沁河从西流过来,转弯东去,学步桥在此横跨沁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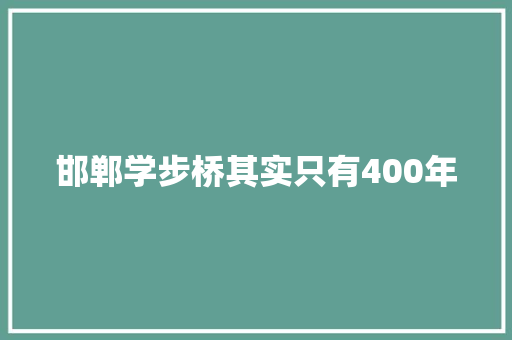
学步桥桥不甚大,却非常有名。凡是到邯郸来旅游的人,险些都会慕名到此桥上,探求“邯郸学步”的觉得。
拨乱接风,追溯桥的前世今生
学步桥处在古代邯郸县城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南北横跨沁河。沁河虽然只是一条时令河,但当年的水量也不小,每逢秋水暴涨时,浮桥每每被冲毁,官民交通往来不便。这个地方,在县的北门外,是人们的必经之地。宋金期间,这里是著名的丛台官渡,那时要到对岸,必须经由丛台渡。从实际稽核看,那时的沁河,水大河宽,这个渡口的位置,应在北门一带。而那时这一带,除了宽宽的水面,附近险些还全是泥潭水洼。邯郸县的北城墙,还在不雅观音阁口一线。金元期间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对河流的整治,这里逐渐干涸,为明代城墙的北扩创造了条件。到了明成化年间,北门里一带已经成为居民聚拢区了。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八月,知县王曰善来掌邯郸县。他首先拿出俸银倡捐,然后费时前后八个月,在沁河上建成石拱桥一座。王曰善读书长于利用,遂根据庄子《秋水》篇的寓言故事,命名此桥为“学步桥”。
有道听途说者说,在王知县建桥之前,学步桥只是座大略单纯木桥。实在这真的是途说。沁河上建石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嘉靖年间。据《嘉靖广平府志》卷三《山川志·川之附》,“北桥,在邯郸县城北门外”。这座桥,没有写明是石桥还是木桥,但可以追溯此为最早记载的桥。从它与全府二十坐桥是并列的来看,桥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主要性更不必多言。又有文献记载,在嘉靖三十八年,即有“知县杨如丝于北门外筑石桥一以是控沁水”。这该当是北门沁河上最早的石桥,比起王知县的石桥,要早六十多年。只是杨知县的石桥,大概是建筑大略,因此很快在夏秋暴水的冲击下没多久就毁了,人们只好仍搭起简便的木桥。但自那往后,沁河连续大水不断: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邯郸大水。隆庆二年(1568年),再次发生大水,沁河水侵城,城几危,以犯他道去,得免。
隆庆年间,人们提起北门外的沁河石桥,常常感慨不已,听说还有要建议建桥的,总认为“乃复欲踵其故智,何其误也”。这期间,很多人以为,只有改变沁河的上游走向,让沁河阔别邯郸城,才可以避免水患。而建桥,很困难。
也正由于如此难,五十年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知县王曰善主持建成的石拱桥“学步桥”,也就显得意义重大。而且王知县所建成的这座桥,确实坚牢无比,直到1980年代拆修以前,没有文献有修整的记载,而桥梁的利用,一贯延续近四百年。这桥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上,每每有行商游子达官国戚从此经由,乃至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也不乏汽车等当代化的交通工具从上面隆隆驶来,更有那战役期间,兵旅凶凶,铁蹄踏踏,坚兵锐甲,铁刺钢炮,骎骎八年。由此可知,王曰善堪称一位建筑设计大师。
王曰善在邯郸任上也不长,县志也没有他的传记,其他业绩也无从得知。我从清《湖北通志》卷五十三人物志里,理解了一点资料:王曰善,字天衢,湖北江陵人。少孤力学,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年)成进士。令邯郸,编里赈荒,课士有法。行取礼部,分校乡会两闱,一时称为得人。后升宝尚寺正卿。
他得中进士后即来邯郸为令,其间,他整理户口里甲,动手救灾赈荒,在教诲学生上也认负责真。后来到礼部,担当乡试和会试的考官,选取了不少的人才。末了到宝尚寺为正卿。宝尚寺属南京礼部,究竟是管什么的不清楚,反正不如大理寺、鸿胪寺之类的部门出名。他修学步桥的业绩,却在其宦涯里险些没什么痕迹。
让王知县名垂千古的是两年后张我续写下的《北关建筑石桥记》。
对付这期间的邯郸县来说,学步桥的建造毕竟算是一件大事。当时住在北门里的张家三公子张我续正在家闲居,于是应邀为这座桥写下了《北关建筑石桥记》。但由于政局的变幻无端,很长一段韶光,桥和这篇桥记并没有文献记载。直到清顺治初年,有心于县史的廪生聂应昌,才把桥的建造记入《邯郸县志续志》内,而康熙十二年的《邯郸县志》也首次在“桥梁”条下,描述了建桥的起因:学步桥,在邑北关。盖沁河经城北入滏,每夏秋之交,山水暴涨,行者苦之。前令王曰善捐俸议建石桥,有邑人省祭魏邦俊亦慕义输金,遂告成焉。世传寿陵子学步于此,桥成,因以为名。刻有石碑在。
不仅如此,康熙《邯郸县志》还附入了张我续的《北关建筑石桥记》一文。但康熙仅仅提到“刻有石碑在”,没有提及是何人所撰。直到乾隆《邯郸县志》方才明确为“明张尚书我续有记”。
乾隆《邯郸县志》:学步桥,在县北关,跨沁河上,明万历中知县王曰善建。取名“学步”者,《庄子》“寿陵余子学步于邯郸,未得其能,又失落其故步,匍匐而归”。盖用邯郸故事借题于此。明张尚书我续有记。
这期间,那座气势宏伟的学步桥,已经矗立在北关外140年了。
万历四十七年,张我续挥洒泼墨留精品
《北关建筑石桥记》是万历四十七年张我续所撰,记中不仅记述了建桥的由始、建桥的经由,而且对横贯于南北京畿大道上的浸染也洋洋洒洒作了评价:
沁水自邑西建瓴而下,由城北关东注于滏。旧葺浮桥以利攸往,及秋水暴涨,彭湃澎湃,桥久啮就窳,远迩病之。梵衲宗信募化营修,越数载弗克底绩。
丁巳秋八月,郢都王公奉简命来宰吾邑,悉其状,甫下车之三日,遂出装中金缮治。于时,省祭官魏邦俊者首输千金以应,风草之机诚捷也。爰咨廉干者,得引礼官郭应举,俾往监役,仍饬义民马相等倅之。计寻丈,揣高卑,庀材鸠工,分功程力,越戊午夏四月杀青。易木以石,撤旧为新,雁齿凌空,蹲鸱椓地,视昔盖增雄焉。邑之父老相与酌酒讴吟,谋伐石以计其事,属记于余。
余按《周礼·司险》:“周知川泽之阻,达其道路。”而郑氏注云:“达道路者,川泽之阻则桥梁之。”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仲春舆梁成,民未病涉也。”是故有惠心者然后有惠政,有远识者然后有远图。今之绾绶号循吏者亦有经理桥梁者矣,每每糜费资财,玩愒岁月,炫虚声而少实效,遂使民视上令尽属空言,其何建树之有?乃我公今日之役则有超人数等者。念环城之水涉之者众,方切云霓之望,已怀厉揭之虞:一旦雨集川盈,咫尺千里,当是时也,漫假鼋鼍之力,空瞻乌鹊之毛,谁司民牧而令至是?于是乎需之夙夜迟早而弗遑,于是乎倾诸囊箧而弗计,于是乎勿狃目前之陋而图不朽之基。阖境闻之,仁沁于心,义呈于色,象指者响赴以输金,受事者得火驰而趋役,遂令积年之患倾刻而除,永赖之功翘跂而定,往来津梁者肩摩踵接,毂击镳联。美哉!晃晃乎称奇不雅观也,讵不伟欤?
乃余之谂我公尤有进于是者。太史公曰:邯郸,漳、河间一都会。自文皇奠鼎幽燕,南北轒于斯,京藩会于斯,列辟朝宗琛贡走集于斯,彼其累累在路者,航大河,浮漳水,坦步王畿方且洒然动色,遥瞻尺五清辉,则道途通塞,桥梁修圮,实国家治忽之征,讵仅仅利病吾邑也哉?因知公之所以为砥柱、为舟楫者,胥于是役焉肇之矣。
公讳曰善,字惟果,别号祁连,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登万历丙辰榜进士。
文中提到的两个人对桥的建筑有较大贡献,除了知县王曰善,其余一个是“省祭官魏邦俊”。魏邦俊,其事不详,只知道是邯郸人,担当省祭官。一说省祭官即“省察官”,祭,古察字,省察官的职能即“纠察”“督察”,与现在的司法监察类的官员相似。明代多设在州县。本来明代初期察院是很主要的机构,紧张是为监察御史前来巡察而设立的衙门,但后来这个职能转到县州一级,改由本地的省察官实行,察院也就逐步废弃了。地方省祭官的级别较低,属于县衙里的杂职一类,与承差、知印、吏典等类似(也有人认为是孔庙的领祭官,即管理敬拜的官员),是个小官吏、差吏,地位一样平常低于举人、生员。举例来说,比如在待遇上,七品官员可以免粮10石,人丁10丁;八品免粮8石,人丁8丁;九品免粮6石,人丁6丁。到了县府里的各级职员,减免标准就大大降落了,如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2石,人丁2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则各免粮1石,人丁1丁。由此可见省祭官的地位。只管如此,这位魏邦俊师长西席,却是第一个出面相应王知县的号召,且捐资千金,从而带动了全县公民捐资着力,修起了一座从此有名天下的桥。魏师长西席也因此而青史留名。此外对桥有贡献的还有几个人,如引礼官郭应举,是当时公认的比较清耿介直之人,紧张做工程监督;义民马相,赞助做监督。当然,知县王曰善的统领浸染不可忽略,他“甫下车之三日,遂出装中金缮治”,对桥的培植起了最主要的推动浸染。
负责读张我续的《碑记》,上面并没有说桥名的“学步”字义;叫学步桥,只是取邯郸故事而借题所为,并不是说这里是当年学步地。何况“寿陵子学步之说”本来就有很多不可尽信的漏洞。康熙《邯郸县志》的编者因此特殊给予注明:“因并志之,俾无失落实焉。”古人老实,反是今人到处宣扬“寿陵余子学步于此”,既无讲求,也无情理了。为此,乾隆本《邯郸县志》特地解释:“取名‘学步’者,盖用邯郸故事借题于此,非果有其人其地也。”
据当代人的丈量,明代学步桥全长33米,面宽8.3米,通高7.8米(桥墩以上高4米)。桥为三孔拱券式石板桥,每孔跨度为6.2米,高为2.4米,拱券顶部外各雕有一只俯视河水的吞水兽。桥下设有三大孔,两侧附设四个小孔拱券,每孔跨度为1.5米,高2米;桥面两侧各有19块栏板和18根望柱,栏板长1.7米,宽0.8米,上雕人物走兽。柱头上分别雕有石狮、石猴等神兽,维妙维肖。
就在学步桥建筑后不久,天启六年(1626年),邯郸又一次大水,平地行舟,漂没田庐无算。这年的八月丙午夜,地震者再,屋宇若倾,四境皆同。到崇祯三年(1630年),邯郸再次大雨水,冰雹伤禾殆尽……而这座桥,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进入清代,康熙年间邯郸也不乏大水的记载。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夏,又是大雨水。那年沁河泛涨堤决,水从河坡直注城壕入城,丛台下水深数尺,连城街几成泽国。惊骇不安的邯郸人,只好关闭北门,把原来废弃的故北门拱极门重新打开供人们出入行走。也就在那一年,设置在丛台上的给皇上祝福的万寿宫,也被迫转移,安顿到南门里的关帝庙里。在一次次大水浸城的城市影象里,却一贯没有学步桥重修、重修的。它是那么倔强,抵御了一次次的大水,稳稳地跨在沁河上,走完了从明到清,又从清到民国的历史。直到解放后的八十年代,它仍是来往沁河两岸的紧张桥梁,纵然来回奔驶的汽车大卡,也没有让它倒下。当然,伤痕累累难免……
旧迹保护,建碑文建园建景不雅观
为了保护古迹,1987年邯郸市政府特拨款30万元对学步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修。修葺时将桥墩以上全部拆除,按原桥形状砌筑,所有青石均从河北省曲阳县定做,柱头石狮、吞水只管即便按原样雕刻,而原栏板上的人物走兽已破损不清,故由邯郸市雕塑办公室重新设计了一组赵国历史故事。重修后,整座桥构造坚固,造型都雅,基本上保持了原桥主体风格。在桥北东侧,还树立了由文保所陈光唐师长西席撰文、书法家李守诚师长西席书丹的建筑碑记。这方由283字碑文组成的《学步桥修缮记》碑,成为守护古桥的又一卫士:
学步桥横跨沁河,乃古城南北交通要冲,史称三辅锁钥。以庄子秋水篇寿陵余子之说,故名。原系木架构造,明万历四十五年改为石拱桥。桥为七孔拱券,宽九米,长三十二米,通高七米又八。两旁各十九块拦板,与栏板间十八对望柱,均有精美雕刻。奈年久风化残损,不复原貌矣。
沁河原名牛首水,西出紫山,东贯邯城,注入滏阳河。昔日河水汤汤,夹岸杨柳依依。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云:“洪遄双逝,澄映两川。”乃古城一大景不雅观也。惜乎迄于近代,源泉递减,污水漫流。公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俱兴,政府遂治沁河,先建上游拦河坝,次治河床戒备,继修桥梁古迹,开辟两岸带状公园,实为公民休憩嬉戏之佳所。复又拨款三十万元,于公元1987年一月至玄月修缮此桥,以保留原主体与风貌。当此落成之际,特立此碑为记。
邯郸市公民政府。公元1987年4月次丁卯十月,陈光唐撰,李守诚书。
1995年10月6日,邯郸市公民政府将学步桥公布为“邯郸市文物保护单位”。
沁河公园始建于1984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步桥周边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整治,2001年,学步桥广场建成,广场总面积20016平方米,个中绿化面积6385平方米。总体布局分为一个中央广场和四个景区,中央广场以学步桥为主景不雅观,沿沁河两岸,围合成椭圆形广场。在园内增加了以邯郸针言典故和历史故事为内容的雕塑、奇石,游人走进此园,感想熏染着浓郁文化的熏陶。2004年,按照“清淤,截污,蓄水,增绿,造景”的十字管理方针,对沁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管理和景不雅观改造。2006年初,根据城市培植的须要,广场两侧的道路各加宽了两米,东南角处又开辟出3000余平方米的绿地,栽种了近200株银杏作为行道树,全体广场显得更加宽阔靓丽。
景区按照桥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方位分别建有四个园。西北沁河北岸西侧是针言典故景区,设有六个纪事花坛,分别代表在邯郸境内建都的赵(战国及两汉期间)、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朝代,针言典故刻在一块高4米半,重18.2吨的巨石上。东北沁河北岸东侧为不雅观桥景区,建有望桥亭,亭下的平台延伸至水面,高低错落,有静有动。西南沁河南岸西侧为邯郸学步景区,有一座寿陵余子学步邯郸的人物雕塑,四周为带有脚印的学步石组成的学步路,游人到此,都会会心微笑:一对邯郸的年轻男女,在前面优雅行走,身后是远道而来的寿陵少年,笨拙地仿步而行。这个区域里还建有19个柱樽,分别刻有十九个县市区的历史典故和名胜古迹。东南沁河南岸东侧为典故雕塑景区,分别散置有“前倨后恭”“鹬蚌相争”“曹冲称象”等雕塑小品。
桥北新建一石坊,楣上南为“袨服新市”,北为“古城迎瑞”。坊上南北两侧各镌刻两幅楹联。
南面:
春满长街昂首过桥思学步
月明小巷同心报国鉴回车
庄周秋水非闲话
太白高歌有古风
北面:
紫山西峙名都十里留佳景
沁水东流美谈千秋有此桥
磁山肇史七千载
北苑拱桥五百年
如今的沁河下贱,在丛台区的部分,如果从环城西路算起,穿公民路涵洞,北行后打个弯斜穿丛台路至陵西大街、学步桥广场,再东蜿蜒过中华北大街、光明北大街,至沁滏汇流处,全长约4.5公里。沿河两岸已是绿意园林、河岸公园,若从陵西大街向东望去,一水穿五桥,邯郸城犹若水城一样平常俏丽。
来源:邯郸 新闻周刊 作者侯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