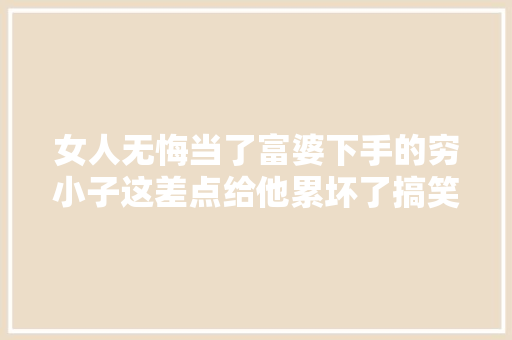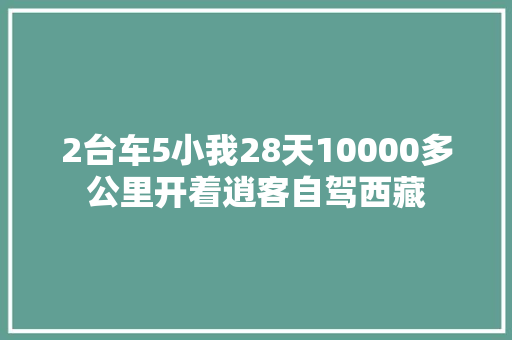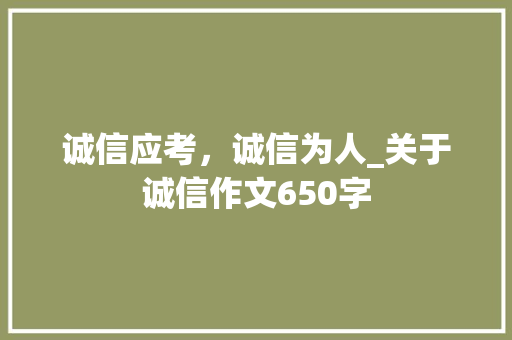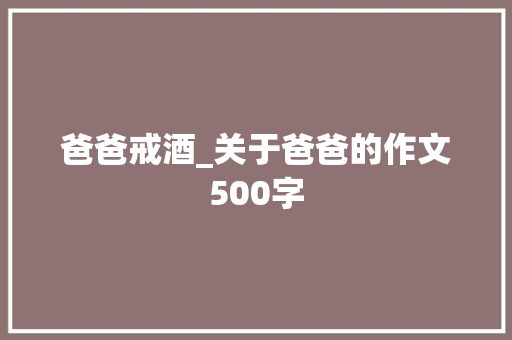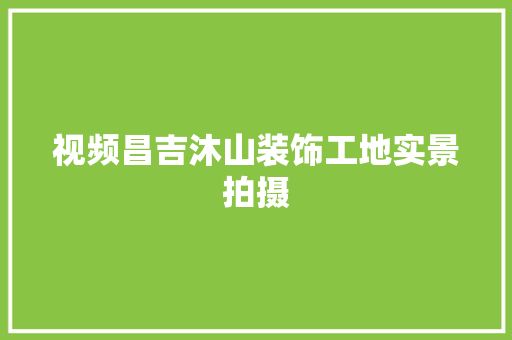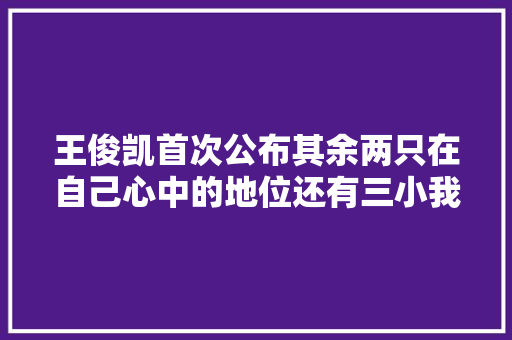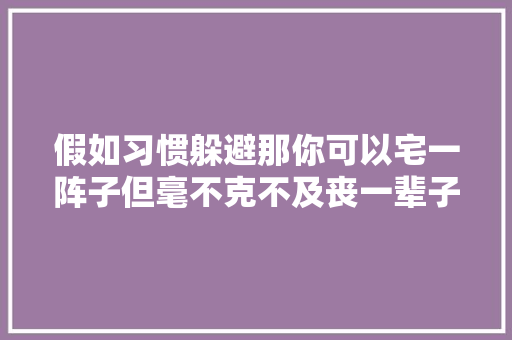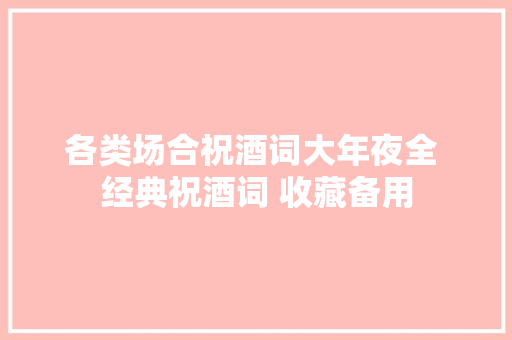打卡,原指高下班时刷卡记录考勤,后引申为为了养成某个好习气而做出承诺、并约请大家“监督”,如一度盛行的在朋友圈分享逐日背单词的打卡记录。如今打卡一词更多运用于文旅场景,表示来到了某个热门地点。打卡的标记、展示和社交功能不言而喻,“网红打卡地”也成为人们对一处风景的顶级赞誉。
城市从“打卡热”中获益良多,打卡帮助城市塑造新的风景。对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得到流量的“打卡地”稍作不雅观察,不难创造多数并非传统景点,“旅游吸引物”正从“景点”转向“风景”乃至“场景”:城市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剧院、绿道、步辇儿街、购物中央、美食……万物皆可打卡,人们会为了一碗螺蛳粉飞到柳州,也会因一间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相约看展游”“美食攻略游”“随着演出去旅行”“借着赛事来出游”成为“说走就走”的新情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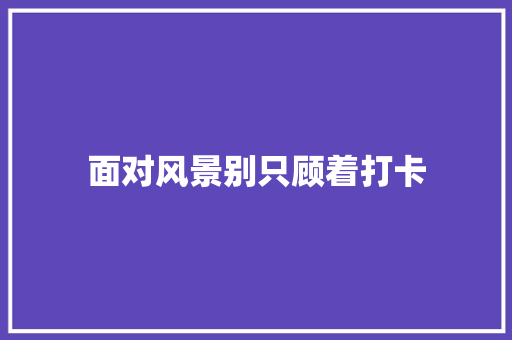
林琨 摄
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贵州村落BA……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打卡热,在媒介地理学意义上重新擦亮了“地方”,让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得到了显示度、拥有了新“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效益。一些独特的“打卡姿势”本身便是靓丽的文旅景不雅观:在大同云冈石窟“与大佛击掌”,在德阳广汉三星堆“戴金面罩”,在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排队拍一个“无语菩萨”,更不用提“国风汉服旅拍”和今春以来盛行的“簪花游”——有媒体对历史上的簪花传统进行“考古”,可见“簪花打卡”既扮靓了城市,也彰显了普通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旅游不但是看风景,更是看风景中的自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央特约研究员厉新建曾这样描述文旅家当的新变革:人们越来越关注旅游中“我在现场”的主体性表达,旅游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交货币代价和话语代价,“旅游式社交”蔚然兴起。
这与多年前的“XX到此一游”有着一脉相承的共性。立足文旅深度领悟的时期背景,伴随着“打卡热”的兴起,是旅游消费从“不雅观光型”转向“体验型”的必由之路。
拍照,修图,上传,等待点赞评论……在某些人看来,“是否出片”成为“值不值得去”的衡量标准。这样的“打卡”值得我们反思。
林琨 摄
从“被种草”到“打卡成功”,是否意味着一趟旅行完成了闭环?小红书、朋友圈里的精细旅拍,每每让人遐想到苏珊·桑塔格在《论拍照》中提出的“拍照式不雅观看”——在拍照技能开始大规模盛行之时,桑塔格表达了她的文明忧思:照片教导了我们新的视觉准则,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的不雅观念,“拍照是核实履历的一种办法,也是谢绝履历的一种办法,它把履历局限于探求适宜拍摄的工具,把履历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旅行变成累积照片的一种计策”,拍照已变成“表面上体验某些事情”的紧张手段之一。
当拍照晒朋友圈成为了仅有的目的之时,走马不雅观花的打卡,注定是一场浮光掠影的“悬浮”。随着“看展游”兴起,本该凝神静不雅观的艺术大展上,常常可以瞥见一些打扮精细、等着拍摄“网红同款”的打卡者,影响了其他人的正常欣赏。景区里,最佳的赏景台也常被“模特”、拍照师和打光板所霸占。
一方面,我们提倡地方和景点,深挖自身文旅资源、创新表达,让“网红”变“长红”,“流量”变“留量”。另一方面,立足个体视角,更有代价的“打卡”,意味着重新出发、建构我们与天下的关联。
“纵然我们去了一千个地方,如果我们只有一副眼力,那也相称于只去了一个地方”。旅行也好,寻觅身边的风景也罢,天下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召唤构造”,等待着我们探索、创造、感想熏染,并为之授予意义。借由与天下的深刻互动,我们完成了自我、天生了独一无二的“个性”——比起打卡晒图所营造的“人设”,本真的“个性”更为真实、殊异和宝贵。
“万物静不雅观皆得意,四季佳兴与人同”。在没有打卡的时期里,我们与天下的关系曾如此清新和亲近。那些惊鸿一瞥的凝眸,那些震古烁今的顿悟,教会我们看待天下的基本眼力和方法。原来,赏景不必从众,它可以是“凌晨四点醒来,创造海棠未眠”;原来,“打卡”未必是“复制”,可以是我们与天下签订的“私人左券”——古人游山玩水之际写下的诗文,何尝不是那个时期的“打卡小作文”?透过那些笔墨,但见青山妩媚,感叹人亦深情。
新华日报·交汇点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