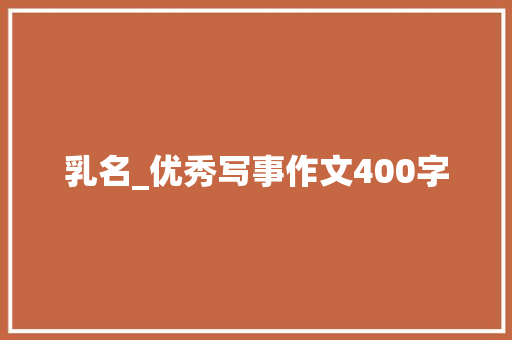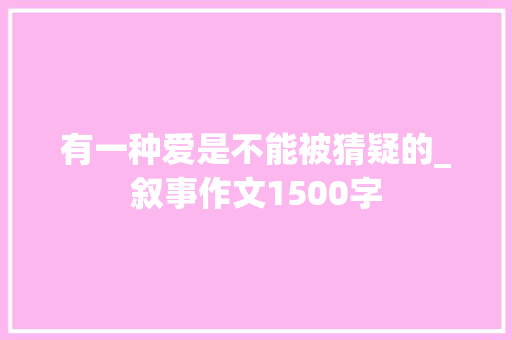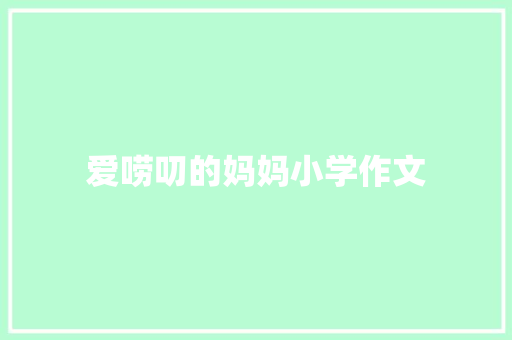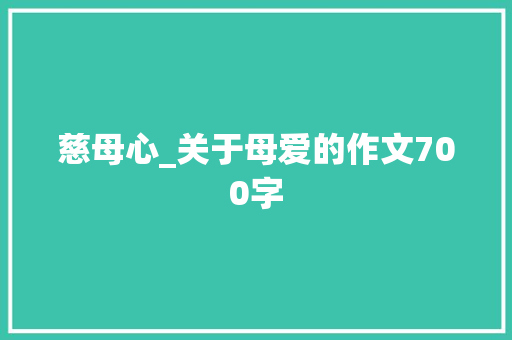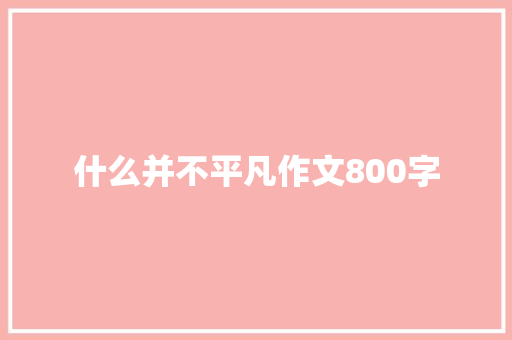漆黑的夜,天空连一颗星星都没有。荒凉的大山深处,没有虫鸣,没有野兽的叫声,没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巨大的阴郁里有一种凝固般的安静。这种安静带着巨大的不安,让人感到窒息。
少焉之后,一声凄厉的号哭撕裂夜空,静止的空气犹如

镜片,应声碎裂,随后起风了,冷风把更大的哭声传了出来,
哭声中夹杂着一个名字--“妞花”!随着哭喊声越来越大,
一簇簇火光亮起,那是一群人举着火把狂奔而来,他们大声
喊着“妞花”,声音迫切到沙哑。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刚才那贯穿黑夜的凄厉哭声便是她发出的。在火把的映衬下,她头发缭乱,脸庞模糊。我看不清她的样子,但听着她啼血般地哭喊着“妞花”这个名字,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漆黑的夜,天空连一颗星星都没有。荒凉的大山深处,没有虫鸣,没有野兽的叫声,没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巨大的阴郁里有一种凝固般的安静。这种安静带着巨大的不安,让人感到窒息。
少焉之后,一声凄厉的号哭撕裂夜空,静止的空气犹如
镜片,应声碎裂,随后起风了,冷风把更大的哭声传了出来,
哭声中夹杂着一个名字-“妞花”!随着哭喊声越来越大,
一簇簇火光亮起,那是一群人举着火把狂奔而来,他们大声
喊着“妞花”,声音迫切到沙哑。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刚才那贯穿黑夜的凄厉哭声便是她发出的。在火把的映衬下,她头发缭乱,脸庞模糊。我看不清她的样子,但听着她啼血般地哭喊着“妞花”这个名字,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妞花是我!妈妈在找我!
这个意识溘然在我脑筋里炸开。我想回应她“我在这里”,但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看着妈妈疯了似的奔跑哭喊,跌跌撞撞地,苦苦探求她五岁的女儿。妈妈的脚步撞开了凝重的阴郁,哭喊声在这片山谷中回荡,也在我的心中震颤。我张大嘴,冒死想回应,却犹如被人掐住了咽喉,发不出一丝声音。
我急得满头大汗,使出浑身力气,一声回应即将冲出喉咙!溘然,一个激灵,面前的统统消逝了,原来是个梦。火车发出的“哐哧”声随之传来,我还在火车上。
稍纵即逝之间,我意识到刚才那不是梦。那是妈妈在
找我,我被人带走了,妈妈很焦急,正在山上猖獗地找我。
我叫杨妞花。五岁的我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并牢牢地记
住了它。
我抬眼看向车厢,创造统统都是雾蒙蒙的,很不清晰。于是,我扭着头前后地看,没错,整节车厢都像蒙了一层薄雾,阴暗模糊。再转头看向车窗外,一片漆黑。我置身在一个完备陌生的环境,被火车带向迢遥而未知的地方,离
家越来越远,离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越来越远。我无助到了极点,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恐怖和不安,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的心牢牢攥住。
那一刻,我嗅到了一种味道,很像铁锅生锈的味道,让我生平难忘。终年夜后,我有时创造,鲜血也是这种锈味。那个梦是我至今影象最深刻的一个梦,那种对阴郁和窒息感的恐怖,也伴随我今后的人生。
踏上这辆火车的几天前,我家隔壁搬来一户新邻居。他
们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女儿,跟我家差不多。不过,
我家有四口人,我还有一个姐姐。邻居搬来后,我常常和他家女儿一起玩耍。那个女孩叫万君,我管她的妈妈叫“大
伯”。由于“大伯”以为我这样喊她比较亲。
我那时刚刚学会织围巾,正好天气有点冷了,就想织一
件围巾。但我没有签子,就从厨房拿了两根筷子到四姨家,想请她帮我削成毛衣签子。但四姨不肯,说我年纪还小,会被签子戳伤的。见我露出失落望的神色,四姨答应我,要给我织一条长长的围巾。于是,我很愉快地回家了。
万君和我姐姐同岁,我姐姐每天都要上学,万君却不用,以是每天爸爸妈妈去上班后,我就和她一起玩。那天,她专门来喊我,说家里买了新玩具,让我去她家一起玩。我对她毫无戒备,就随她去了。她家屋子是租的,只有一间屋子,进去便是床,她妈妈恰好坐在床上。瞥见我之后,她妈妈起身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很温和地问我想吃什么,想要什么。
我看着蹲在我面前、和我的视线平行的“大伯”,那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长相,瘦瘦的长脸、高颧骨、三角眼。我说想要一副织毛衣的签子,她笑了起来,点头说要给我买。
第二天,万君果真来喊我。我出来的时候瞥见“大伯”
就站在门口。她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买毛衣签子。”
我一听,愉快极了,心想,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毛衣签子了。
于是,那个小小的五岁女孩,没有任何戒备和疑惑地随着妖怪走了。她不知道,这一走,就犹如火车脱轨,从此踏上一条波折坎坷的人生之路。如果命运真的有齿轮,在那一刻,她的齿轮肯定是“咯噔”一声被卡住了,然后转出了新的轨迹,欢迎她的将是未知的深渊。
每每回顾起那一刻,我都心如刀绞。只管已经复习了成千上万遍,我依然忍不住想隔着近三十年的光阴,冲那个小
女孩大喊:“别去!她是人贩子,别跟她走!”
但那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踏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