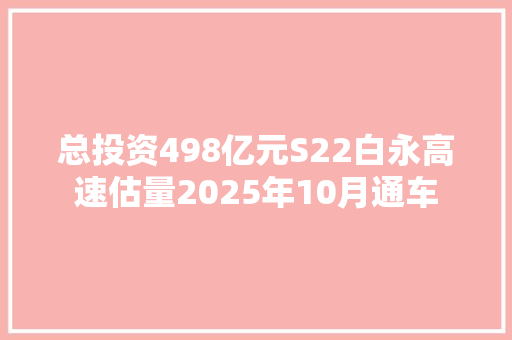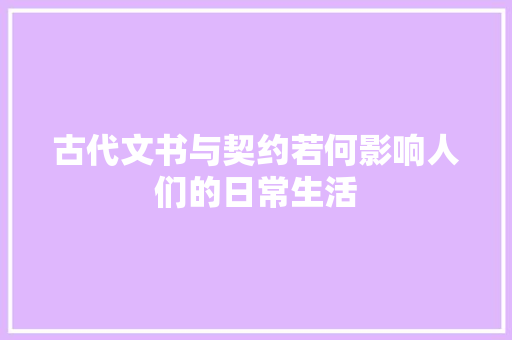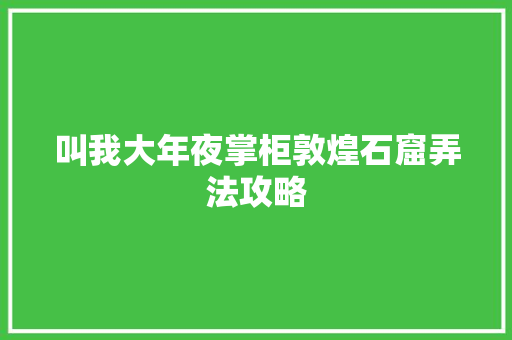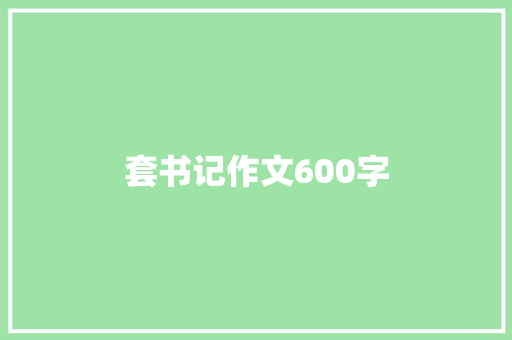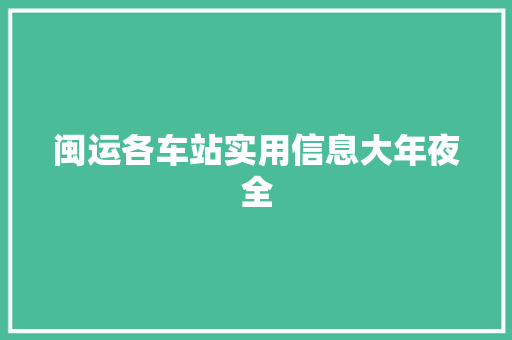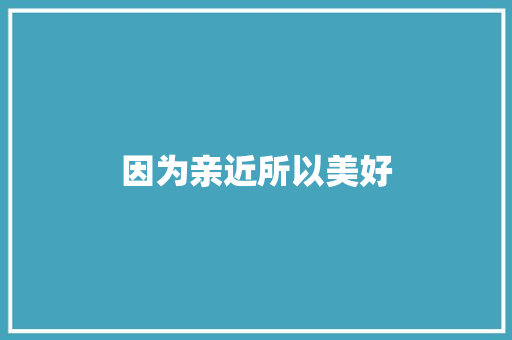厦门大学团队在永泰县梧桐镇兰亭宫现场研读历史文书。受访者供图
在福建省永泰县乡间,历史至少以三种形式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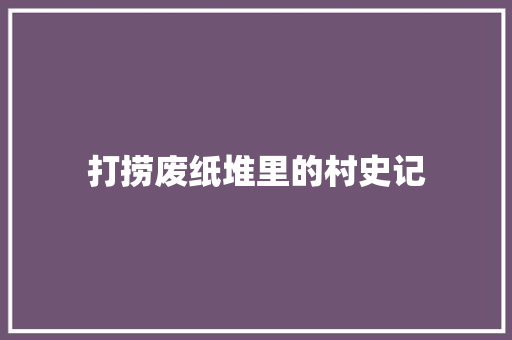
一种盘踞矗立在地面上,它们是152座散落在深山中的庄寨。这些极具规模的乡土建筑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是大家族为了共同生活和抵御外敌而建。岁月更迭,这些庄寨已成为文化和建筑遗产,它们的大门不再只对本族人开放,而那些曾在此聚族而居的庄寨子孙们也早已离开庄寨,四散成一个个小家庭。
另一种历史则活在村落民的影象与口口相传中。它可能以一句“我爷爷曾见告我”开启话头,在夹杂着神往与愁绪的讲述后,终极以一句“这些人已经不在了”的慨叹来结尾。说话的人未必亲历过他所讲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传承的速率有时也跟不上村落民老去的速率。
还有一种曾藏在瓦片下、阁楼中、箱子里,也刻在楹联上、牌匾上、石碑上。它们曾面对两种命运:被当成一堆废纸或旧时期的“遗物”被丧失落、卖掉、烧掉;或在一代代人的嘱托和通报下被守护至今。正由于有后者的存在,一些人得以恢复活过的痕迹,一些庄寨得以还底本身的故事和家族精神,一些村落落得以重拾凝聚民气的聪慧与自傲——它们便是正在被“瞥见”的永泰民间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永泰文书”)。
差点被当成废纸卖掉
永泰文书能闯进公众年夜众的视野是个意外。
八年前,如果不是一位青年学者的一声“先不要扔”,在永泰乡间,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历史文书被当作废纸处理掉。
当时,还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董思思随着村落庄方案设计机构“东南乡建”创始人张明珍来到地处闽中山区戴云山脉的永泰县同安镇三捷村落仁和庄。当董思思溜达于这座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庄寨时,他以为这里的每一处都值得追问:铺地面用的巨大青石块并不产于本地,当年如何能运进这深山里?随处可见的石雕、木刻、彩绘、泥塑工艺博识,想必造价不菲,庄寨主人的财富从何而来?
顺着庄寨内四通八达的道路,董思思走到了后楼,于有光阴推开一扇挂着“大队部”牌子的门,一眼就瞥见散落在地上的一堆文件纸张。出于研究习气,他蹲了下来,接连拣起个中几张翻阅,随即意识到,这里在集体化期间曾是三捷大队队部所在地,这些文件是大队部存留下来的基层档案,内容既涵盖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有普通村落民经济生产生活的大事小事。看出文件的系统性和完全性后,董思思难掩愉快,立时冲出去,请张明珍问一问村落干部,这些档案将要作何利用?
“我们立时要请人来打扫,把这些废纸卖掉。”听了村落干部的回答后,董思思有些焦急,他当下作出决定:“这些文书很有代价,请你们暂缓清理,由我组织团队来整理这批档案。”
永泰县盖洋乡珠峰村落十八股寨坪阄书,写于清朝乾隆十三年。 受访者供图
这一决定在日后被董思思视为“我过去十年当中做的最主要的决定之一”。在当年的5月和7月,他先后两次组织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生为主的团队来到永泰,将这批韶光跨度近40年,且递年相连几无中断的档案抢救、整理了出来。年底,他们还与张明珍的东南乡建团队一起,在修缮好的庄寨里策划了“集体化时期文书展”。与此同时,他们向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央郑振满教授申报请示了一个:在永泰其他村落,也创造了大量明清以来的民间历史文书,它们不仅包括了涉及田发生意或租赁的左券,还包括了族谱、账簿、阄书、诉状、收据、税单、科仪本、碑刻等。2017年夏天,以郑振满教授为首的厦门大学研究团队来到永泰,由此永泰文书正式进入学界视野。
回顾对永泰文书最初的挖掘过程,张明珍心头有万般感慨:“我们便是这么有时地看到那些文书,如果没有董思思来,就没有后面的几位教授跟进,更不会有大量永泰文书被创造、被重视。”
而有时之下实在也潜藏着某种一定。如果你能见到一个叫张培奋的人,你就会明白,永泰文书注定会被瞥见。
命运的齿轮开始迁徙改变
在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落古建筑群三对厝中的祥园厝见到张培奋时,他正在厅堂前的院子里一边比划,一边与人商量桌椅该怎么摆放。
张培奋剃着寸头,长了一张圆圆的脸,肤色较深,一看就常年在户外奔波。“今年6月15日到22日,永泰要举办一场历史文书野外调查活动。到时会有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过来。”在先容中,张培奋提到,这并不是永泰村落庄第一次举办类似的活动。2018年,他们就考试测验把论坛放到村落里而不是酒店里,2023年举办村落庄振兴民间论坛时,更是开启了参会者自付用度的模式。
在那张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脸下,张培奋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去理解他姓名前的各种称谓,你就能从他对永泰庄寨、传统文化、村落庄振兴的所思所想中看出,这是一位扎根在乡土的能人。
九年前,作为永泰县政协副主席的张培奋在新成立的永泰县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村落保办”)中,又被任命为主任。那之后,仅用了几年韶光,永泰庄寨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爱荆庄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永泰庄寨建筑群被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锦安黄氏家族“父子三庄寨”被列入《2022天下建筑遗产不雅观察名录》,永泰县也被评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而从最初翻山越岭、走村落串户做庄寨的挖掘、保护事情时,张培奋率领的村落保办就意识到,不能只关注地面上的实体建筑,还要挖掘庄寨里的文化遗存和内涵。八年前,张明珍之以是会频繁来永泰乡间,还带上了董思思等人,正是由于张培奋的约请——他说希望出本关于永泰庄寨的书。这之后,才有了命运的齿轮开始迁徙改变,永泰文书正式登场。
打捞芸芸众生的历史
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的名字吗?这个问题大概会让很多人陷入沉默。
这时,如果你能找到一本族谱,便可以一代一代、顺着血脉去溯源自己从何而来。而当你念出那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时,你是否会好奇,这些被你称作先人的人,他们曾如何生活、到过哪些地方、有过哪些梦想、度过了若何的生平……很可惜,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下,芸芸众生很难留下自己的“史记”。他们可能曾富甲一方,也可能颠沛流离,但跋涉过期光的长河,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只有被遗忘这一种,就像“水溶于水”。
然而,通过二三十份韶光从清朝康熙年间超过到咸丰年间的永泰文书,一位在永泰当地乃至没有留下后人的小人物规复了自己的历史——这是哈佛大学东亚措辞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每次提起永泰文书时,一定会分享的故事。
“吴履人,嵩口镇漈头村落人,租田欠租被收回,后变卖家产,包括粪厂。其子吴仙海,家族衰落亦卖产。道光年间,吴仙海离家久未归,其子去世,无钱葬,支属卖其地以葬。”为吴履人一家人撰写故事的是宋怡明和他的学生。2019年,宋怡明带着十来个学生参加了厦门大学在永泰举办的“民间文献与区域史研究”暑期学校。在漈头村落,他们创造那里有相称一部分左券文书会讲到姓吴的人,但如今的漈头并没有吴姓家族。这些姓吴的人去哪里了?带着这个疑问,他们通过左券文书里一笔笔的买卖记录和地方史料,重修了吴氏的家族谱系。而在还原吴履人,这个在历史上一点都不主要的人,所度过的悲惨生平的过程中,宋怡明捕捉到了永泰文书的一个特点——它可以创造一个从下往上的历史版本,让我们规复普通人的历史。深感永泰文书富有的代价,后来,他还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叫作“中国民间文献阅读培训课”的选修课,把更多的永泰文书以及研究放到了课程里。
钻进永泰文书里去打捞历史的并不但有学者,还有永泰本地的村落民。
“你想看文书的话,可以去我家。”在嵩口镇玉湖村落,在村落民金尔勤的激情亲切约请下,来到他家。然而,在看到文书前,的目光首先被客厅的一壁墙吸引了。那面墙上贴着一张至少有2米长、1.6米宽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几百个名字,从格式来看,是族谱。
“这一张是我自己弄的,我吃饱了没事做。”站在令人震荡的家族谱系前,51岁的金尔勤自我调侃道。他指出自己身在个中的位置——基本处于纸张底部,然后一代一代地往上数,绍朵是他的爸爸,2008年去世了;良多是他的爷爷,只活了不到49岁;宽棫是他的曾祖父,当年捐职布政司理问,在清朝算从六品官员……
金尔勤之以是会制作这张族谱,跟永泰文书的挖掘事情息息相关。小时候,他常听老一辈人讲,过去金家老先人多么有本事,最辉煌的时候,被嵩口人称为“金半街”,意为半条街的商铺都是玉湖金家的。如今通过文书,他不但看到了这些辉煌的佐证,还找回了族谱里曾丢失的一些信息。“通过剖析这些文书,我们判断出哪个人是属于哪个支系的,把族谱连接了起来。”他说。
而文书中的“五姓开垦公益之约”也让他大开眼界。过去,玉湖村落三面环水,交通不便利,往来嵩口镇都要坐船。于是玉湖五姓家族联合去山上开垦,拿经营这块地的公益性收入来支付渡船的维修费、舟子的工钱。“原来那么早以前大家就知道要有互助精神。”金尔勤感叹道。
如今,文书在金尔勤心中的分量比以往更重。拿出一个俊秀的木箱子,他说:“这便是我们家的文书,都是2016年我伯父金绍招在89岁临终前整理好才给我的。前几年我卖了两箱,大概有50本,包括地理书、医书等,一本才卖20块。现在只剩下这么一丁点,也就几十份。这些不敢卖了。”
看到这些文书,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触碰,由于有的略有糜烂、有的被小虫子啃出了密密麻麻的洞,有的虽然保存得完完全整,但一看就年代久远,让人担心一碰就碎了。但真的拿在手上后,从嘉庆年间的欠条、民国期间的分家阄书到1952年的房产所有证、1960年的结婚证……一个家族的历史就这么真实且优柔地被握在手中,每一次翻看都像穿越时空回到了历史的现场。
从2021年动笔制作新的族谱开始,金尔勤就期待着它被印成书的那天,他尤其希望把当年祖辈们如何保护文书的故事写进去。
而在同安镇洋尾村落爱荆庄,爱荆庄第二十代后人、庄寨修护发起人鲍道文已经实现了将一些家族文书整理成书、发放给族人的心愿。坐在爱荆庄内厅堂的方桌前,他拿着一本重新扫描影印好的家族阄书说:“幸好有这些文书,我们年轻的这一代人才能瞥见家族的历史。”
从藏在箱底到登上“庙堂”
2022年12月,福开国平易近出版社以《福建民间左券文书》为题名,将永泰文书列入《八闽文库》第2辑,先行出版50册——在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布告林彬看来,永泰文书的出版意义并不止于成为一家一姓一村落一个永泰的过往史料,而是标志着“民间”第一次成系统、有标准地登上了“庙堂”。
为什么永泰文书可以“登堂入室”,作为经典文献进入得到政府、官方认可的文库中?这要归功于其独特的学术代价——“归户性”“归物性”。
“这个你要特殊写一下。”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卓竞向阐明道,“左券文书这个东西在中国并不稀奇,比较著名的就有徽州文书、净水江文书。但为什么永泰文书是独特的?由于其他地方的很多文书已经流入市场、流入博物馆了,原有的系统性已经被打乱,我们乃至不知道这些文书详细属于哪个村落、哪个人,它的学术代价就大打折扣。而永泰文书是从村落民家中挖掘的,可追溯其根源。每一张永泰文书,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产生于什么地方,被哪些人接手过。同时,在搜集文书的过程中,看到文书上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及时地去做野外调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文书。”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永泰文书被村落民世代持有这一现实也给文书的搜集和保护事情带来了寻衅。
据张培奋先容,2016年至今,厦门大学历史系在永泰县村落保办等单位的帮忙下,已扫描收录永泰文书7万余件,但这个量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推论,永泰文书的总量可能有一百万份旁边。
“我们考虑过做地毯式普查,发动群众把历史文书网络起来给我们扫描,但又一贯犹豫未定,担心动作太大会惊动文物贩子。一旦发生买卖,文书的完全性很随意马虎遭到毁坏。以是,目前我们选择顺其自然,跟村落干部、当地的文化志愿者沟通,能挖多少挖多少。”他透露。
2017年夏天,当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岳沁之带着扫描仪到嵩口镇漈头村落网络历史文书时,她得到的是村落民们的激情亲切回应。他们把家中成箱的文书搬到村落部,有人乃至专程从外地赶回。在野外调查的末了一天,吃着村落里的土菜、吹着山风、喝着村落民自酿的米酒,有位学生乃至激动得哭了。而学者与村落民间之以是能建立起这份信赖,离不开村落保办、地方干部、乡贤宗亲的合营折衷。
“如果厦门大学学生自己直接去村落里面,村落里人是会有防备心的。以是须要我们帮他们组织联系,向村落民解释怎么修复、怎么扫描整理,向他们担保每包左券之后都会按原样包好还给他们。”村落保办事情职员黄淑贞说。
嵩口镇文化站站长林廉松透露,并不是所有村落民都乐意将文书拿出来。“尤其是老一辈人,他们害怕左券公开后,可能会引起一些轇轕。比如万一左券上说这个山头不是他的,他会很难办。”他说。
在玉湖村落,“90后”村落党支部布告金华厦深度参与了历史文书的挖掘事情。为了帮助一户村落民打消顾虑,他曾多次上门沟通,还通过发动家庭里的年轻人去动员老人家。
“有人说过在她家楼上的箱子里看到过历史文书,但我们去了她家好几次,她一贯说没有。后来我们动员她的儿子帮忙去找到了那个箱子。厦门大学团队到她家后,起初她一次就拿一两本。后来看到团队扫描后,不但帮她把文书用熨斗熨平,用防虫袋套起来,给她按顺序整理好再还给她,还给她分享了电子版的文书,她才放心了。”金华厦说。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村落民、基层干部、乡贤宗亲、学者、出版人等各界力量的配合尽力,永泰文书很难在这么短的韶光内完成从箱底走进论文、走上书架的超过。而如何让这种协力持续下去,也将成为下一步的寻衅。
重新理解我们的村落庄
任何人看到永泰文书,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这些文书是谁写的?乡间原来有这么多能识字、擅书法、会写作的人吗?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不但笔墨是多余的,连措辞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这几年与历史文书打了那么多交道,永泰县政协农业和屯子委员会主任陈岩进不服地表示,“过去说‘笔墨不下乡’,但通过历史文书,我们创造笔墨在村落庄中发挥了非常主要的浸染。”在三对厝,他指着一张左券说,“你看,连一些不会写字的村落民,也知道在左券上画个圈,中间一横,代表自己的具名。”
永泰文书的存在也让宋怡明有了新创造:传统中国经济没有产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从历史文书里看到永泰人在清代什么都可以证券化,连粪厂也可以证券化,变成一种有经济代价的东西。你说中国所有权制度掉队吗?这是对全体天下史,乃至全体天下的经济、政治都有启示的东西。”他说。
毫无疑问,永泰文书为学者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一篇篇以永泰文书为研究工具的论文也让它的学术热度进步神速。但郑振满教授的一句话——文书对付当地人当事人才真正主要,不是对学者主要,却让人寻思。尤其是当漈头村落党支部布告陈秋东反响,一些村落民当年合营了学生的文书网络事情,但他们后来以为自己没得到什么实惠时,一项任务摆在张培奋的面前——须要有人来回答清楚文书挖掘和保护事情之于村落民、村落落的现实意义,否则,这项事情将难以持续。
“实在不但有村落民迷惑,很多领导干部也说,搞历史文书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呀!
”张培奋的答案是,很多人喜好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但不能用做工程的思维去做文化。
“文化是极具发展性且耐久不衰的家当。文化搞好了,流量自然来了。今年春节期间,福建游神的火爆出圈便是最好的例子。”他表示,“永泰文书里藏着村落庄管理的聪慧、凝聚民气的法宝,它是巨大的宝库,能增加我们的乡土自傲,给我们精神力量。我们要做的便是,把文书的故事用老百姓喜好的办法讲好,让年轻人看到乡土文化的多元和残酷,让他们与村落落建立更深的联结。实在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不少考试测验,有的是民间自己的聪慧,比如大洋镇麟阳村落的鄢氏宗祠,你可以去看看。”
永泰县大洋镇麟阳村落鄢氏宗祠里的牌匾。农人日报·中国农网 朱凌青 摄
在那里,见到了一种分外的历史文书——牌匾。而更分外的是,在“文魁”“进士”等超过了多个年代的牌匾中间,还挂着几个写着“博士”“博士后”的牌匾,这明显是当下的新词。联系上个中一位“博士后”牌匾的拥有者鄢莉莉,她是目前鄢氏宗祠里唯一挂牌匾的当代女性,目前在中心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任副教授。
“2012年我博士毕业,后来在北京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当时挂牌匾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你不要挂博士后,博士后只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学位。但我妈去写牌匾的时候,宗祠里头的人认为博士后彷佛更厉害,说就写博士后。”提及这段情节,鄢莉莉忍俊不禁。自小生活在村落落里,她见过祠堂里的牌匾,但从没想过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会涌如今上面。
“说实话,我便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也没干出什么造诣。我以为我还不足资格去挂牌匾,这个牌匾挂上去,更多是父母的意愿,他们很以此为荣。”鄢莉莉坦言。但无论身处大城市的她以为自己有多微小,在那个小小的村落落里,全体宗族显然以她为荣。同时,从牌匾挂上的那一刻起,对她来说,与家乡的联结的确更紧密了,在参与村落落活动时也多了份任务感。
这正是张培奋等人渴望看到的改变。“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迷茫困惑的时候,可以回到历史中,回到成长的地皮里,在村落庄的这套叙事里找到自己。”张培奋说,“同时,也须要给年轻人供应理解村落落、亲近村落落、培植村落落的契机,历史文书便是一种媒介。”
2024年1月起,张培奋还开始考试测验拍摄短视频,为永泰文书的传播“扩圈”。永泰县文史研究员李剑常在视频中出镜,他曾创造,在永泰一处宋代古道的1300多个台阶上,每一踏都镌刻有为修台阶捐款捐物者的姓名。“这表示了永泰民间很有活力。我们做历史文书研究,便是想让大家更理解屯子,更懂得怎么发挥基层的力量。”李剑说。
在村落保办,大家还有各式各样的畅想。陈岩进希望能约请作家、编剧来把历史文书里的庄寨故事写成小说、拍成电影;黄淑贞认为不能只让永泰文书躺在学术论文里,要从中总结能运用于村落庄管理的履历;张培奋想做的事还有很多,策划展览、成立研究基地、办论坛、报告中国影象名录,更主要的是,连续讲好永泰文书故事。
在玉湖村落,金华厦、金尔勤、金华基还在持续摘录、解读历史文书中的细节,并家族微信群中。有一天,他们收到了一位平常不生活在村落中的族人金尔栋的。
他说:“有空我也想回来跟你们一起上山拍墓碑、解读文书、考证族谱。如果能把族谱考证出来,上可告慰先祖一脉真传,下可教导子弟惟读惟耕。玉湖金家过去的辉煌虽然不可复制,但生活总要向前。我们说走再远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我们做的不便是探求来路的出发点跟方向吗?”( 朱凌青 韩啸)
来源:农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