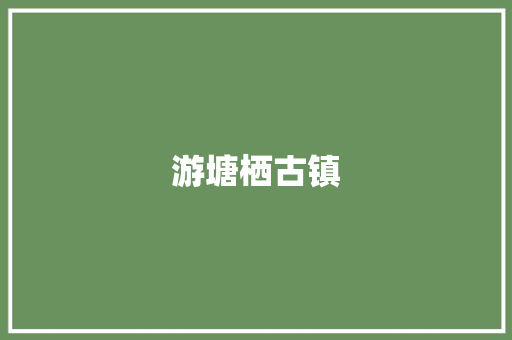【阐述者名片】
胡建伟 塘栖人,塘栖中学语文老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余杭区作家协会主席,塘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从出生至今60余年,刨去下乡插队和外出求学,胡老师未曾离开过塘栖。出版有小说集《牛滩美人埭》《村落庄颂》《狂野周末》《河之洲以南印象》,散文集《淘一首生命的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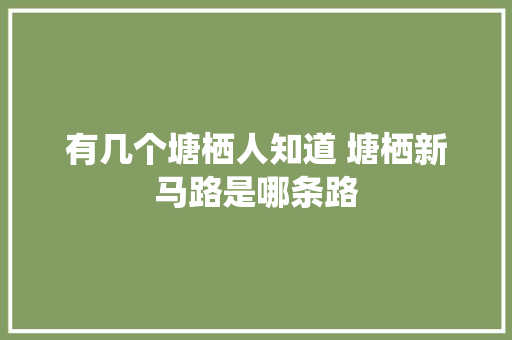
新马路在何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塘栖新马路(今广济路)/谢伟洪摄
塘栖新马路,路在何方?这大概是现在的许多年轻人要问的问题。新马路在塘栖人的口语中叫“马路啷”,它在过去的塘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儿。那么,塘栖的“马路啷”又在哪儿呢?老塘栖人会见告你:“噢,你是问马路啷啊?便是现在的广济路呀!
”
提及广济路,大家都知道,就在塘栖广济桥的南桥堍。现在,从广济桥南桥堍下来一贯往南到09省道乔莫线,都叫广济路。但是,仅仅在十多年前,这条马路既没有这么宽,也没有这么长。而且,当年的新马路,虽然冠以一个“新”字,却是上世纪30年代修的“老”路,距今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
新马路是一条水门汀浇筑的路。所谓的“水门汀”,是民国期间老百姓对水泥路面的称呼,这与塘栖古镇其他的路、弄堂大不一样,后者要么是青石板铺成,要么是三合土夯就。因此,新马路一露相,便是“民国范儿”。新马路不像塘栖其他的路,路的中间有河道相隔,而且,两边的商店门前,没有河流,也没有廊檐,更没有“美人靠”,购物的人们是可以横穿到对面的。新马路两边的建筑,当然也是民国期间的风格,这也是新马路与塘栖古镇其他地方不同之处,由于当时的塘栖,全镇便是一个明清建筑的博物馆。
新马路在当时,是塘栖最宽的一条街,却不是最长的,从广济桥堍到三官堂,也就百八十米。可是,大概是由于它的“新”,也或许是它的可以横穿两边购物方便,因此,百八十米的新马路从出身那天起,便是塘栖一个热闹的去处。
至于一条路为何叫“马路”,这或许与当时塘栖人习气思维有关。塘栖古镇地处江南水乡,自古以来,百姓出门远行靠的是舟船,民间少马。塘栖民气中的“马路”,便是古代策马飞奔的驿站官道。可实际上,它又可能并非专指驿道,大概便是较宽较直的大路而已。我们本日把通汽车的公路叫做马路,实在便是一个理儿。
筑路元勋劳少麟
广济路/唐永春 摄
提及塘栖的新马路,就不得不提劳少麟。劳少麟(1879年-1936年),名勤余,塘栖镇西小河人。家境小康,却是冥顽不化,远避当时所谓的经济文章,故屡试不举,终日闲居家中。他常与士绅为伍,诗酒唱和,谈论些天下大事,南北风情,在逍遥的光景中丁宁光阴,在横目苍天和壮志未酬中等来了大清皇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民国13年(1924年)受德清县故旧、出身探花的俞陛云之邀,劳少麟独身只身前往中国北洋政府所在地北京。俞陛云是清翰林院编修,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和字画大家吴昌硕的老师俞樾之孙,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之父。这是劳少麟生平中唯一的一次远行,他要去看看表面的天下,去感想熏染一下表面的空气,由于时年45岁的他,心里总揣着一个梦想:为几百年来不变的塘栖做点什么。期间,因其长于交际,博得国务总理孙宝琦青睐,谋任国务院某部佥事一年有余。1929年,劳少麟去职返回故里,担当塘栖西镇镇长。
彼时的塘栖分东、西两镇。东镇是塘栖经济繁华的闹市所在,西镇则冷落落寞,水北街尚从属于湖州德清县。上任伊始,劳少麟站在古风悠悠的广济桥堍南望,面前冷落的市井,让这位中年男人的心里生出了些许的飘摇。干吧!
在北京呆了五年,开阔了眼界的新镇长,决心鼎新西镇市容,把广济桥堍到总管塘百余米的破败甬道改建成一个新的街市。他想,有广济桥这座塘栖标志性的建筑,不信新建的街市聚不拢人气。
塘栖西镇这边市情冷落,西镇镇公所财政捉襟见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新辟一条街市,启动资金从何而来?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劳少麟对此彷佛早已胸有成竹。他以镇公所的名义告示全镇商贾和民众:凡是乐意在新街开店的,可签订协议,预支拆迁、拓路和建房用度,统一施工,多还少补,平房楼宇,悉听尊便。结果是一呼百应,新街市和新马路就真的建起来了。
政府没钱搞城市根本举动步伐培植而向民间借力,现在叫“PPP”,也便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缩写,也即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以特许权协议为根本,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互助关系,并通过签署条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以确保互助的顺利完成,终极使互助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想不到80多年前的劳少麟也会这一手。这真是不怕当官的有文化,就怕当官的既有文化又有创新的思维啊!
新马路旧时的样子容貌
据1990年版的《余杭县志》记载:劳少麟1930年发起开辟塘栖西镇新市场,选址在广济桥南桥堍至总管塘百余米凌乱甬道,拆去旧房,夷平道路,建房造楼,一年余新市场建成。
所谓塘栖西镇新市场,实在便是一条新街。新街的路面由混凝土浇筑而成,条石镶边,大路朝天,宽阔平直。沿街建铺面60余间,店门均为玻璃橱窗,宽敞通亮。因其与塘栖东、西两镇原有的廊檐盖街、路幽店暗之旧街面貌迥异,塘栖人便称新街为新马路。
新马路所开各店,以做事业为主,迎合时期新气息。有酒楼、茶馆、旅店、浴室、摄影馆、西药房、电话所等等,个中的“栖味馆”“栖园菜馆”“孙鹤轩摄影馆”鼎鼎有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些店家还在老地方业务,只不过经历了“公私合营”等等之后,这些店家都换了店名,比如广济桥南桥堍角上的塘栖面馆,原是栖味馆的旧址,孙鹤轩摄影馆改叫塘栖摄影馆,而栖园菜馆则改成了当时塘栖最大的冷饮店。文革之后的有一年,《红楼梦》电影解禁上映,蜂拥而至的附近乡民不仅挤满了塘栖剧院,电影散场后吃冷饮的不雅观众还把原“栖园菜馆”的楼板踩塌了,好在这是民国期间的木构建筑,这次事件并未伤及人命。
新马路从建成的那天起,因其全新的气候,无疑成了塘栖这座千年古镇时尚的所在。外来客商和运河过往船户上岸休憩、饮食、逛街、购物、投宿,不仅方便,更有恍若隔世之感——新马路的酒肆茶楼设有艺人说唱专场,评弹、滩簧、说书、独脚戏,好戏连台;新马路的电话、摄影、西药、浴室等等新玩意儿,更是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一韶光,塘栖新马路商贾云集,买卖兴隆,十里八乡的民众纷至沓来,造诣了塘栖古镇一条靓丽的新风景线。
重新马路到运动场
新马路,1990年版《余杭县志》记载是青石板铺的路面,后来大家熟习的水门汀路面是何时浇筑的,现在已无从查考,或许是“县志”所述有误也说不定,由于以劳少麟的见识,在上世纪30年代采打水泥浇筑路面,也是说不定的。
塘栖新马路不敷百米,到总管堂的丁字路口,往东向北走是去吉家兜、仓桥头、墨鸭埭的老街小路;往西则是一条同样无廊檐的新街路,实在便是新马路的延伸,拐弯抹角地向着东北,终点便是塘栖人称作“运动场”的地方。
在劳少麟修建新马路、开辟新市场之前,总管堂以西一带,实在是塘栖古镇的荒郊野外,坟冢、破庙、荒地连片,平时是很少有人光顾的。劳少麟开辟新马路的成功,进而便向当时叫做“花园坟”的方向拓展。重新马路修路到花园坟,沿途建造了露天市场、熙春剧院、火力发电厂、勤余小学校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富有全新气息的城镇公共根本举动步伐项目。
特殊值得一提的是,在花园坟平整出来的空地上,劳少麟又将当代体育引进了塘栖古镇,举办了古镇历史上第一届青少年足球比赛,还有放鹞子比赛等等。此前,对劳少麟开辟新马路之举,时人或有非议,但他不为所动且在广济桥堍勒石记事。此时此举,时人除了惊异的目光,说东道西的倒反而少了。
关于塘栖新马路的那一段历史,有两件事还得说一说。
其一是晋代郭璞井遗址的创造。据“县志”记载:劳少麟在平整花园坟施工中得晋郭璞建井古碑两块,按碑文所记深掘,得废井旧址,井圈石尚在;再循井圈挖至井底,有水甚清澈。乃筑墙保护,立旧碑于壁墙,西侧置木栅门,供打水出入。也便是说,劳少麟不仅喜新,而且恋旧,现在广济桥南桥堍的郭璞井还真有其事,只可惜是“拆迁户”而已。
其二,旧时的花园坟空地,于解放后的1951年被正式命名为“塘栖广济路运动场”,这是余杭、杭县两县第一个正式冠以“运动”之名的场所,而发轫人正是劳少麟。塘栖运动场于1963年改作他用。期间及至文革开始,塘栖运动场一贯是古镇人们集会和开大会的场所,倭寇侵华时日本人在那里杀过中国人,也曾经做过1958年“大炼钢铁”的园地。那里还曾经有一座石砌的“司令台”,台面的正中是“塘棲公民公社”六个大字,两边有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这个司令台听说是专为塘栖青年增援宁夏而建的,故又叫“支宁留念台”。
塘栖运动场的淡出人们视线,始于塘栖“红太阳”广场的建成。从此,塘栖人集会有了新的去处,运动场就逐渐被冷落了。再往后,司令台拆了,石狮子也不知所踪。哦,对了,运动场那里那边所现在就叫“塘栖公园” 。
来源:余杭晨报 阐述者 胡建伟 整理者 姚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