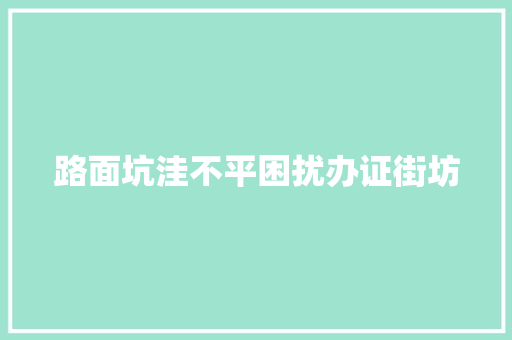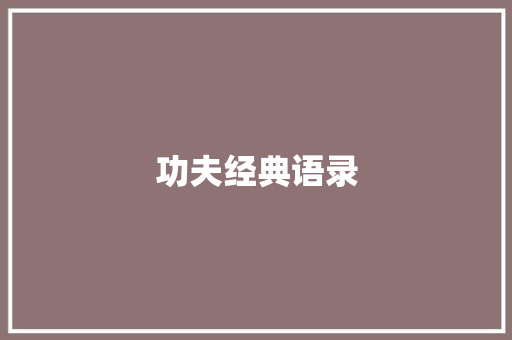在顺德大良的高坎巷口,谢满春的修车铺存在了近十年。人来人往,路子此处的街坊都能创造这位于一隅的修车档口,而它也成为了小巷风景的一部分。
二十年如一日,谢满春修了无数辆单车,而小小的档口,也成为周边街坊口中的“口碑小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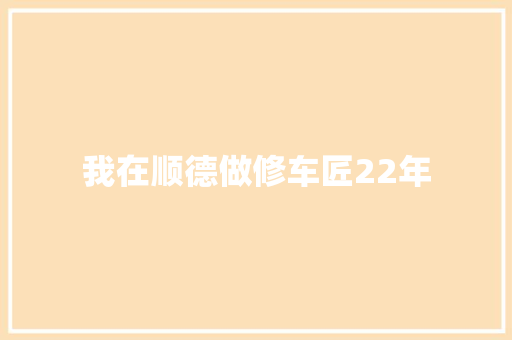
“年纪大了,加上现在大家都骑共享单车,修车买卖少了。”一身技艺难敌时期“年夜水”,谢满春决定“罢手”,作别这座城市,回家开启新的人生。
谢满春和修车铺末了的合影
来顺德做“修车匠”
“当时大家都往南方跑,我也随着湖南老乡,来到了顺德。”1998年,在南下打工的热潮下,谢满春也来到了顺德“搵食”。
在谢满春的影象中,年轻时的自己,就尝尽了穷日子的苦。“家里就一点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家里吃不饱。”又是一年春节时,谢满春也不禁回顾过去,彼时过年,家里人都“守着”一头猪,宰了后卖一点挣钱,分一点给亲戚,剩下一点留给自己家吃。“肉的味道一年就尝一次。”谢满春说。
上世纪90年代,路上“跑”的私家车还未如今天这般多,生活过得去的家庭里,总会有一辆或两辆“铁驴”(单车)作为代步工具。修车匠,自然成为了一份有需求的“技能工”。
“当时,有不少湖南老乡在顺德修单车,为了赢利,我也就随着他们学修车。”谢满春说,有老乡在顺德做五金买卖,但自己没这个本钱,也就无法“跟投”。“不如修单车更实在。”而关于修车这门技艺,谢满春说是“老乡带入门,得靠自己悟。”上手后,谢满春便在大良河岸边摆了一个修车摊。
“那个时候,这里还没那么多人,阁下都是农田、水田。以前路上,大家都是踩着单车出行,就像现在很多人骑电动单车一样。”谢满春和回顾着那时候的城市“风景线”。
面临“无车可休”的无奈
凭借着博识技艺和老乡、街坊们的口口相传,谢满春的修车买卖有了转机。“大家便是一传二、二传三,逐步地都来找我修单车。”
2012年,谢满春将自己的修车摊搬到了高坎巷康乐村落的巷口,租下了4平方米的档口,这里也成了谢满春“大展技艺”的地儿。
谢满春在巷口的修车铺
过去靠着修车,谢满春过上了算是自足的生活。“以前修一天车,连本带利可以收入几百元,一个月下来可以挣下个几千块。”谢满春说,除掉日常开销,自己每个月都能存下一笔钱。
“我的收费不贵,在不换材料的情形下,我就收街坊几块钱。”谢满春说,自己能得到一众街坊的信赖,靠的便是“实在”二字。
为了多赚一点,谢满春的妻子也从湖南来到顺德。一韶光,修车铺成为“夫妻档”,谢满春修自行车、修鞋、修伞,而妻子则顺便帮街坊缝补衣服,补贴家用。
“后来买车的人多了,路上又有了共享自行车,大家都是扫个码,骑到哪,停到哪,很方便,不须要自己买自行车了。”在今后的日子中,谢满春逐步感想熏染到了自己要被时期给“淘汰”。
“你看,共享自行车那个轮轴,我拆不了,不好修。”谢满春说,自己节制的修车技能,已经无法“匹配”现在的新产品,“还有街坊送来电动车让我维修,我不太懂,除非是轮胎、零件有问题,我可以换一换。”
一身技艺难敌时期“年夜水”。“这一两年,一天也就修几辆单车,赚不了多少钱。”感想熏染到了“无车可修”的谢满春,也一贯思考着,要不要就此告别这门行当。
究竟是离去的时候
修车铺里曾经宝贵的补鞋机
不舍和顺德的告别
今年初,谢满春决定“不做了”。
“一方面确实也没车修了,另一方面我的身体也不如以前,我要带着一个老花镜,才能看清楚这些零件。”谢满春说,家人都在湖南老家,孙子也由老婆照顾,“离家那么多年,一贯没怎么陪家人,是不是要回去享受一下清福?”谢满春愉快地说。
离开顺德前,谢满春开始清理他待了近十年的修车铺。
“一些不要的东西,当做‘烂嘢’(废品)卖掉,没什么可惜的,也带不走。”在修车铺,谢满春指着他曾经如数家珍的补鞋机和先容,“那个时候,这个机器都要好几百块,很贵。”
“啊,你不做了?”看到了谢满春在整顿档口,无论是否帮衬过买卖,途经的街坊纷纭上前讯问,语气中多有惊异和不舍。“还回来吗?”
“驻扎”此处多年,谢满春与街坊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都会打呼唤,举头不见低头见。”谢满春说,街坊们有时候有多的菜,也会分自己一点。
有媒体人特意为谢满春拍下一张照片
在顺德生活了二十年,谢满春还能用大略的粤语和街坊互换。“来到广东干了这么多年,我听得懂,听多了我自己也会说一点。”谢满春说。
在高坎巷康乐村落一带,租住了不少低收入群体,有的靠收拉纸箱瓶子挣一点生活费,生活不易。“他们会把三轮车拉来给我修,我都不会收他们很多钱,他们都是街坊。”谢满春说。
知道谢满春要离开顺德,一些街坊特意来告别。“我会记得这里的统统。”只管心中有万般不舍,谢满春还是和街坊回话说:“不回了,不回了。”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 黄子宁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胡群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