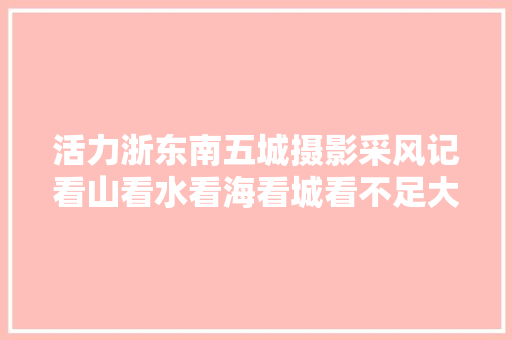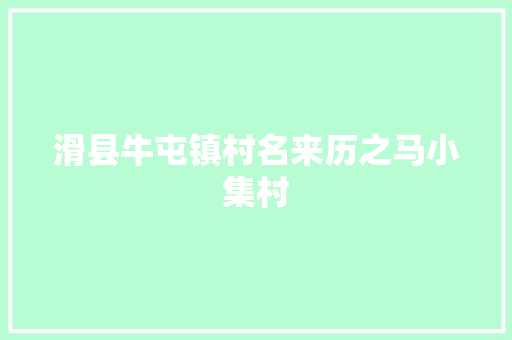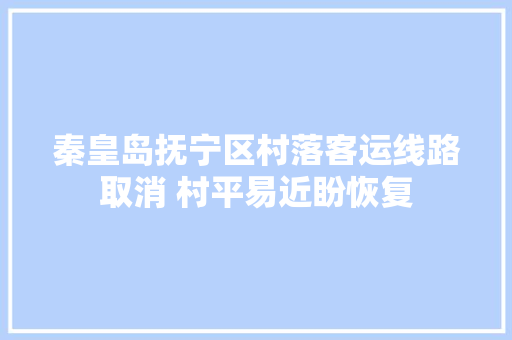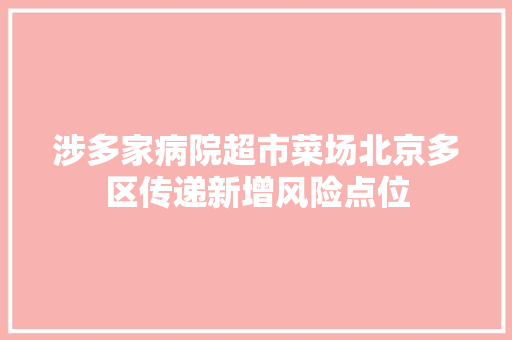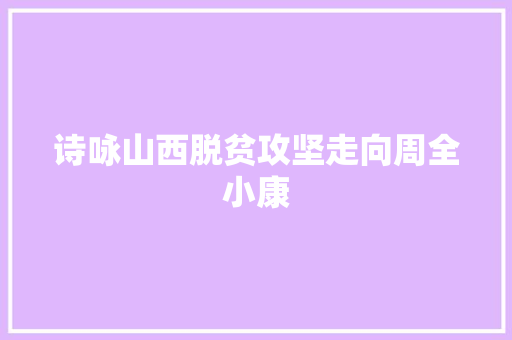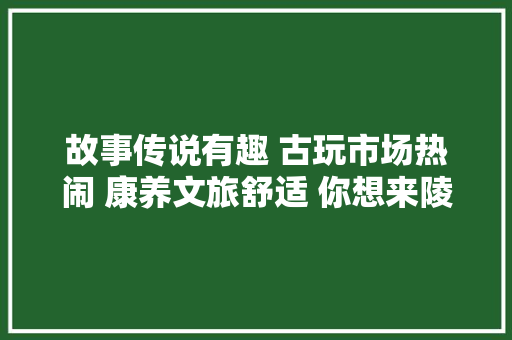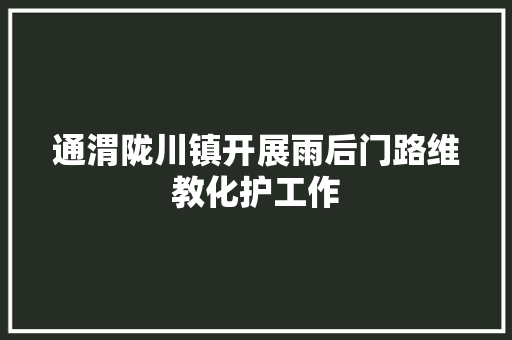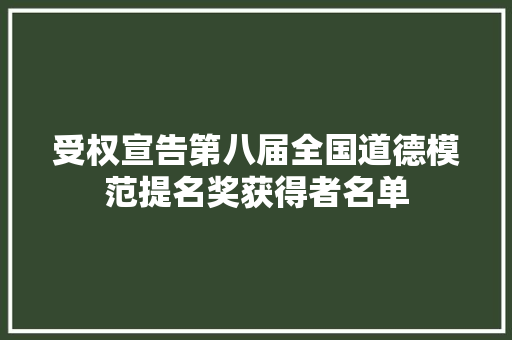豪杰本便是明治维新的产品,学校,作为维新思潮鼓荡的中央,自然也就成了这些豪杰扎堆汇聚的所在。各学科中最具狂放脾气的艺术学科,更为豪杰气概烈火烹油。于是,在明治日本压倒一切的艺术院校东京美术学校的大门口,上演再荒诞的豪杰活剧,众人也见怪不怪。毕竟,这座院校自出身之始,就孕育着冲突与对立:象征文明开化的泰西艺术理论与日本传统艺术美学四目相向,其一触即发之势,稍不留神,就会擦枪走火。
然则日清晨,校门口的一幕,仍旧让神经大条的学生们瞠目结舌。他们看到自己熟习的教授把守大门,力阻那些身穿法国巴黎盛行衣饰的学生进入学校。比起那些学生身上泰西风格的“奇装异服”,教授身上的服装更显怪异,那是一身中国式的长袍马褂,配上一脸持重肃穆,晓风袭来,尤显出一派荒诞不羁的豪杰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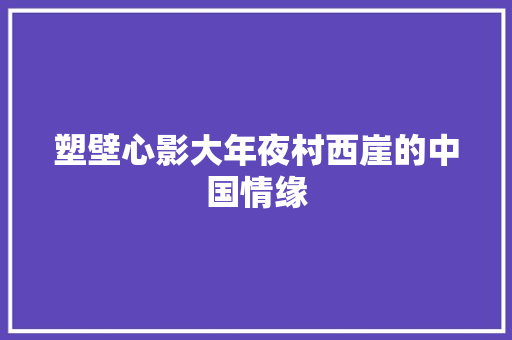
本文出自11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塑壁心影:大村落西崖与中国雕塑之缘”专题B02-03版。
撰文 | 廖鹏
《中国雕塑史》(全三册),[日]大村落西崖著,疏蒲剑/姚奕崴/管浩然译,广东公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叛逆”的明治之子
大村落西崖可谓不折不扣的明治之子。他出生于1868年7月13日,三个月前,被倒幕派推上前台的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开启维新时期。次年,倒幕派与幕府军之间的内战拉开帷幕,大村落西崖的故乡静冈县作为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困居之地,自然也被卷入个中。随着战乱的结束,维新之风终于刮遍这片地皮。年轻的大村落西崖也像那个时期渴望站在风口浪尖的青年一样,对未来充满着乐不雅观得近乎狂放的想象。但另一方面,虽然公路戳破了村落庄的封闭自守,电灯也照亮了传统屋舍中弥散千年的阴翳。但心灵的古老领地却尚未被乍然入侵的新潮思想完备盘踞。对神佛的崇奉,和与神佛相生相伴的日本传统美学,依然沉默无言地浸润着这片新风吹拂的地皮。多年后,大村落西崖仍回顾起自己童年时,父母笃信佛法的情景:
“予之生父母法华信者也。以故,予自婴孩时,朝夕闻读经之声,熟于耳,记于心,髫龄自能诵《方便品》《寿量品》等。”
大村落西崖照片,左为1918年大村落西崖因《密教发达志》获颁日本学士院奖的照片,又为大村落西崖1921年在中国稽核时身着长袍马褂的照片。
1889年,21岁的大村落西崖,作为静冈县的精良生,进入东京美术学校,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期入学者。东京美术学校,在成立之初,就有着成为日本压倒一切艺术院校的勃勃年夜志,它的首任校长冈仓天心,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都被认为这天本明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家。当“脱亚入欧”的思潮席卷日本之时,冈仓天心却貌似反其道而行,提出“现在正是东方的精神不雅观念深入西方的时候”。这一不雅观念,初看像是“脱亚入欧”思潮的反动,表面上鼓吹亚洲文化的一体性,将日本作为亚洲文明的范例代表,但本色上,无论是“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还是“复兴亚洲代价不雅观”,抑或是所谓“亚洲的爱与和平”,都是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所进行的解读。由此生发出的所谓“兴亚主义”,更奥妙地将从西方趸来的二手民族主义思潮贯注个中,以高唱人性自由,排斥物质争竞为名,将这一不雅观念提升到精神领域,改造成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以知足日本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风雨飘摇的国家自傲心。
东京美术学校,正是冈仓天心践行之一理念的教诲工具。在科目的设置上,冈仓天心收受接管了美籍客座教授费罗诺萨(Earnest F. Fenollosa)的发起,以提倡日本国粹的办法,来与当时来势汹汹的泰西艺术美学分庭抗礼。日本画和雕刻,被认为能够代表日本国粹,因此备受推崇。特殊是雕刻科,尤被认为是足以和泰西反抗的日本精粹所在,因此备受奖掖。1876年,附属于文部省工学部的工部美术学校特殊规定:“美术学校的全部学科,唯有雕刻科学生,可用官费就学。本邦雕镂师职业,历来被视作庸职贱业,但在欧洲,却为上流人士扬名立万之高尚技艺。特以此规定褒奖立志以雕刻学贡献社会之有志之士。”
大村落西崖来到的,正是这样一所肩负着复兴日本文化精神的艺术院校。而在这里,他碰着的雕刻老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大村落西崖回顾当时美术学校的雕塑课说:
“当时雕刻课所教,专在日本古风技能,其原本多用佛像,因始发欲知佛像尊容、印相、持物等由来之念。教官有今泉也轩,颇好佛教。其讲考古学于校堂也,常手念珠,每每谈密教。予欲学焉之志愈切矣。”
在日本,佛教与雕塑之间的关系,如身随影。日本镰仓时期最精彩的两位雕塑大师运庆、湛庆父子,都是佛像雕刻师。至今,前往日本著名古刹三十三间堂游览拜会的游客信众,仍能从佛像精妙的雕刻中读出昔日大师恭谨的忠诚之心。雕刻不仅是手艺,也是心灵的艺术,更是崇奉的艺术。理解这一点,成为了大村落西崖步入雕刻史堂奥的关键一步。
冈仓天心和费罗诺萨(Earnest F. Fenollosa)
在这种学习环境下耳濡目染,大村落西崖理应很随意马虎被冈仓天心充满“精神”“文化”“代价不雅观”的理论所吸引,成为他娓娓动听的兴亚学堂中一名精良的学生。但令人惊奇的是,大村落西崖却成功地摆脱了这种强烈的诱惑。这位精良的毕业生竟然走向了老师的反面。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冈仓天心和费罗诺萨构建美学史的核心之处:这两位日本美术史的首创者精心构建起的大厦基石并非坚实的史实材料,而是玄虚的理论。本当成为基石栋梁的史实材料,反而成了理论的点缀和装饰。费罗诺萨的研究紧张依据日本美术品和在日本收藏的中国美术品进行,而对同期已在中国广泛开展的野外考古并取得的巨大造诣视而不见。比如殷墟、敦煌的发掘。冈仓天心的美术史是“以论代史”,美术史只不过是此中兴日本美术、倡导日本美术中央论、日本美术精良论的工具。
大村落西崖性情倔强,不雅观点明确,他不赞许“以论代史”,主见“治史论实”。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大村落西崖从事德国美学研究,同德国美学家霍特曼一样主见“自然”,被戏称为“大村落-霍特曼”。日语“自然”一词是明治维新后对英文“Nature”的翻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学界尚没有清晰的定义,同时具有泰西近代新不雅观念和东洋传统不雅观念两重意义。大村落西崖从“自然”一词中领悟到西方的实证主义精神,同时把这种精神贯彻于自己的治学之道。一如日本学者庄司淳一在《美術と自然—大村落西崖の「自然」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
西崖的著作无论从任何细部来看,都有着通过引用文献来确认的事实依据。他的所有论述也不是对事实乏味和呆板的罗列,字里行间仍可以感想熏染到他强烈的激情亲切……他的著作之以是能成为座右铭,正是由于彻底的“实证”。
针对母校教授冈仓天心的美术史著作,大村落西崖指出:首先冈仓天心的不雅观察和立论有概括和笼统的取巧之嫌,难有说服力,由此产生漠然和根基薄弱的弊端。大村落西崖用“自然主义”鞭笞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日本美术精良论”。
1893年大村落毕业后从事传授教化事情,先在京都执教,后来回到母校。因不雅观点不同,大村落西崖与冈仓天心激烈冲突,从此,成为冈仓天心最大的论敌。他还将冈仓天心的得意学生横山大不雅观、菱田春草创造的新日本画批驳为“朦胧体”。东京美术学校校门口的那充满豪杰气概的一幕,正是故作长袍马褂装扮的大村落西崖,以自己的办法,对宰制日本美术界的冈仓天心和他的学生学派发起的一场正面攻势。
横山大不雅观的名作《屈原》,绘于1898年,横山大不雅观是冈仓天心的学生,与大村落西崖都是东京美术学校的第一期学生,但两人却因不雅观念不同而产生龃龉。冈仓天心评价大不雅观:“横山大不雅观之作,发自奇思妙想,每每出人意表。从创作《屈原》开始,将高蹈雄伟的新思想引入画坛,恐怕无有出于大不雅观之右者。”而大村落西崖则嘲讽横山大不雅观的作品及其代表的美学是“朦胧派”。
横山大不雅观的另一幅作品《彗星》,描述了1910年哈雷彗星拜访地球的情景
只管此时的大村落西崖已然声名鹊起,但仍旧是孤身作战,在外人眼中,他长袍马褂的打扮纵然算不上不可理喻,也称得上风趣可笑——自1894年甲午战役中国惨败后,昔日的天朝上国一时沦为执拗不化的垂垂老朽,自然会受到明治维新后顾盼自雄的日本唾弃嘲笑。大村落西崖这般做派,无异于成了食古不化的守旧冬烘。众声喧哗的明治-大正时期,唯有理论可以故作玄虚,高唱入云,因此更能引得全球瞩目。而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学,却难逃灰头土脸之讥。只管这场论战以大村落西崖缄默退场而告终,但他耿介的性情和“治史论实”的治学理念,一如刻刀,在激辩论战的磨砺下更见锋芒,当他决定奏刀雕刻他的作品时,会让众人看到他是如何使刀如指,游刃有余。
创造“雕塑”,结缘中华
“现森罗万象之形,具霎时之相,现出浑然之美,长留于人间,待心腹于千岁,刓逋客之俗肠。”
1893年10月,26岁的西崖揭橥《雕塑在美术界的地位》一文。在文中,他如此阐述雕塑所具有的力量。“雕塑”一词见之于论文,此为大村落西崖创始。他指出:“雕塑占立体之全境,显形想之美,以实体穷沉雄持重之趣。”“从实有界不雅观之,雕塑为最完备之形相美”。
1894年10月,又揭橥论文《雕塑论》,更全面地阐述了他关于雕塑的主见。大村落西崖给“雕塑”下了明确的定义:“何谓雕塑?即具有实体造形艺术之总称。”接着他从“雕”与“塑”所具有的美术意义的视角,对“雕刻”与“塑造”作了如下差异:“木与石则取其材而雕刻之”,其技法是“消削性的”,与西方的carving一词附近;“蜡和泥则用其质而捏塑之”,其技法是“捏成性的”,与modelling的意思附近,而“雕塑”一词正可以涵盖“消削性之雕刻与捏成性之雕塑”。
日本因与中国有着分外的佛教渊源,近代中国大量宝贵文物流失落外洋,收藏了大量中国佛教雕塑。仅帝室博物馆(即后来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收藏了包括天龙山21窟的“如来倚像”及著名的“七宝台石刻”在内的差不多3000佛像。大村落西崖从前的发展环境和在东京美术学校的学习经历,都与佛教息息相关。1911年10月,大村落西崖皈依佛教,他对佛教及佛教美术特殊关注。由佛教透视美术史,成为了他研究美术史的切入口。在1906年揭橥的《东洋美术小史》中,就有大量佛教美术的研究:唐五代研究中,大村落西崖特殊从佛教幡画谈论后世挂轴的起源;佛教美术叙吴越王造宝箧印经塔;炽盛广佛在五代的盛行。宋代更是先容了佛教美术的盛行题材,罗汉、祖师像的崛起,特殊这天本寺院从明州得到的佛画,关于佛教美术的研究元明清各代均有诸多内容。
大村落西崖有感中国的字画书本汗牛充栋,然后记录雕塑的书本,却无一本,许久以来,大村落西崖都为这一领域短缺文籍而感叹。有着雕刻科毕业背景,加之编写《东洋美术史》对佛教美术及佛像材料的搜集,依托日今年夜量中国文物和佛像影像、拓本收藏,便匆匆使大村落西崖坚持十余年的资料搜集,编写了《中国美术史·雕塑篇》这一划时期的巨著。
《中国美术史》书封,大村落西崖著,陈彬龢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此书即大村落西崖《东洋美术史》中国部分的摘译。
1915年,《中国美术史·雕塑篇》由佛书刊行会图像部出版,此书集日本几代学者成果之大成之作。这部著作资料的网络历时十余年,困难自不必言,大村落西崖一度认为机缘尚不成熟想要放弃。
后来,得到明治期间美术界先驱、已故的冈仓天心这些起先游历中国带回来的雕塑影像,创造冈仓觉三早已经在关注中国的雕像,带回来的广元千佛崖等各地的照片,给大村落西崖极大的振奋。
同时,早崎天真长期逗留西安及北京,游遍河南、山西等地,拍摄的龙门、大同等石窟及分散各处的遗迹文物影像,归国后将影像资料赠与大村落西崖所在东京美术学校。其见闻最精华属华塔寺,带回了碑铭拓本等资料可以供大村落西崖尽情研究。其后,塚本靖、伊东忠太、关野贞三位博士及平子铎岭亲赴大江南北广泛拍摄遗迹,所留下照片、拓本,都供大村落西崖研究利用。
近代来华的冈田博士、内堀维文、铃木直三郎、竹内金平、老田太文、八杉直、黄中慧等人从中国带回了道佛雕塑、金成全品、砖瓦、墨本等,使得日本的博物馆及大学馆藏日渐丰富。还有古时流传下来藏于正仓院的无数珍品,以及古代入唐请回来的佛像等材料都被大村落逐一网集。此时,大村落西崖才以为略知中国古代雕塑变迁,认为机缘成熟可以写作了。
1914年冬天,大村落西崖听说鼎鼎大名的中国硕学罗振玉旅居京都,并知道罗振玉有极丰富的金石藏品。经内藤湖南博士及藤田剑峰先容,两度登门拜访:
“我与罗振玉师长西席一见平生,只言片语,仿佛故交。仰赖这份深厚情意,我得以借阅两千多种雕塑拓本。不仅使资料近乎倍增,更能够与过去所看到的浩瀚拓本相互参照,补正著录疏漏之处。又承蒙罗振玉师长西席指教,大有裨益,并且有了新的创造。譬如汉画像石,尤为仰仗他的秘藏,还得到了很多未曾收录的精妙拓本。”
罗振玉像
罗振玉见大村落西崖纵谈中国古雕塑能够旁征博引各种文籍,滔滔不绝,惊异于大村落西崖的见闻之广博,于是大方将自己所藏的两千多件古器物、古刻墨本让大村落西崖遍览。西崖求知若渴,摄取影像,摘录笔墨,日以继夜。罗振玉感叹大村落西崖对中国雕塑研究专注和勤奋。在后来为《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作序,罗振玉难掩惊异之情:
“解韬绳读之,书厚逾寸,密行细字,无虑数十万言,征引至繁博。肇于邃古,而下逮赵宋,阐述井井有条理,盖言吾国雕塑之书,未有如此之详且尽者也。”
大村落西崖之后与罗振玉该当还保持着学术上的互换,《密教发达志》也可能得到过罗振玉的指示和帮助,1916年,罗振玉为其书名题签。大村落西崖去世后,家里依然挂着罗振玉篆书的横匾“留书藏石”。
中华觅知音
当初撰写《东洋美术史》时,大村落西崖就一贯渴求能一履中土。罗振玉的渊博学识,更让他对他乡未见的朋侪心生企慕。但遗憾的是,资金的匮乏,一贯是他前往中国的一大阻碍。与美术界大佬冈仓天心破碎后,大村落西崖公费访华的可能也微乎其微。为了张罗旅费,他绘制了20双折半的金屏风画,终于筹得一万两千元川资。
1921年10月21日,大村落西崖踏上了中国之旅。而这一次旅程,让他结识了一位契心石友:陈师曾。
近代西学东渐“美术革命”论,引火“文人画”之争。鲁迅称一些当代派绘画为“怪画”,陈独秀则把倪黄文沈一起的文人画叫“恶画”,批评文人画(他在文章里叫“学士画”)“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另有“临”、“摹”、“仿”、“拟”,复写古画,不事创作之流弊,断然要革取性命。
1921年陈师曾连发两篇文章《文人画之代价》、《文人画是进步的》,站在世界美术演进的大势和艺术内部自律发展的高度,论述文人画代价和进步性。
1921年,大村落西崖初次访华,结识了中国著名画家陈师曾(陈衡恪,陈宝箴宗子,陈寅恪长兄),二人一见如故。陈师曾翻译了大村落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又加上自己的《文人画之代价》一篇,合为《中国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刊印出版。
与之隔海相望的日本,同样对中国明清文人画存在着偏见。文人画曾是中国元明清绘画的主流。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见过元四家、明四家、四王、扬州八怪、二石、八大等正宗的文人画,而是接管有时流传到日本的二三流画家的作品。所谓日本文人画,每每是用这些劣等的绘画东拼西凑的产物。费诺罗萨认为中国美术在公元8-9世纪之间达到高潮,此后趋于衰落。冈仓天心也与费诺罗萨见地同等:“日本美术在世界上名声很高,毕竟是由于继续宋代文化的缘故。”而对后来中国美术的评价也不高。费诺罗萨和冈仓天心的见地,可以说代表了从明治期间以来的日本美术界中一向很有影响力的一种态度——重唐宋,轻明清,排摒文人画。
辛亥革命爆发后,昔日宫廷贵胄秘藏的字画开始流向日本,日本人首次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元明清绘画佳构。社会上重新唤起对文人画的好奇心。东京帝室博物馆在1917年4月首次举行了南画特殊展,与其前后呼应。通过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文人画的打仗,大村落西崖萌发了对文人画的新认识。
1921年1月7日,大村落西崖完成了自己生平中主要的论文《文人画之复兴》,并在同月25日由东京巧艺社出版。在《文人画之复兴》中,他推翻了自己一贯坚持的自然主义学说,认为只有“从自然中分开”,才是艺术的实质;同时,他还开始编辑出版《文人画选》,利用东京美术学校的讲坛和其他讲演大力倡导文人画。在偃旗息鼓近40年后,日本再次涌现文人画热。
“比来开始画文人画,加倍想多看中国的古代画。”
大村落西崖访华,正是携这股文人画的热潮而来。这股日本反哺的热潮,陈师曾等待已久。11月1日,大村落西崖与陈师曾会面。陈师曾阅读大村落西崖著《文人画之复兴》。读罢大喜过望——大村落西崖文章与自己的不雅观点竟不谋而合。陈将其译成中文,与自己的《文人画之代价》合编为《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陈师曾绘《北京风尚图册》之《墙有耳》
在陈师曾的勾引下大村落西崖会见了一批京华最高级的画家和收藏家,大村落西崖陆续结识了完颜景贤、庆小山、陈半丁、杨啸谷、廉南湖等收藏家,目鉴履历激增,金城、陈师曾等人为他开启了民国初年收藏家的大门。
“吾生来爱书,赛过爱饭。”
在中国,嗜好字画的大村落西崖可谓如鱼得水,昔日只在照片和书本中见到的字画名品,如今如巨潮奔涌而来,让他目不暇接。在北京,他与逊清小朝廷的“帝师”陈宝琛结识,获准拍摄清室秘藏的字画。陈宝箴将字画从宫中携回自家宅邸,大村落西崖逐日携同两位日本拍照师前往拍摄,拍摄字画达八十余幅。在共计五次的访华经历中,他险些看遍自唐宋以来及至明清所有主要画家的作品,个中包括王维的《伏生授经图》、李公麟的《五马图卷》、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赵孟頫的《水仙图卷》。等等。只管访华之旅阅尽中国文物珍品,但大村落西崖与当时的许多来华人士有着巨大的不同。他的所有活动都是环绕学术研究和文化互换进行的。当他的一些同胞打着文化互换的幌子,充当“猎宝人”的角色,在各地古籍盗运石窟佛像时,大村落西崖只是对那些贰心仪已久的字画进行拍照记录,购买古籍图书作为资料,以为将来研究之用。
大村落西崖在北京与陈师曾相约共著《中国大美术史》,然而,由于陈师曾在翌年去世,这齐心专心愿未能克成。而在大村落西崖的家中,始终悬挂着亡友陈师曾写给他的一首诗:
“水面离人数寸余,白蘋花底看游鱼。田鸡跳掷靴纹皱,掀动芦根四五须。”
绝唱:塑壁残影
1926年,大村落西崖在日本收到来自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陈彬和信件,信函中向大村落西崖先容了北京大学历史学者顾颉刚在苏州水乡甪直创造的“古代剧迹”:保圣寺罗汉塑像:“寺建于梁(南朝梁天监二年),像制于唐(天宝年间)”。
可叹的是,目前由于古刹年久失落修,屋面塌坏。顾氏奔忙呼吁五年未见效果,遂于1923年12月分别在《小说月报》和《努力》周刊上揭橥《杨惠之的塑像》一文和有关照片,呼吁各界年夜方解囊,抢救古刹唐塑。”陈氏希望约请大村落西崖到中国实地稽核,并为文推介,推动抢修,使塑像得以存世。
大村落西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于1926年4月29日毅然前往中国,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中国稽核。5月2日,大村落西崖到达上海,在故人故友唐吉生的热心帮助下,与朋侪小林荣居、画友木村落杏园、拍照师一起顺利地到达甪直。寺门开启,天光透过屋顶洒在斑驳的罗汉塑像和海山塑壁上,千年之美,在历经岁月沧桑后,在这位万里蹈海的他乡来客的面前倏然绽放,不由得使他冲动不已:
“壁端山岩,树石,云水之配景,有关文献,殊足令余惊喜!
多年忖度之塑壁,今日始获亲睹,诚幸事也……良以塑壁之真代价,于今日之美术界中,尚未为人所认识故耳。今余乃于无意中得之,又安能不对之流连而不忍去乎?”
江苏甪直保圣寺塑壁海山罗汉像,大村落西崖末了稽核的文物。
就像每个人都会终极寻到他的出发点,或许在这一刻,大村落西崖也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从他儿时父母呢喃的佛经,家乡寺庙中斑驳褪色的佛像。东京美术学校里手执念珠,低吟佛号的雕刻老师,《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一帧帧来自中国各地的石窟造像照片和拓片。亡友陈师曾送给他的蕴含佛理禅机的诗句。
如今,他伫立凝望的海山塑壁之间形容怪奇、古趣妙生的罗汉。他是否会想起多年前,他身着中式长袍马褂,站在东京美术学校的大门口,阻拦那些身着巴黎奇装异服的学生的场景。如果每个人便是一具雕塑,那它末了会成为何种形象,须要用生平去雕塑。
“余以越世殊族,乃以学术之故,不惜以衰躯远渡瀛海,至此僻地,为日人涉足之开端,殊为惘然不能自已”,在稽核条记《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中,大村落西崖如此写道。他本已病体孱弱,而这趟苏州保圣寺稽核之行,成为了他末了的中国之旅。《塑壁残影》的写作险些耗尽了他末了的精力。1927年3月8日,他因肺癌去世。
那具名为“大村落西崖”的雕塑,终于刻完了末了一刀。
大村落西崖画像及署名
(本专题图片及图说均由大村落西崖《中国雕塑史》编著者赵省伟师长西席供应)
撰文|廖鹏
编辑|刘亚光 李永博
校正|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