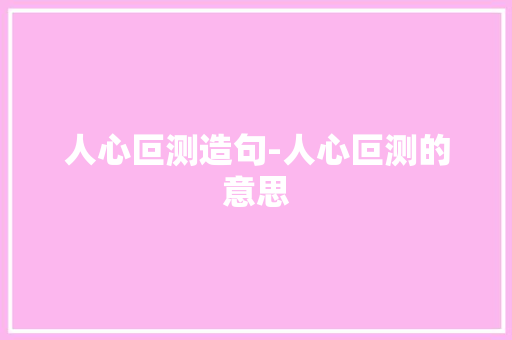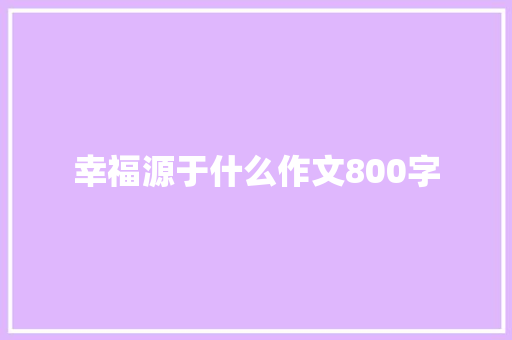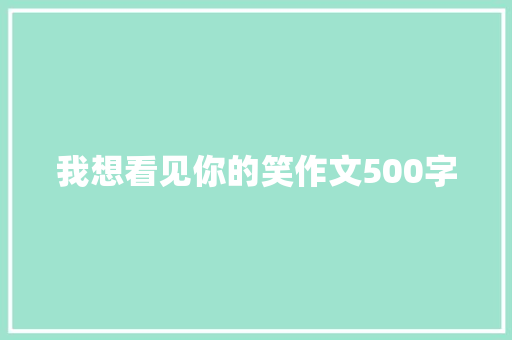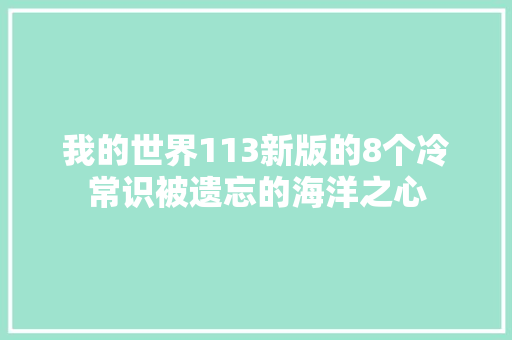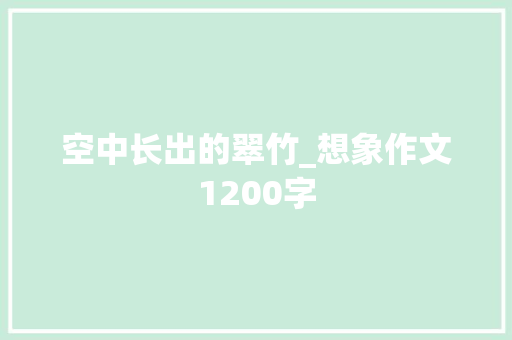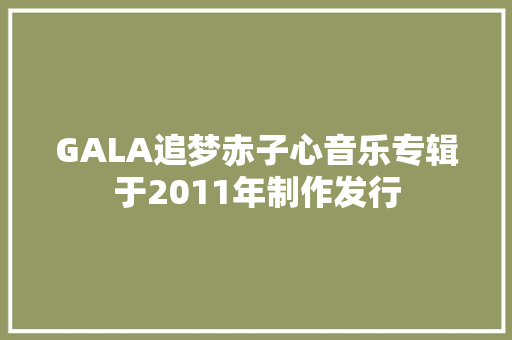“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表示了民众在政权稳定中的根本浸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心论则揭示出政权的来源和政治正当性的根据。这样的不雅观念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有着集中的阐发,老子则以“贤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开启了道家关于“民心”的独特思考。
“无常心”在帛书乙本和北大简中写作“恒无心”。“心”可生情欲,又有认知功能,“无心”便是老子所说的“无知无欲”;“无常心”则强调不受特定情欲、认知的支配。贤人之“无心”为“心”的空想状态,在《老子》中多种表达。第十六章有“致虚”“守静”,郭店简中“静”作“中”。“虚”“静”相对的用法在道家文本中涌现较晚,《老子》的原始文本可能为“中”。“虚”为“无所藏”,《管子·心术上》说“虚者,无藏也”,可解为无成见;“中”可解为中正、无偏私,北大简就写作“积正”。此外,第十九章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二十章描写了与俗人相对的“愚人”之心,“沌沌”,“昏昏”,“闷闷”,糊里糊涂、浑然无知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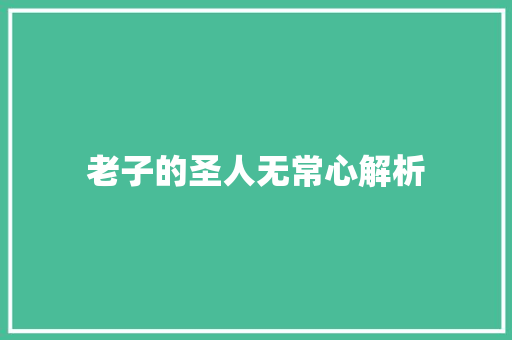
贤人无成见、无偏私,不会以出于一己之心的标准对百姓强为分别并对“百姓心”施以干涉和教养,“以百姓心为心”是对百姓之心的屈服和原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以善的标准去衡量,百姓有善有不善;以信的标准去衡量,百姓有信有不信;去除分别而同样地对待他们,正是“以百姓心为心”的表示。庄子对此有充分发挥。《齐物论》说:“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因此贤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贤人不屈服判别是非的认知办法而以“天”的视角不雅观照万物,去除了附加于物的、出于人的“成心”的是非判断。“因是”则肯定了千差万别的人、事、物的存在状态,是超于“是”和“非”的“是”,而不是与“非”相对的“是”。该篇“尧欲伐宗、脍、胥敖”寓言中的“旬日并出,万物皆照”可以说是“照之于天”的比喻。“万物皆照”所表示的正是所有物均应得到尊重、彼此平等的不雅观念,无论是什么面貌,都不会被否定,被放弃,被改变,被消灭。这个寓言的上文正是关于“辩”的谈论:“贤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贤人之“怀”是一种原谅,不去分别万物的是非、百姓的善恶,而众人之“辩”则一定要争出是非善恶。《齐物论》中啮缺追问王倪“物之所同是”,王倪否定了“同是”即适用于所有物的共同标准的存在。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规则制度便是“同是”的具象化。《应帝王》中反对“藏仁以要人”和“以己出经式义度”,便是反对君主将出自“成心”的“是”变成百姓均需遵守的“同是”,这是君主有“心”并哀求百姓“以君主心为心”。庄子所讴歌的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无容私”也便是“无常心”。
贤人“以百姓心为心”,而百姓之心可能涌现负面状况。《老子》第三章中有“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民心”会由于可欲之物的诱惑而混乱;第十二章说“驰骋野猎令民气发狂”,纵情佃猎会使民气发狂;第二十章中的俗人之心有“昭昭”“察察”的特点,聪明睿智、明察秋毫;第六十五章则将“民之难治”归因于民之“智多”。在老子看来,民心的狂、乱、多智源自君主的有“心”之治。君主分别物的贵贱,“贵难得之货”,“见可欲”之物,引发民众的贪欲;君主分别人的贤愚,“尚贤”,“以智治国”,导致民众争名夺誉、尔虞我诈。就像《庄子·应帝王》中去世去的浑沌。倏和忽认可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食息,于是为浑沌凿开七窍而导致浑沌去世亡;君主的管理行为,让百姓开启了心智,产生了希望,民气的淳厚状态就这样被毁坏。《庄子·天运》中批评黄帝、尧、舜、禹管理天下,使民心发生了“一”“亲”“竞”“变”的变革。“一”指不别亲疏远近而同样待人;“亲”是有偏私的相亲相爱;“竞”指相互争胜,“变”指变革难测。民心之“一”“亲”“竞”“变”离无知无欲的素朴状态越来越远。
儒家主见以仁义礼乐教养民心,这成为道家批评的重点。《庄子·骈拇》讲:“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落其常然也。”这里的“常然”指民气的本来状态。君主用仁、义、礼、乐来安慰民气,是对民气本来状态的侵害。分别来说,仁义是对民气的哀求,礼乐是对行为的约束,《马蹄》中表达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在宥》中,面对“不治天下,安藏民气”的质疑,老聃提出不要“撄民气”。“藏”为“臧”字之讹,善之义,“撄”为扰乱。这是将使民气向善的管理行为看为难刁难民气的扰乱。老聃批评黄帝 “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导致天下大乱,“治天下”的罪过就在于扰乱了民气。
“以百姓心为心”并不虞味着纵容百姓希望的膨胀和智巧的发展。《老子》第四十九章接着讲:“贤人活着界歙歙,为天下浑其心。贤人皆孩之。”“歙歙”,王弼注:“心无所主也。”“歙歙”便是“无常心”;“浑其心”意为使百姓之心归于淳厚,也便是第二十八章的“复归于朴”;“孩之”便是使百姓之心“复归于婴儿”。贤人可以使狂、乱、多智的百姓之心复归婴儿的素朴状态。第六十五章讲:“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里的“愚”与“智多”相对而言,是淳厚、无诈伪之义,“愚之”便是让百姓拥有“愚人之心”。第三十七章指出,面对万物(百姓)的“化而欲作”,侯王应“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指“道”。侯王以“道”安定百姓之欲,使百姓之心复归无欲。百姓有欲则争,争则乱,无欲则静,静则天下自然安定,这便是“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章的“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更为详细,可以“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实现“虚其心”“弱其志”“无知无欲”的效果。“浑其心”“孩之”“愚之”“镇之”,“虚其心”,“弱其志”,以及“使”的反复利用,都表示出君主权力对百姓之心的浸染,这彷佛与第五十章“我无欲而民自朴”中的“自朴”不合。实际上,这种浸染是为民心复归其本来状态供应条件,不是让百姓服从于君主个人的意志,也不是对民心的扰乱,这属于“辅万物之自然”(第六十四章)。
《老子》中亦有关于如何“得天下”的思考。“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第二十九章),“取天下常以无事”(第四十八章),“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取天下”即“得天下”。老子认为,通过“无为”“无事”,不干涉、不扰攘,可以“得天下”。此外,第七十八章讲“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第六十六章以“江海”和“百谷”为喻,江海处下,万流汇聚,而成为“百谷王”,贤人面对百姓,“以言下之”,“以身后之”,使得“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从而实现了“天下乐推而不厌”的效果。屈辱、祸难、下位为“众人之所恶”(第八章),贤人却选择承受屈辱、祸难,选择居下、处后,使百姓感想熏染不到上位者所带来的压迫和侵害,因而得到百姓的至心拥护,取得天下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权。可见,复归素朴的百姓之心,仍旧有“乐”有“恶”。他们期望过上“食甘”“服美”“居安”“俗乐”的美好、清闲的生活而不期望承受压迫、祸难和侵害。这也是关于如何“得民心”的思考,也是“得民心”能“得天下”的思路。与“无为”“无事”能“得天下”相反,《老子》第二十九章和第六十四章讲“为者败之,执者失落之”。“为”是对百姓的干涉,“执”因此强力掌握。如果以强力去干涉、掌握百姓,扰乱百姓之心,会导致天下大乱,也会由于给百姓带来其不愿承受的压迫、侵害而失落逝世界,这是道家意义上的“失落民心者失落天下”。
老子所提出的“贤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和庄子对“物之所同是”的否定,表示出道家对民心不干涉、不逼迫的政治原则,是否遵守这一原则成为“得天下”和“失落天下”的关键。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3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