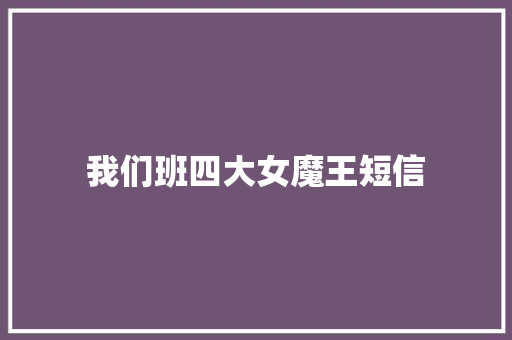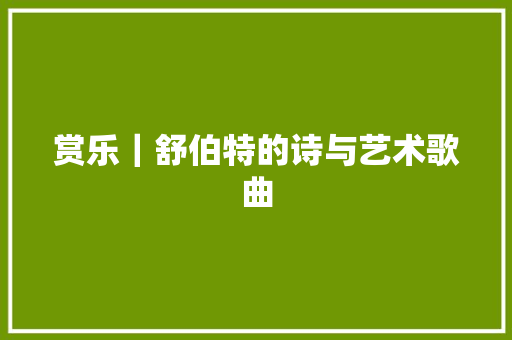——歌曲《魔王》创作背景及音乐剖析
旭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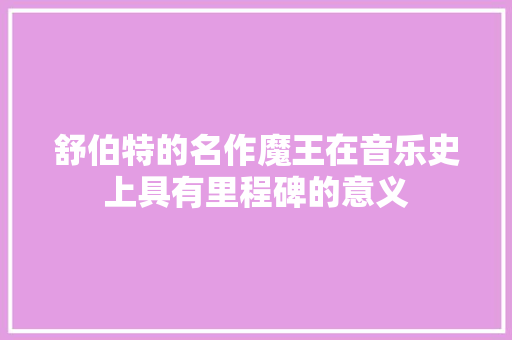
弗朗兹.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德奥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第一人,有人给予他以艺术歌曲之父的崇高名誉。舒伯特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西席家庭,从小在一所投止学校上学,他参加学校的合唱团,担当乐队演奏员和指挥,他的音乐学习很多来自于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经历。
舒伯特
舒伯特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写下了在本日看来是划时期的作品,他17岁写成歌曲《纺车旁的玛格丽特》,一年后,即1815年完成的名作《魔王》,在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创作背景
1.歌词来源
《魔王》歌词的原诗作者是歌德,原诗是作者于1781年创作的一首叙事谣曲。1781年,歌德在图林根地区旅行时,住在一家叫“枞树”的旅社里,听人们饭后闲谈时讲到附近村落庄里前几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库尼茨村落的一位村落民,由于孩子病重,夜里骑马抱孩子赶到城里去找年夜夫看病,途中要穿过一大片树林。由于孩子已病入膏肓,在归来的路上,还没到家,孩子已经去世在怀抱中。歌德听说了这件事,遐想起民间传说中的妖怪夜里勾魂抢孩子的故事,妖怪只要碰一下孩子,便摄去魂魄,孩子也就去世去。把道听途说的生活事宜与民间传说结合,很能知足他对民间谣曲的兴趣,便写了《魔王》用在他的叙事歌剧《渔妇》中。叙事谣曲是一种很自由的艺术形式,它可以从客不雅观陈述转入戏剧性的演出,叙事性和戏剧性里又不排斥作者的主不雅观抒怀,叙事内容既可以是现实的,又可以是抱负虚构的。如此之下,叙事谣曲里现实的、抱负的、戏剧的、抒怀的交织在一起,供应给艺术家一个宽阔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创作空间,可以容纳下极为繁芜多变的抒怀需求,这些特点使浪漫主义艺术家着迷,由于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束缚他们的艺术想像,于是叙事曲就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常采取的形式。
歌德
2.角色塑造
舒伯特用音乐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触目惊心。歌曲虽然具有很强的戏剧性,但却有统一的构造和完美的形式,叙说与行动合营的十分贴切适当。情节的变革是通过戏剧性的发展而表达出来的,因此他的音乐和歌词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音乐总是牢牢地跟随着歌词的发展而作相应的变革。舒伯特把故事阐述者、父亲、孩子、魔王四个不同角色分别予以独到的塑造,笔调细腻,旋律奇妙。四个角色力度层次明晰:魔王的威胁、凶险、狡诈,父亲的慈爱、无助,孩子的胆怯、可怜,阐述者的无奈、同情。孩子的每一声呼喊仿佛都在我们耳边,父亲的每一次强作沉着都在引起我们心里的不安,魔王每一次的诱惑都让我们感到惶恐和痛恨。孤独的父亲既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又要降服心中的恐怖。他柔声地讯问和安慰着孩子,试图解除他的恐怖,然而他也意识到了魔王的存在,当他做后一次对孩子说“那只是老杨柳树”的时候,自己也深切地感想熏染到了魔王的恐怖,于是加紧策马。此时已经极度虚弱的儿子连续三次惊骇的发出求援,花费了身体末了全部的精力,音乐一步步推向紧张和危险(音区更高、力度更大)。然而这一次次求救得不到真正的救赎,孩子在呼救中浑身逐渐瘫痪,生命的挣扎力逐渐衰退(力度变弱)。魔王的诱惑更加肆无忌惮,把自己渲染成了一个幸福的青鸟使,将魔爪隐蔽了起来,音乐的旋律非常抒怀,它讲述着它的能歌善舞的女儿,华美堂皇的宫殿。这样,阐述者、父亲、儿子、魔王四个角色共同上演了一曲扣民气弦的艺术之旅。
二、音乐剖析
1.歌曲概述
《魔王》这首随处颂扬的叙事曲采取通体歌的形式创作而成,全曲共 148 小节,4/4 拍,分为八段,每段四句歌词,共 32 句歌词,每两段歌曲之间用较为短小的钢琴伴奏隔开。全曲采取自由贯通的创作手腕,其旋律曲调依照歌词中人物性情的不同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展开,在这首作品中,舒伯特以他天才的创造力授予诗歌生动的音乐形象和高度的戏剧性表现力,使之具有极其渲染力的伟大气势。此歌曲中塑造了五个音乐形象,分别是钢琴伴奏所刻画的动态场景和演唱者扮演的阐述者、父亲、孩子以及魔王四个角色形象。这五个音乐音响相互交织、交替的涌现,使这首歌曲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在《魔王》148小节的贯穿发展过程里,几个不同人物的不同角度所表现出来的心情和语气,通过调性的比拟转换,织体、力度和旋律线条的变革被生动地表达出来。魔王的诱惑(大调性、平缓),孩子的呼救与父亲的紧张不安(小调性、急匆匆并一直地转调),阐述者宣叙性的腔调,以及钢琴自始自终地奔跑,以定型化织体、戛然而止及末了的两个特强和弦,与歌者共同营造出紧张阴森的情境和气氛。
2.人物形象
①阐述者
阐述者在作品中共涌现两次,第一次是在作品 16—32 小节中,阐述者的旋律紧张因此二度音程在主调 f 小调上平稳的向前发展,钢琴伴奏部分较之前奏部分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革,仿佛以一种平稳的语气在向听者阐述故事发生的韶光、地点、场景及紧张人物等。 作品中第 22—27 小节,由主调 f 小调转至关系大调(降 A)上,舒伯特以大调调性通亮的音响效果来作为第一段的结束,是为了能更好地刻画出一种温暖的父子之情。第二次是在作品 133—148 小节中,阐述者的旋律虽然仍以二度音程在 f 小调上连续平稳的发展,仿佛是在以渐强的速率和力量来描述父亲此时错愕、颤栗的恐怖之心,以及儿子病情的加剧和精神的崩溃,同时也表达了阐述者对父子二人的同情与关怀和对魔王低劣行为的痛恨与厌恶。在歌曲的结束部分(146—148 小节),作者在旋律部分以小二度的暗淡、忧伤与不协和等特性办理到主和弦上来作为整首歌曲的结束,而伴奏部分作者则以重属导七和弦进行到属七和弦再办理到主和弦上,给我们一种完备终止的觉得,彷佛是在暗示阐述者对付父子二人惨痛遭遇的一种悲哀和无奈,留给听众的则是无限的悲痛与愤怒、同情与怜悯。
②父亲
表现父亲的旋律腔调在作品中共涌现四次,它的特点是沉着、寓于神色。音域在声部中低音区,腔调也较平稳,刻画父亲的关怀、抚慰与慈爱,非常恰当地表示出父亲的年事和性情特色。在第一次父亲对孩子的问话中(36—40 小节), 作者以连续的半音上行以及从第 40 小节由主调 f 小调转至其下属 降b 小调(增长其惨淡的色彩),以此来渲染父亲错愕程度的逐步加深,也同时展示出了父亲对儿子的关心和爱护。父亲对儿子提问的第一次回答 (51—54小节), 作曲家利用了持续稳定的主和弦进行连续的发展,并由此展现父亲刚毅、稳定的性情,并采取坚实平稳的回答来达到肃清孩子紧张害怕生理的目的。当儿子因第一次受到魔王领导而表现出来的恐怖生理时,父亲的表现已不像之前那样沉着与自傲了( 80—85 小节),作者以a 小调的和弦进行, 并在 81 小节 处 涌现了一个 a 小调 IV 级上的属七和弦, 以此来展示父亲略显紧张、发急的生理。 但父亲紧张的生理并没有持续发展,作者在连续 4 小节转入 a 小调的和弦之后,随之又转回到主调 f 小调上,以此来展示,此时的父亲虽略有些担心,但他立时顾虑到病中的儿子的感想熏染时,旋即又以沉稳的语气来回答并安慰儿子紧张的生理。在父亲的旋律腔调第三次涌现的时候(105—112 小节),作品上涌现了两次转调 ,作者首先从儿子唱段的 g 小调转至到 b 小调上,持续 3 个小节往后又转入到 c 小调上,父亲旋律调性的小二度上行与儿子刻画魔王形象旋律的半音(小二度)上行在此处形成前后呼应,形象地刻画出父子二人的内心同时都流露出不安与胆怯的生理,虽然父亲旋律声部依然连续采取比较平稳的和声进行来发展,但这更能逼真地刻画出此时的父亲正极力掩饰笼罩心中“不安”的感情,尽力安慰孩子。第四次旋律腔调的调性很不稳定。虽然仍采取刚毅、沉稳的语气来回答孩子的问话,并希望以此来打消孩子的恐怖生理,但较之前两次,父亲此时的发急与惶恐生理却更为加深。表现父亲心里很紧张,但还是用武断的语气见告孩子那些都是他的幻觉。
③孩子
孩子的旋律腔调相比拟较高,在作品中共涌现四次,舒伯特采取同一旋律在不同的调上,模拟进行的手腕,以二度音程不协和的特性和频繁涌现的六度大跳来表现孩子看到魔王的幻影时所感到的错愕和不安与恐怖和颤栗的生理,虽然作者在孩子第一次回答及后面三次涌现的惊骇与呼喊中所用的音型、节奏及旋律走向大体相同, 但作者却多次利用了转调手腕,使孩子的波折衷音高每一次都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因孩子感情恐怖度的加深而升高。作者采取从孩子口中描述魔王及其女儿形象进行创作,在第一次描述中 (41—50 小节),作者在强拍上利用了降 A 大调的重属导七和弦,而在孩子旋律的走向方面作者也采取了旋律下行的手腕,重属导七和弦的不协和性和旋律下行的暗淡色彩,第一次从孩子的口中,急速就为我们生动地描述出一个头戴雉尾皇冠的“邪恶”魔王来。
在后面两次的描述之中 (72—79 小节,97—104 小节),作者均利用了半音进行的手腕,同时也都在旋律与伴奏低音部分利用了连续的平行小三度对位手腕,此两处都强调了用横向的旋律线条来刻画孩子对魔王“邪恶”的描述,与第一次以降 A 大调重属导七和弦纵向不协和的音响效果形成了光鲜的比拟,这同时也解释了孩子对魔王邪恶的“恐怖”生理正逐步加深。当孩子在魔王的威胁、威吓之下所发出的末了一次惊呼时(123—131 小节),作者以全曲中的最高音(小字二组 f)以及小二度音程极不协和的特性进行,来展示孩子此时的极度惶恐与绝望,从而把全体故事情节的抵牾冲突推到了极致。对孩子的末了一次“惊呼”, 作者的创作手腕是把该段的调性回归至整部作品的主调 f 小调上,舒伯特采取这种调性变革,旋律逐渐移高的作曲手腕,很好地刻画孩子惊骇加剧,一次比一次强烈的音乐形象。同时作者利用纯挚的和声进行来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孩子”在去世亡和恶势力面前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充分解释了代表阴郁社会及恶势力的“魔王”力量的强大。
④魔王
魔王作为邪恶、 惨淡势力的一方,其音乐旋律是抒怀歌唱性的。表面上显得甜蜜,但骨子里却隐蔽着巧诈、虚假、狰狞、刁滑。旋律腔调在作品中共涌现三次,凶恶、狡猾的魔王每一次都用卑鄙、可耻的伎俩领导精神恍惚且处于病中的孩子,作者在塑造魔王的音乐形象时多采取比较平稳的旋律走向,且多以欢畅、柔柔的节奏和力度来展示魔王的凶险与刁滑,由于魔王前两次涌现的旋律、力度及转调手腕较为附近,与第三次的涌现差别较大。
对付魔王在作品中的前两次涌现(57—71 小节,86—96 小节),作者以极弱的力度(ppp)来塑造魔王领导孩子的狡猾伎俩,调式调性的变革不大,转调手腕都是主调上的近关系调。第一次所利用的转调,是在主调 f 小调上转调进行到平行大调(降 A)上,而在第二次魔王涌现的时候作者却利用了 f 小调的下属大调(降 B),只管这两个调都属于 f 小调的近关系调,但对付音响上的效果来说,平行小调毕竟还是比下属大调要更自然一些。在第 87 小节处,作曲家再一次利用半音进行来塑造魔王那种“不怀美意”的假惺惺,同时也塑造出魔王因第一次领导不成而所涌现的发急心情。此外,钢琴伴奏部分在魔王第二次涌现的时候(第86—96 小节)涌现了较大的变革, 作者利用了降 B 大调主和弦上的分解和弦,且在音乐连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作者一贯都在利用非常平稳的主属和弦的连续交叉进行,较第一次涌现时的伴奏部分显得更为的轻盈与平稳,仿佛是在见告我们,魔王因第一次领导的失落败而对孩子所采纳的一种更为柔柔、鬼魅般的迷惑与领导。
在魔王第三次涌现的时候(116—123 小节 ),作者利用的是主调 f 小调的上属 c 小调。旋律腔调和前两次比较,已不是那么抒怀柔和了,而且力度也加强了。彻底暴露出了魔王狰狞霸道的实质。
末了第八段,阐述者又出场,并用发急沉痛的腔调描述了可悲的结局:“虽然父亲不遗余力策马赶回家,但怀里的孩子还是去世去了”。 钢琴以两个特强和弦,表现了精疲力竭的父亲悲痛。
3.曲式构造
《魔王》的构造,按照歌词及与之相适应的曲调、伴奏可分为八个段落。第一段涌现的是阐述者对故事开场的交代,舒伯特利用的旋律宛如彷佛口语化的朗诵腔调,节奏紧张。表示出阐述者较客不雅观的一壁。第二段起至第七段则是表现父亲、孩子和魔王的对话,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三种不同的生理活动。舒伯特在设计这三个人物的音乐形象上,利用的音乐材料在旋律上的力度、节奏,各个人物之间都有光鲜的比拟。
三、创作特点
1.旋律
《魔王》是一首戏剧性、艺术性很强的叙事歌曲,它属于范例的通体歌。在前奏曲中就涌如今同音上的三连音(表现疾奔的马蹄声),这时隐时现、时弱时强的三连音除了具有描述的写实浸染外,也是造成局促不安生理的主要成分,低声部的问息乐句则暗示时时掠过的林间阴风。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为了使音乐紧密合营歌词的发展,舒伯特将《魔王》中四个角色配上了性情光鲜的旋律,用不同音区与音色加以陈述。人声和器乐伴奏达到完美的结合,丰富的音乐形象和完美的变革手腕风雅地刻画出不同人物的性情特色与故事发展的情节,歌词里的诗性成分溶解成纯音乐成分,人声和钢琴共同达到一个艺术境界,诗与音乐之间成为均衡关系,音乐的表现力和文学向音乐的渗透都得到了保护。实现了诗乐十全十美的艺术效果。
2.伴奏
这首《魔王》由钢琴伴奏,一开始的前奏以快速的八度音群描写奔跑的马蹄,由低到高的一串三连音之后,又在小调的主和弦上作下行断奏,把这首曲子的精神表现到了极致。伴奏在这里不仅仅是伴奏而已,它渲染了曲子深奥深厚端庄、紧张焦虑,或是恐怖、温和等各类感情。舒伯特在《魔王》里将钢琴伴奏与歌唱旋律并入同等主要的位置,极大地提升了钢琴伴奏的艺术地位,使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浸染,成为全体声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不再是对歌唱旋律的大略附和,而是通过写意、造型、描述等手腕渲染作品的氛围,陪衬意境。通过织体的造型塑造完美的音乐形象,从而与旋律融和,共同揭示诗歌的意境,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境界。
(二胡谱)
3.腔调
曲中四个角色——阐述者、父亲、孩子、魔王,由同一人担当,而以不同的音色来诠释。
舒伯特对音乐措辞的博识利用和高超的创作技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他采取较为轻盈的节奏并减少力度,以突出魔王的巧诈,营造出紧张阴森的情景和气氛。
4.动机
《魔王》原诗讲的是一位父亲怀抱发着高烧的孩子骑马穿过黑夜的森林,孩子因瞥见森林中的魔王在反复领导他而不断发出惊呼,末了终于被魔王攫取生命的故事。由于歌德的原诗是按照第三人称写作,按文体分属于叙事性诗歌,以是在歌词中我们能够看到四个不同的人:阐述者、父亲、孩子和魔王。舒伯特为了表现这四种人也利用了四种不同的动机。个中表现“魔王”是最为丰满的。“魔王”在歌曲中涌现了三次,第一次和末了一次的动机旋律险些是一样的。“魔王”出场的时候总有一个大二度的上行,然后有一个四分符点,下行纯四度这样反复两遍,由于演唱时的难度,舒伯特为了合营此处“魔王”措辞中频繁涌现的闭口音节而把音高掌握在f2以内。
5.角色
在舒伯特《魔王》中,除了首尾的旁白,全都用对话来表现。父亲、孩子、魔王这三个角色(加上阐述者共四个角色)都有各自的力度层次,父亲总是柔声地讯问和安慰着孩子,试图解除他的恐怖,然而他末了一次对孩子说“那只是老杨柳树”的时候,他自己也为无名的恐怖所裹挟,而加紧策马奔驰(这里的伴奏极富效果)。已经极度虚弱的孩子三次惊骇地求援都是用了全副精力,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声嘶力竭(音区更高、力度更大),可是每次都是话未说完就浑身瘫软、力不从心了(力度变弱)。魔王因此甜言密语诱拐孩子,也没有张牙舞爪的声势。它的旋律是抒怀性的,当它说到会唱歌舞蹈的女儿时,把声音放得更柔柔。
四、综合评价
《魔王》全曲以德国墨客歌德的同名叙事诗为词,通过不同的旋律腔调,配上不同的唱腔,以及钢琴模拟持续不断的急驰马蹄声和呼啸魔的风声的三连音,表现了叙事诗里父亲、孩子、魔王以及阐述者四个性情互异的人物和特定的环境。《魔王》整部作品形式自由,富于抒怀性,刻画细腻而逼真,不仅在文学诗词与音乐之间展现了一种承载的浸染,并且用诗与歌共同抒发感情,刻画人物内心,通过诗、乐的高度领悟,给予不雅观浩瀚层面的艺术享受。
通过对《魔王》的剖析,可以看到浪漫乐派代表人物舒伯特把古典期间只处于从属地位的钢琴伴奏,无论在写法上还是音乐语汇上都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一个重大的打破,使歌曲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这首歌曲虽然是自由发展,但保持了却构的统一和形式的完美,是一首戏剧性、艺术性很强的叙事歌曲。
舒伯特的生平是为音乐而生的,可以说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音乐奇迹。在舒伯特短暂的生平中,他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他惊人的灵感和高超的作曲技巧任他创作,而《魔王》是艺术歌曲中公认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