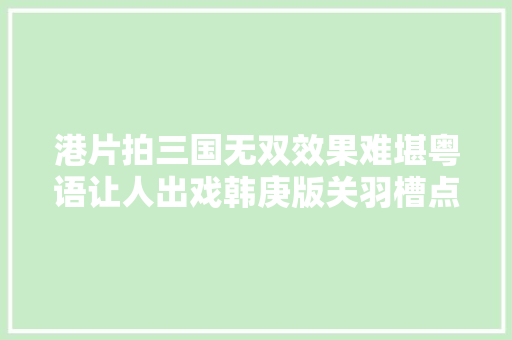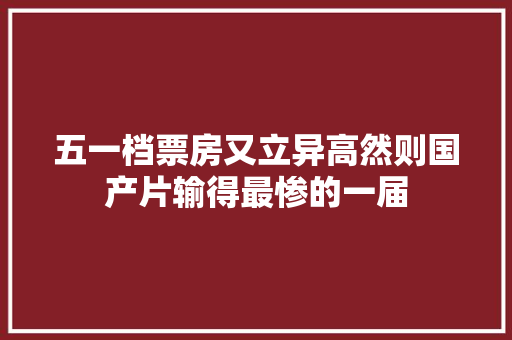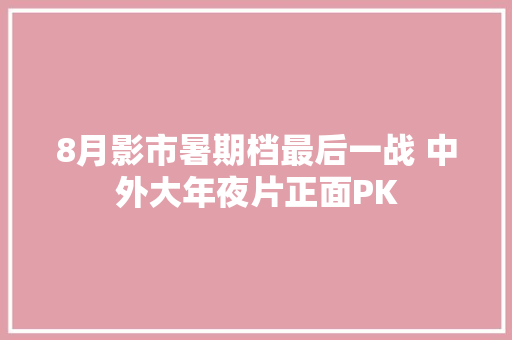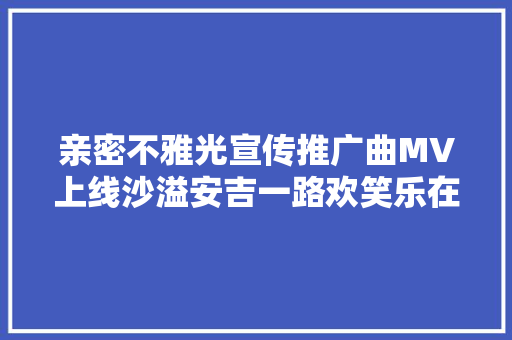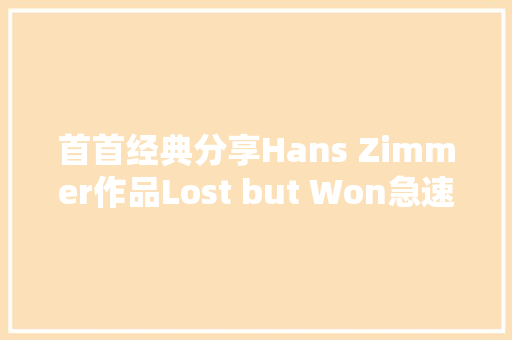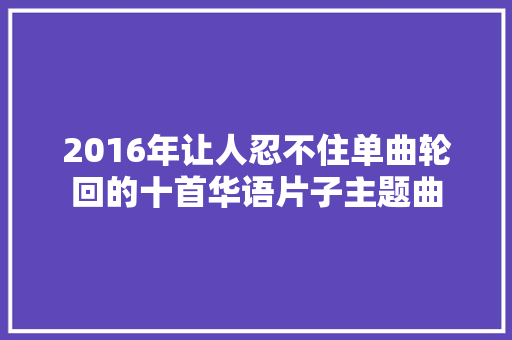然而,正是被誉为“新浪潮祖母”的她,却长期被法国电影圈打消在外。作为电影制片人,瓦尔达曾公开表示:“大家都爱我,但没人想要我。”在边缘人的位置,她生平都在探求并切近亲近她视野范围中“好作品”的那道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是瓦尔达眼中的“好作品”?她如何看待电影中光影、情绪乃至于谎话这些核心议题?以及回望来时路,她又会如何界定自己与“新浪潮”的关系?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中“没人想要我”一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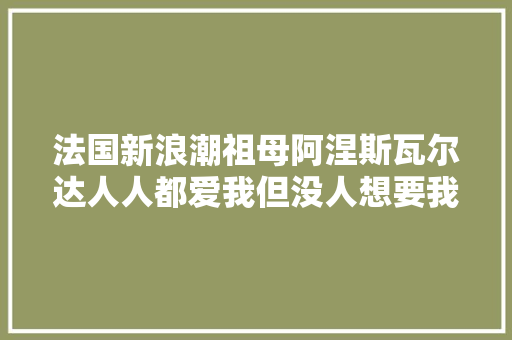
《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美] T.杰斐逊·克兰 编,曲晓蕊 译,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7月。
“我才不拍摄‘常规电影’”
A & J:自从《短岬村落》之后,您彷佛就有了自己制作电影的意愿或欲望。
瓦尔达:这是出于意愿或欲望吗?不,这是一种一定须要。当“他们”不想制作我的作品,或者当项目看起来很难完成时,我就成了制片人。毕竟谁会乐意制作、投资或努力完成一部——比如《墙的呢喃》,关于洛杉矶的墙的电影?或者《记录说谎家》,关于笔墨、流放和痛楚的电影?这些项目本身都困难重重。因此,我自己动手,制作自己的作品。我想起曾经在一家中餐馆吃过的幸运饼干,上面写着:“当你须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乞助于自己的双手。”这便是我成为制片人的缘故原由,这样才不用放弃我的项目。
1954年拍《短岬村落》时,没有谁对我有信心。我还自己掏钱拍了《穆府歌剧》。之后,我的作品开始有制片人了,如《五至七时的克莱奥》的乔治·博勒加尔,《幸福》和《创造物》的玛格·博达尔(Mag Bodard)。这就像一场梦,我所要做的事情便是导演。与《狮之爱》的联合制片人马克斯·拉布互助时,情形就没那么顺利了;他筹集到了资金,而我则卖力管理……那是在 1969年。在那之后,除了我自己,我再也没有请过其他任何制片人,不论男女。但我不想连续这样下去了。自己制作电影太累了。我摧残浪费蹂躏了太多精力,本来可以把这些精力更好地用在电影上。此外,制片人是一个糟糕的角色。你终极会成为一个糟糕的老板——并不总是如此,但毕竟……我在制作《达盖尔街风情》《一个唱,一个不唱》《墙的呢喃》和《记录说谎家》时感到精疲力竭,更别提为雅克和日本人制作《凡尔赛玫瑰》(Lady Oscar)了。够了,我不准备再做电影制片人了。或许不如彻底放弃拍电影。
电影《短岬村落》(1955)剧照。
A & J:真的吗?您不准备再拍电影了?
瓦尔达:我不知道,但我须要帮助。我想拿钱做我最善于的事,那便是编剧和导演。我借着同时成为片场的店主和(无偿)雇员来粉饰我失落业的事实。经历了十年或十二年这种拙劣伪装的赋闲状况后,我已经受够了!
我并不是说自己拍不了电影……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为制片事情投入的精力都粉饰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没有人以法国电影家当的常规办法对我的作品表示过信赖。如果必须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制作实验性电影,那么我们终极将失落去这个“文化标签”,它曾在其他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故意思的是,我想到了克莱奥,俏丽的克莱奥,她说“大家都想要我,但没有人爱我”。作为电影制作人,我也可以说“大家都爱我,但没人想要我”!
我不介意像往常一样演出绝技似的完成电影制作,想办法让十五个临时演员看起来像有二十个,但我不想再去筹钱来支付这十五个临时演员的人为;筹钱支付拍摄这十五个临时演员的技能职员的人为;筹钱请司帐,让他给这十五个临时演员和十五个技能职员开人为条;找车把这三十个人运到片场,末了再想办法让这十五个临时演员看起来像是二十个或二十五个。这已经不但是走钢丝了,这是在上面跳八三拍的帽子舞!
记得拍《一个唱,一个不唱》时,我在两个镜头之间跑到梧桐树下的电话亭给法国国家电影中央打电话,讯问预支用度能不能批准和支付……我很光彩能拿到预支款,没有这笔“嫁妆”,我切实其实无法想象这部电影能等到在电影院大厅里放映的一天。
《墙的呢喃》起初还算顺利。文化部预支了一部分款项;电视二台和克莱斯·黑尔维希(Klais Hellwig)也供应了一些资金……但电影从短片变成了长片,预算却没有增加。差额只能由我来补足。
至于长片《记录说谎家》,情形完备不同。我只能从法国国家电影中央那里得到一小笔帮助,这部电影险些没有赚到钱。因此,我终极欠下了一些债务。不过并没有拖欠技能职员,没有迟发或减少他们的人为,每个人都领到了酬劳。我仍旧须要偿还电影工业和其他组织借给我的所有款项,好在可以分期偿还。电影工业……您知道,在洛杉矶,人们会问:“您也是业内人士吗?”彷佛工业指的便是电影业这一点不言而喻。我总是回答:“不完备是,我是艺术家型的电影制作人。”我试图规复“艺术家”和“工匠”这两个词的含义,在“第七艺术”中,他们制作的并不是大型电影(major motion pictures),而是影片(films),它也是电影的一部分。“我拍电影,不做生意。”
电影《记录说谎家》(1981)剧照。
我最受不了听贩子们说“电影无非便是和刺激或者恐怖等干系”。他们常日还会说:“电影不是某些可悲的精英分子的思想理论……”他们大言不惭地定义电影是什么……他们怎么便是弄不明白电影包括各种类型、各种风格呢?我只是在重申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怎么重申都没有用。正是由于这些荒诞的辞吐,我才不与常规的制片人互助拍摄“常规”电影。
我梦想与马塞尔·贝尔贝(Marcel Berbert)这样的人互助,他为特吕弗不遗余力。作为回馈,特吕弗让他涌如今自己所有的电影中。贝尔贝的客串就像希区柯克在他自己电影中的客串一样隐秘而低调。我很乐意在我所有的电影中为一位负责可靠的制片经理供应客串机会!
A & J:在职业生涯当前的阶段,您处于什么状态?
瓦尔达:无力运转了。不是没有灵感,而是没有勇气,哪怕我以为自己最近拍了一些好作品,取得了进步。不过《墙的呢喃》不算,它还是以相称范例的手腕拍摄的……对我自己而言范例的手腕——记录式、个人化。我花韶光真正谛听人们的心声,思考问题,享受个中的乐趣。我所评论辩论的不是别人眼中的“好作品”。现在有很多电影艺术家以各种不同的办法制作出了还算不错的作品。
对我来说,“好作品”有其他的含义,指的是凭借想象力重塑固有的东西和刻板印象。当思维真正打开,自由发挥遐想时,当我开始用纯粹的电影词汇写作时,这便是“好作品”。电影写作,可以这么说吗?图像和声音之间新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呈现之前被压抑或隐蔽在内心深处的画面和声音……用所有这些再加上情绪来制作电影,这便是我所说的“好作品”。在创作《记录说谎家》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随着作品在进步。我一贯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项未完成的作品,而不太在意奇迹的发展。我拍过一些电影,也喜好拍电影,但我的电影并没有像其他电影那样取得那么大的进展。
A & J:您有没有哪部尚未拍摄的电影尚有机会成为令人愉快的作品?
瓦尔达:当然!
我写了几个剧本,至今仍未拍摄,或者说不会拍了,包括 1960年的《殽杂》和 1980年的《玛丽亚与裸男》。我希望能与特蕾莎·拉塞尔(Theresa Russel)互助拍摄前者,我以为她非常出色。她曾出演尼古拉斯·罗格(Nicolas Roeg)的《坏机遇》(Bad Timing),法文名为《激情调查》(Enquête sur une Passion)。还有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我非常欣赏她的才华,还有她的嗓音。我还得找一个美国人扮演被警察打去世的裸体男子……不管怎么说,拍摄操持还在,我还没有放弃这个项目。
A & J:《圣诞颂歌》呢?
瓦尔达:我在 1966年还是 1967年拍摄了十分钟的素材,当时也是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首次亮相……那本来是一部有关 1968年之前的年轻人的影片,但我没有重新艺国际电影公司(CIC)拿到预支款,发行商放弃了,我也放弃了,然后就去了美国。该放手时就得放手。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雅克一起去看普雷韦(Jacques Prévert)。他对我们说了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每一个当选中、付费并拍摄的剧本,背后至少都有两部有着完全对白的作品,在完成后无人问津……想想写一个剧本须要花的韶光吧!
我花了五个月的韶光来写《玛丽亚与裸男》。我和一位美国编剧互助,自己先写了三十页旁边的手稿。我须要别人帮我用英语写作,用创造性的措辞……我们每天都不间断地事情,周六上午也不安歇。幸好末了拿到了报酬。此外,我也喜好一有想法就付诸拍摄,尤其是记录片。《达盖尔街风情》和《扬科叔叔》都是如此。受到冲击、引发情绪、构思构造,然后就开始拍摄。我也喜好这样。至于《扬科叔叔》,我在一个周四见到了他,扬科叔叔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们周六、周日和周持续着拍了三天。就这样结束了!
全体拍摄过程中我情绪上都很投入,也很愉快。我在创作的阵痛中拍摄了这部电影。
电影本身的韶光、情绪与谎话
A & J:这让我们想到您与景象和韶光(均为le temps)的联结。您能谈谈吗?
瓦尔达:我很乐意聊聊,当然,我更喜好在阴天拍摄彩色画面,在晴朗景象中生活……不过,您的问题也涉及 “temps”的另一层含义,即不断流逝的韶光,我喜好生活中那些觉得不到韶光流逝的时候。韶光是流动的。孩子会终年夜,树会长高,这让我感到惊奇。有一天,戈达尔来到我们在达盖尔街的住处,来看罗莎莉,她正在用真的羽毛做一些巨大的天使翅膀,准备将它们用在戈达尔的电影《激情》(Passion)当中。当看到戈达尔和罗莎莉时,我笑了。二十年前,戈达尔和我在同一栋屋子里相识,当时罗莎莉只有三岁,总在我脚下打转。我创造很难在电影中捕捉这样的光阴,虽然已经由去了二十年,但我们并不以为现在的自己与当时有多大的不同。
在电影中,为了真实可信,我们必须利用扮装等手段来表示韶光的流逝……在内心深处,我们并不以为自己在朽迈。我们不是生活在镜子前,也无法从外部感知我们的现实。我们知道这一点,却很少真正意识到它。在电影中,让我着迷的是电影本身的韶光,电影拍摄的韶光,有关韶光本身和它突如其来的密度。我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表现了这一点:韶光在何时溘然凝固,又在何时重新开始自由流动。韶光就像血液循环,或者像在《记录说谎家》中,韶光被抽空,分开本色,变成了纯粹的空间:海滩,或是两栋迷宫式建筑之间的过道。
电影《记录说谎家》(1981)剧照。
我最近在南锡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是雪莉的女儿温迪·克拉克(Windy Clarke)做的。她在南锡戏剧节主帐篷里搭了一个小屋,在这里制作和放映她的“爱的录像带”。大约五年前,她开始制作一部有关集体治疗小组的影片。参与者拍摄自己,也拍摄对方,影像通过房间四周的屏幕播放出来,这样他们就能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描述自己和对方。大略地说,全体过程有些沉重。但是在这之后,她有了一个新的方案:请每位参与者用三分钟韶光谈谈爱。她已经网络了大约七百分钟这样的证言。小屋的四周安装了屏幕,上面用法语和英语播放着这七百分钟的“爱的录像带”。如果有人想试试,就可以进入小屋。温迪向他们阐明视频的事情事理,让他们选择框架和背景音乐,然后把他们独自留在小屋里。拍摄者锁上门,面对摄影机拍一段三分钟的视频。三分钟后,摄影机关闭。温迪再进来,重放录像带。如果对方赞许保存,温迪就会把它加入影片集;不同意的话就删除它。
这些“爱的录像带”非常迷人,它们揭示了拍摄者和不雅观看者的统统,还有拍摄的韶光。一位五六十岁的女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梳着发髻,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一位奶奶。她热爱统统:鲜花、生活、事情、同事……这真的很动听,一个看上去如此温和沉着的人,内心有着如此强烈的对生活的热爱,这也让我感到吃惊。到了第四十秒钟,她重复了一遍“我喜好鲜花和生活”,又溘然说“还有我的孩子和我的丈夫”,然后就不说话了;接下来她说,“哦,三分钟太长了”。因此,在末了两分钟里,她只是时时地说,“我想不到三分钟会这么长”,或者换种说法,“太长了,用三分钟来聊什么是爱太长了”。真是不可思议。我有一种觉得,我真正触碰到了这个女人被困于个中的这段韶光的肌理,它也是我不雅观看和聆听这盘“爱的录像带”时所处的韶光。
在《记录说谎家》中,我进行了一些新的考试测验,在强烈的情绪时候之间引入一段静默的时空,让不雅观众有韶光抵达那里,感想熏染自己内心情绪的余震、话语的反应和被遗忘的影象。这就像把他们自己经历的韶光用在电影的韶光里。我安排了充满情绪的时候,然后是将这些情绪投射个中的画面,末了让两者产生寂静的回响。
A & J:以是这是一种情绪储备?
瓦尔达:是的,情绪储备,还有对情绪的操纵,通过从一个镜头运动到下一个镜头来实现。一种情绪的“滑动”(这个词让我着迷):词语和词语所引出的画面。笔墨—图像对我们来说是标记或旗子暗记,但并不总是以期望的办法呈现。在《记录说谎家》中,我拍摄了埃米莉和情人之间的爱情场景(写实的、详细的、做爱的)。这是一个图示,也是在彼此的怀抱中尽享身体爱欲的标志。在纳丽丝·阿维夫拍摄的另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自助洗衣店里背对着我们抚摸自己的头发。她心不在焉地在油腻的头发上编织着孩童般的辫子。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毫无感官享受性,却带着明显的性意味。当我和埃米莉的扮演者萨比娜·马穆(Sabine Mamou)一起看这部影片时,我把稳到了萨比娜在演出做爱场景时的一个动作,她会将手肘举过分顶。我还记得,当意识到可以将自助洗衣店里女人的镜头与做爱时抬起的手肘并置在一起时,我切实其实大喜过望。通过这种办法,在代表爱情的镜头措辞和下一个镜头中化为希望符号的纯粹官能之间,我可以实现“滑动”。
A & J:在《穆府歌剧》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事实和符号间的分离。
瓦尔达:没错。但在此之前我很少这样做。它涌如今《穆府歌剧》中,《五至七时的克莱奥》里也有 ——多萝泰(Dorothée Blanck)担当裸体模特时的姿势和保温箱中的婴儿。
A & J:那两个袒露的身体呢?您有时让他们彼此分开,彷佛是为了象征他们的分离。但有时这两个身体又在一起……
瓦尔达:这个阐明不错,我没这样想过。你只有在做爱的场景中才能看到这两个身体在一起,这无疑来自过往的影象,而不是什么新的美谈或性体验。其余,裸体男子独自睡觉的镜头,还有赤裸的埃米莉独自一人度过全体下午的镜头,都不象征着希望,而象征着不包含感官希望的韶光,是只有身体的韶光。
电影《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剧照。
A & J:但由于这种缺失落感,这两个镜头也充满了感官希望。
瓦尔达:是的……那种空的觉得……缺失落会带来一种非常强大的存在感。在电影中表现希望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说的不是希望和希望得到知足时的迹象,而是无法描述的希望,那种难以言喻的张力,除了通过具备形式的空来表现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就像在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雕塑作品中,空与满这两种形式一样强大,前者乃至更为强大。在陶艺中,我们也必须将空视为一种形式:在那里,陶器环抱着空的形态。
A & J:《记录说谎家》是一部关于孩子渴望拥有父亲的电影,还是一部关于身体希望的电影?
瓦尔达:毫无疑问都是。孩子惦记父亲,须要母亲。对付母亲来说,这是充足与空虚的稠浊,笔墨变成了一种痛楚的情色,且笔墨是希望的替代品。在第二部分中,孩子简短却精准的话语取代了母亲的话语,它总体地表达了母亲的希望,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希望,例如,“我不想一个人睡”或“没有你,就没有爱”。当男孩说“我想见爸爸”时——随口说出的话语——我确立了孩子这一主体,同时将主体分散了。第三部分则是关于其他人。所有那些表现出困惑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在场景中(无论是多么不起眼的场景)没有特定身份,却构成了影片的身份:一个打烊了的咖啡馆的女做事员,一个睡在长椅上的瘾君子,还有那个趴在沙地上一边哭一边用手抓沙子的女人。纳丽丝·阿维夫事后见告我,她认为这是伏都教的某种仪式……我不知道,我只是很受触动——这个痛楚的女人来到此地并涌如今我的电影里。
A & J:另一个场景中,有两个人彷佛在为一个去世去的人守灵,这彷佛更具仪式感。
瓦尔达:这是我某天看到的一个场景,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我重新组合了一下,一个女人像去世去了一样躺着,腹部放着一本《圣经》,两个男人跪在她身边。
A & J:《记录说谎家》彷佛偏离了您喜好的光明与阴郁、乐不雅观与悲观的对立。
瓦尔达:影片之中的确如此。这部电影充斥着阴影。但是,当将《墙的呢喃》和《记录说谎家》这两部影片放在一起看时,我们就从阳光转向阴影,从外部转向内部……这两部影片共同表达了对抵牾的偏爱。
A & J:这种对立并不总是那么严密或对等。我个人以为,《穆府歌剧》包含了 90%的痛楚和 10%的希望。
瓦尔达:大概是吧。两部影片确实有共同点,包括德勒吕(Georges Delerue)的音乐。它们都是彩色的,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这两部影片拍起来也都很难,就彷佛我一贯在抗拒,不想拍一样。我写《记录说谎家》的剧本写得很困难。我不断推迟开拍日期,当统统都定下来后,开拍的前一天,我在两个不同地方丢失了我所有的身份证件,还有没来得及复印的唯一一份剧本手稿。萨比娜设法找到了剧本。如果没有她和纳丽丝的耐心,没有她们将这个项目付诸履行的坚持,我可能就不会开始、更不会完成这部电影。
后来,我一贯被各种障碍所阻挡。我坚持要租下以前住过的公寓,但房东不同意。我坚持着、等待着,延误了很多韶光。拍摄开始前三天,我终于放弃了这个地方,半小时后,我创造了许多 20世纪 30年代的贫民房屋,它们内部宛如迷宫。这个园地有种诡异的沉着又令人不安,对付埃米莉和马丁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这比我坚持许久的那所公寓要好上十倍。这便是我所说的作品:遮蔽与戳穿、痴迷与现实、超现实主义、魔幻、拍摄不可拍摄之物的希望。
A & J:为什么您要在《记录说谎家》中利用“说谎”(menteur)这个词?这部影片中彷佛不包含任何谎话。
瓦尔达:正好相反。整部影片反对的便是“真实电影”原则。它是“电影—梦想—寓言”,是阿拉贡会称之为“真实的谎话”的东西。不是我,我现在所说的统统都像是后记,电影已经分开了我的掌握,别人可以看到它们。我评论辩论电影,阐释电影,梦见电影,我试图理解电影,评论辩论电影操持和它的构造,谈论细节。当我拍电影时,我是影片有机现实的一部分。拍完《墙的呢喃》后,我与萨比娜·马穆一起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剪辑事情,处理图像和笔墨,不雅观察它们,谛听它们。等待影像变得清晰,并开释其他信息。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开始写别的东西,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回来连续剪辑。至于《记录说谎家》,从声音、面孔到身体都是“真实的谎话”。谁在说话?以谁的名义?当从萨比娜手中剪辑出屏幕里萨比娜的影像时,我们真的感到迷惑,我说“是你……还是她……”,我们笑自己建立的这座迷宫——现实、虚拟形象、真实形象或想象中的形象终极都彼此相似。
“我从未真正属于某个团体”
A & J:末了我们想问一个历史问题……您如何看待如今自己与“新浪潮”的关系?
瓦尔达:套用雷诺(Renaud Séchan)那首歌,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一群孩子……但我从来不是某个团体的成员。他们说我是早于“新浪潮”的先行者,但我完备是自己摸索的,不是电影文化的一部分。我当时身处“新浪潮”的浪潮之中。多亏了戈达尔,乔治·博勒加尔能担当雅克《萝拉》一片的制片人。托雅克的福,我拍了《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接力棒就这样通报下来,匆匆成了一些共同方向,比如拍摄低本钱电影,人物穿行于巴黎街头。
电影《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剧照。
从这个角度看,当我们看《北方的桥》(Le Pont du Nord)时,会创造里维特从未老去!
但我从未真正属于某个团体,因此人们习气于遗漏我,将我打消在外。 1976年,穆西多拉(Musidora)团体出版了一本关于女性的书《话语,她们在旋转》(Paroles, Elles Tournent),里面没有提到我。去年,也便是 1980年,《电影手册》杂志出版了两期专门先容法国电影的特刊。这两期都没有提到我,也没有提及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天知道里面谈到了多少人,有趣的人,不同的人,各种类型的法国电影人,男人、女人,奥弗涅人。但没有提到我。是由于我在美国吗?路易·马勒也在美国。是由于厌女症吗?当然不是,卡特琳·布雷亚(Catherine Breillat)、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人都在个中。是身高不敷五英尺的人被忽略了吗?不,尚塔尔·阿克曼也在里面。只有我被遗漏了。没有人联系我,我所有的信件都寄到了洛杉矶,但从没收到任何见地表。我真的很伤心。如果多年来邀我做过多次长篇访谈的《电影手册》杂志都将我打消在外,那真的觉得像被流放了。
但这并非有时或轻忽。恰巧我的新电影讲述的便是这个问题,有关分离。这部电影是关于缺少居住之所的,缺少旧日环境或群体带来的温暖,缺少可以依赖的肩膀。现在,我带着两部作品来到这里(很奇怪,我们在这次采访中险些没怎么谈到《墙的呢喃》)。我回来后,每个人都在看我的电影,和我谈天,问我问题。我受到了激情亲切洋溢的欢迎。大概我确实存在于法国电影中,只管没有得到多少热度或庇护,但至少我现在身处个中而非居于其外。
原文作者/ [美] T.杰斐逊·克兰 编
译者/曲晓蕊
摘编/申璐
编辑/申璐
导语校正/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