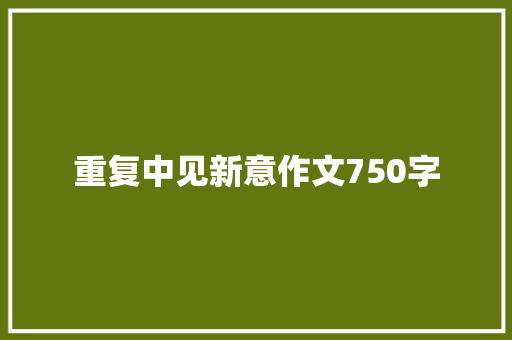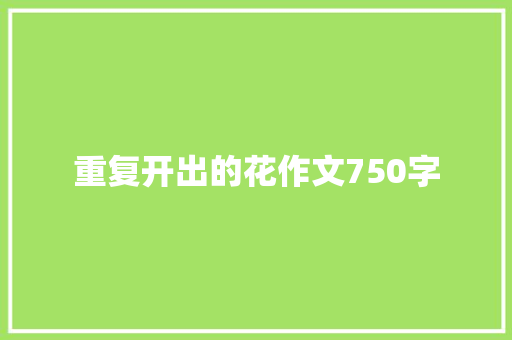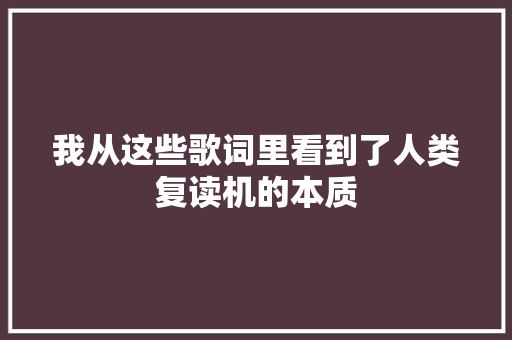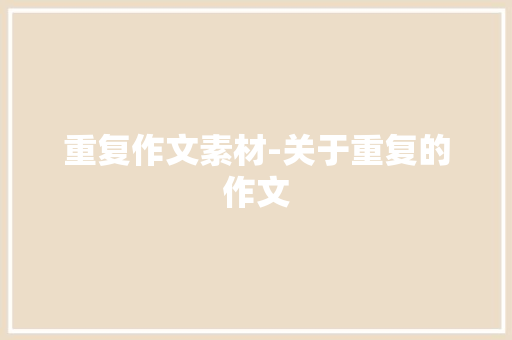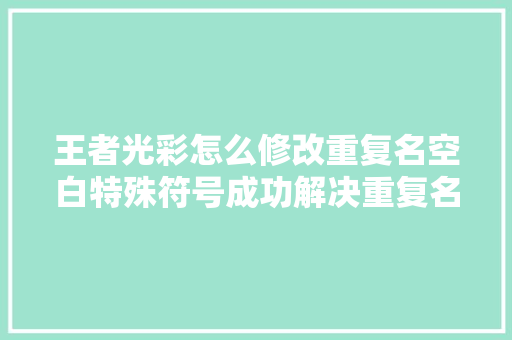这阵子在上海的生活有许多突发的变革:小区居委会的存在感溘然变得显著,戴着口罩的爷叔挨家挨户拍门关照晚上检测核酸的韶光;保安在进出门的时候也会多加一个祈使句“量一下体温吧”,声音很轻却有不容反抗的威严,哪怕只是去拿一趟快递,也得把手腕抵到测温处。而这时院子里的紫叶李已经由盛转衰,玉兰花也落了一地,只在家里多待几天,像全体春天都要错过了。
没有料到的变革会带来虚无感吗?如果会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上周五听了一场名为“虚无不是悲观生活的情由”的线上讲座,主讲人是哲学教授孙周兴,紧张从尼采哲学的角度讲述了这一问题,个中最故意思的是讲到承认人生终归虚无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以及日常生活不断重复,而生命的意义指向何处。得出的一个大体结论是,应该以创造性重复对抗虚无,力求每次重复有所变革,而不是悲观混日子——这彷佛是一个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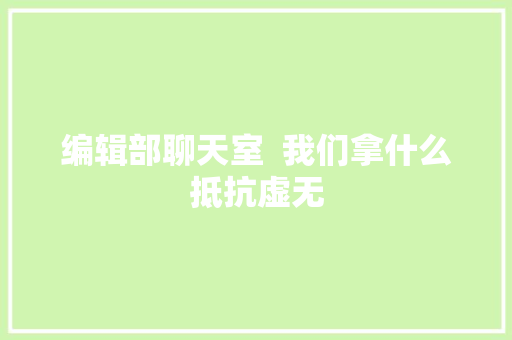
不去谈论虚无的来源“上帝去世了”,也可以将这种觉得引申为此前坚信的秩序的溘然瓦解,不管是生活的还是生命的秩序,或是创造甜蜜安稳的生活不那么天经地义,或是父老的讲述对付我们彷佛不太适用——池莉的《霍乱之乱》中科学降服愚蠢的乐不雅观基调对我们很难说有所启示;而《瘟疫与人》里的以史为证显得更有道理,在特定的时段,人们更须要寄希望于一种秩序,以从容应对瘟疫胆怯与心灵创伤。
就在当下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又应该如何将被击落的履历、错失落春天的痛惜、被保安哀求量体温的不宁愿编织成具故意义的叙事呢?
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理解是纵然认识到了某些人生部分原形,也应该提醒自己反抗绝望的必要。陈嘉映讲述的良好生活,在我对抗虚无觉得时常常起到主要的浸染——他说,不管社会与时期如何,只要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中培植你自己的良好生活,这种培植包括批驳与改造,而不能让批驳流于抱怨。一方面承认人被抛入的处境——人的生平中难以割舍的东西都是被抛入的,诸如家乡、祖国和家庭,另一方面也认为人有不断培植更好的自我的必要,这也是一个方法。
是什么让我们觉得虚无:缺少预期或是重复循环
林子人:我常常想,在我的人生乃至我们这代人的生命中,新冠大盛行都将是最主要的迁移转变点。如果问我在生活中是否觉得到某种虚无,那大抵是这一认知给我带来的,从2020年初至今依然存在的某种不真实感:“战疫状态”在过去两年里被常态化,许多我们认为是正常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东西——比如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没有口罩遮挡的表情、自主性或永劫光段的人生存划——都不再天经地义,乃至无比奢侈。如今的我对做下个月的行程操持都迟疑不已,每次在影视剧中看到俏丽的风景都近乎贪婪地睁大眼睛。缺少预期的生活最随意马虎让人产生虚无感。
徐鲁青:我和子人正相反,最近居家隔离后体会到的虚无感不是来自巨大的变动,反而是更深刻感到日日是无变革的重复,一眼望得到尽头。由于不能出门,活动空间很小,每天难得和人说上一句话,生活也变得无比规律,起床后便是写稿,用饭,写稿,再用饭。或许由于极其有限的外部刺激,我加倍体会到生活近乎荒谬的循环往来来往。难怪众神认为最毒辣的严刑便是让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石上山,让他在重复里直面绝对的虚无。但末了西西弗斯找到了对抗虚无的路径,他创造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自己感到充足,以是加缪说西西弗是荒谬的英雄,由于他不再依赖“众神”是否给予更伟大的意义和目的,而是完备面对此刻的体验本身,自己创造了幸福。或许我在陷入重复的生活循环时,也该当在看似无味的日常中创造乐趣,接管生命便是不断推石上山。
陈佳靖:疫情确实带来了很多不愿定性,比如一场活动溘然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一次出游操持由于居家隔离被取消,每个人打仗外部天下的机会彷佛都在变少,或者时断时续,时常被迫做出改变。大概没有人会喜好长期处在一个自身难以掌控又相称封闭的环境中,虽然是在自己最熟习的家里,但实际上并不在最舒适清闲的状态。对我而言,保持规律生活这件看似最大略的事反而成为了抵抗日常混沌无感状态最主要的一环。
重复在过去可能意味着厌倦,现在则变成了对意志力的磨练,对内心天下是否足够宽广和稳固的磨练,对持久耐心和原谅度的磨练。能够在日常中加入一些创造性得到更多乐趣当然很好,但纵然没有,重复本身就不可能带来快乐和力量吗?我们是否有能力仅仅依赖重复来构建生命的意义呢?实在放在任何一件小事里,重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向的重复会叠加出质变,正如重复的运动让身体保持康健,重复的阅读会带来智识的收成。在这里,重复不是静止的,而该当是能动的。回归到详细的行动里,觉察到细微的改变,就不至于太虚无。
认清虚无之后,仍要好好培植人生
林子人:之前谈论农人工读海德格尔的那期谈天室我说过,“无知无觉的幸福是非常虚妄的,懂得更多、思考更多虽然有时候是一种包袱,但也能给人带来活下去的勇气和做选择的指引。”对我来说,在阅读中学习和思考便是对抗虚无的最好方法。纵然我可能对所处的环境暂时无能为力,但至少“理解情形”能让我得到某种把控感。更幸运的是,我的事情让我能够用采访和写作与他人互换我的想法,专一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的避风港。《冰雪奇缘2》中安娜演唱的The Next Right Thing非常符合我这两年的心境,与诸位分享个中的几句歌词:
The life I knew is over(曾经熟习的生活已然结束)
The lights are out(灯火熄灭)
Hello darkness(你好阴郁)
I’m ready to succumb(我已做好屈从的准备)
This grief has a gravity(悲痛如引力般)
It pulls me down(要将我击垮)
But a tiny voice whispers in my mind(但一个眇小的声音在我心中低语)
You are lost hope is gone(你已迷失落,希望已逝)
But you must go on(但你必须走下去)
And do the next right thing(去做下一件精确的事)
Take a step step again(再次迈出一步)
It is all that I can to do(这是我所能做的统统)
The next right thing(下一件精确的事)
潘文捷:豆瓣乱来学小组有一个万能金句:韶光面前都是尘土,普通人是,伟人是,国家也是,人类也是,连宇宙都是。这句话之以是能乱来万物,是由于它点出了人生虚无的实质。我理解“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就在于你首先得认识到人生本来便是虚无的,然后才能在这根本之上构筑自己的人生——由于人生中的统统重大变革的条件在于,意识到意义不是数学公式,不是可以抄的作业,存在是由我们自己来诠释的。
海德格尔有一个术语叫作“沉沦”,人总是故意无意地进行自我欺骗,躲避自身的可能性,让其他人来决定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他人的自我而不是本真的自我,便是一种沉沦。弗洛姆也有躲避自由的说法——他会把孤独和自由联系起来,人们为了肃清孤独,并不想要自由。这样久而久之,人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躲避自由的生理机制。这样会形成两种人,一种是虐待狂:办理办法便是通过掌握他人、剥削他人往返避孤独;一种是被虐待狂——有内在的自卑、内在的无能、内在的无意义感,于是让自己被他人统治、被他人保护、被他人掌握。虐待狂和被虐待狂构成了共同体,但两者都不能在根本上办理问题。弗洛姆认为该当发挥人的创造性——包括事情和爱——来办理这个问题。
徐鲁青:文捷提到的弗洛姆的说法也让我想到了萨特,他认为存在本身便是虚无,我们逃无可逃,这种虚无意味着绝对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而是人被抛入这个天下后完备面对洞开的可能性。但这时许多人会陷入“自我欺骗”,也是弗洛姆所说的“躲避自由”的状态,由于一直歇地探索,不躲避地面对洞开的可能,须要充足的勇气与长久的决心,这比陷入规定好的实质标签,度过未经核阅的生平要难得多。
姜妍:我觉得我的回答会歪楼。由于提起“虚无”,我首先想到的是《黄帝内经》中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既是古人对康健的认知和建议,也是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虚无”没少被提及,《道德经》第二十三篇的小标题便是“虚无”,《庄子》外篇《知北游》里,讲了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的故事,在这个过程里,他实在是在求道论道,后面遇见黄帝时,黄帝对他说“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这里面表示的也是道体虚无的思想。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虚无,那我只能说这是可望不可及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