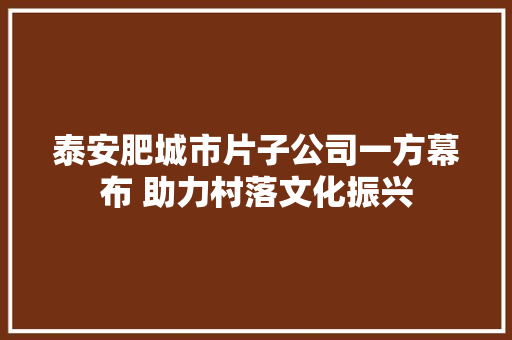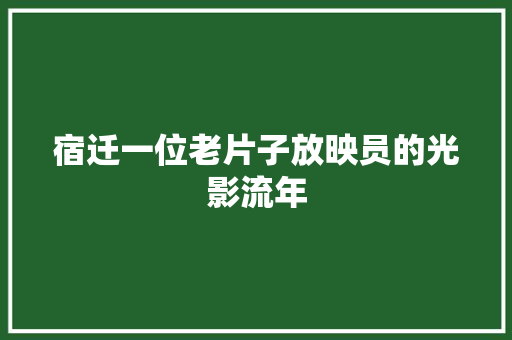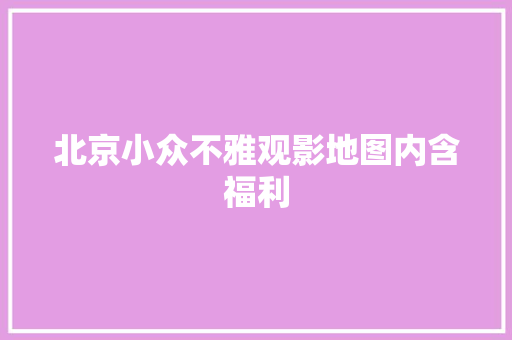这是一个践履惟新、承上启下的年度,中国刚刚走过雕琢奋进的5年,又将开启新的征程。新京报也历经循环,见证国家之巨变,用纸笔、用领悟创新的奇思妙想,坚守“做一个时期记录者”的不变初心。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本日,我们重新出发,聚焦曾在大时期浪潮中搏击、思虑的近30位新闻人物,追寻他们的故事,回顾过往,期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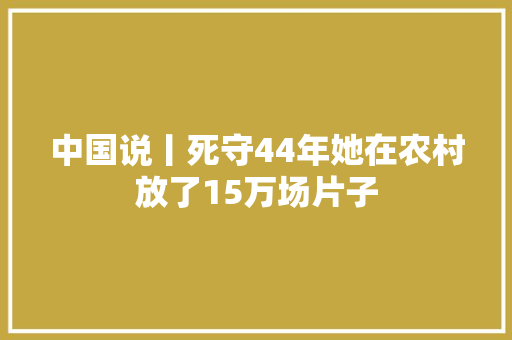
95岁的反腐老人杨维骏,深感自己时日不多,而反腐仍在路上;大凉山峭壁村落里的学生上学有了钢梯,但他们仍想走出大山;新科技日月牙异,令人愉快又如逆水行舟……还有专一坚守的实业家、居庙堂之高的顶尖学者;抑或默默无闻的草根,他们是大千天下的一花一叶,他们的人生进程,构成了中国社会改革变迁的素描绘卷。
重新出发,我们同在路上,怀揣着初心和梦想。他们的过往便是我们的过往,他们的未来亦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故事,即是连接着过往与未来的“中国说”。
郭建华,开封市基层电影放映员,坚持在屯子放电影44年。新京报尹亚飞 摄
凡是有采访郭建华,她就会把带到开封的田间地头、村落头巷尾走一圈,看看地里的庄稼,和老百姓聊谈天。
她说,只有看看屯子,才会理解她大半辈子做一件事的意义。
63岁的郭建华是开封市一名放映员,坚持在屯子放电影44年。44年中,她在屯子放了15万场电影,不雅观众达一亿人次。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先后三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电影家当促进法草案的搜聚见地反馈会,反响屯子农人不雅观影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屯子电影市场逐渐衰落,基层电影公司主动关门,郭建华固执逆行,竭力坚持着自己的那块银幕,她说,城里的屏幕越来越多,农人也该拥有一块属于他们的屏幕。
美好的光阴
1960年,郭建华五岁,她第一次看电影。
“本日放电影啦!”
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好的,很快就传遍全体村落庄。
父亲牵着她,也去看电影。
夜空中的星星一颗颗亮晶晶的,空气里弥漫着花喷鼻香和青草味。
星星下面的乡间小路上,村落民们三五成群,领着孩子,拎着凳子,拿着扇子,说谈笑笑往打麦场赶。
电影开始前,麦场上已经人隐士海,麦秸垛上,树杈上,墙头上都坐满了孩子,星光亮得能照亮乡亲们欢笑的脸。
一束光从背后照过来,对面洁白的幕布上涌现了八一制片厂几个发光的大字……
那部电影是个战役片,名字已经记不住了,郭建华当时还看不懂,但她好奇,“布上的人哪里来的?会动,还会说话。”
父亲带着她去问放映员,放映员逗她说,“等你终年夜了,也当放映员,就知道了。”
郭建华看到电影里一个姑娘留着两条很好看的大辫子,从此,也留起了辫子,后来,一贯留到长及膝盖。
回到家,她就见告爸妈,终年夜后,也要当放映员。
1973年,全国招收第一批女放映员,她所在的开封县,现在开封市祥符区招收三名女放映员。郭建华去应聘。
口试的老师看到郭建华,摇了摇头:“你又瘦又小,怎么搬得动电影,我们是干事情的,不是帮你爸妈养孩子的。”
郭建华苦苦哀求,“我体力好,啥活儿都能干,让我试一下吧。”
当晚放电影,不到80斤的郭建华骑车带了四部影片,跑得比所有的男同道都快。
从此,放映场上有了一名长辫子女放映员。
“那时候,能当上放映员,便是屯子女孩子里面的佼佼者。”郭建华说,那是光荣的职业。
从1973年到1993年,郭建华放了13000场电影,“常常是一天三场。”收工的时候,都能听到鸡叫了,她和同事们推着自行车踏着晨露回家。
现在回忆起来,她认为那是美好的光阴,“由于你能实实在在感想熏染到给老百姓带去了快乐。”
不管放映场有多少人,多拥挤,她只要一到场,乡亲们就会让出一条路,还有村落里的老奶奶捧着盘子给她送花生,往她口袋里塞红皮鸡蛋。
她最享受的是,自己扭开放映机开关,放映场上成千上万的人立即安静了,乡亲们随着电影情节一起哭,一起笑。
至今,看过郭建华放的电影的人,超过一亿人次。
当年的美好光阴,被现在的很多人怀念,她的故事被搬上荧幕,以她为原型拍成了电影《放映路上》,放映场次超过10万场。
郭建华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新京报尹亚飞 摄
要把放电影当作几辈子的事儿来做
和郭建华一样,《放映路上》的女主角喜好微笑,脸庞姣美,是个大辫子女孩。
但美好背后,也有悲哀故事。
1978年,《红岩》这部电影很火爆,每天要放六场,已经有身七个月的郭建华每天加班。有一次放映中,郭建华腹痛难忍,被乡亲们用板车拉到公社卫生院,孩子早产,只有4斤重。
年夜夫见告郭建华的家人,孩子弗成了,活不了。百口人失落声痛哭,郭建华的丈夫用军大衣裹住孩子,牢牢搂在怀里。他安慰郭建华,“你别伤心,你很能干,你看孩子多有福泽,知道你是放电影的,都急着出来看电影呢。”
丈夫说着说着也哭了,“孩子肯定没事,你看,她是带着名字来的,你放的电影主题曲叫红梅赞,她就叫红梅。”丈夫开始哭着哼红梅赞。
哼着哼着,孩子动了。
郭建华的第一个女儿,就叫红梅。现在,红梅在祥符区图书馆当副馆长。
为了郭建华放电影,本可以留在部队事情的丈夫末了做了农人。
同是1978年,丈夫参军队回家探亲,要把有身的郭建华接到部队生产,“这样丈夫可以留在部队,那里的医疗条件好,我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他们买了晚上十二点的车票。
当晚,郭建华整顿行囊,也没有去放电影。
他们整顿行李的时候,公社的布告来了。
当晚,一名新放映员接手郭建华的事情,为一万多名屯子不雅观众放电影,但电影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乡亲们看一次电影不随意马虎,好不容易等来一次,没有声音,就不满了。
有孩子到公社布告家门口喊顺口溜:“拿竹竿,扛扁担,你这个布告真软蛋,便是管不住一个放映员。”
大家埋怨,布告放走了郭建华,让大家看不成电影。
布告没办法,就骑车去了郭建华家,冲进郭建华屋里就说,“白培养你了,现在你要走,老百姓都不满意了。”
当晚,丈夫带着郭建华来到了麦场,放出了声音。
二人回到家,丈夫见告她,“你睡会儿吧,赶火车的时候我喊你。”
一贯到第二天,郭建华醒来,创造丈夫已经离开。
后来,为了照顾妻儿,丈夫放弃提干机会,退伍在家,当了农人。
“丈夫、女儿两辈人都为我付出了,有时候会想,值不值?”但每次到放映场,郭建华又以为值了,“每次去放映场,人隐士海,我一涌现,人们就给我让出一条路,他们渴望电影。”
郭建华说,当时人们缺衣少粮,不忍心看到他们精神上再饥饿,每次去放电影,觉得都是给老百姓送饭,“我要把放电影当作几辈子的事儿来做。”
众人划桨开大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郭建华创造,她想当做几辈子来做的事儿,不怎么受市场欢迎了。
当时,电影开始从操持供给向市场化转变,县城、州里录像厅开始满地着花,加上VCD、DVD开始在屯子盛行,再到屯子放电影,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各地的电影放映公司开始纷纭关停。
1996年,郭建华所在的电影公司也面临倒闭,老领导留下一封”改革难”的长信,背着铺盖,回了老家。
刘兰生便是那个时候进入电影公司的,他回顾,那时候,员工每人每月人为只有30块钱,办公室的门锈迹斑斑,一下雨,屋子还漏水,屋子里的水能把脚都埋没,开会只能坐到桌子上,到后来,30块钱的人为也发不下来了。
郭建华的同事,也纷纭转行,亲戚朋友劝郭建华,“转行吧,没人看电影了。”
“我不信没人看电影了,由于我去放电影的时候,还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银幕。”郭建华说,“风光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好,现在不风光了,我不能忘了他们。”
1996年2月,郭建华出任电影公司总经理。
上任第一天,员工等她揭橥就职演说,她沉默了半晌,“我想和大家说说电影人的心里话,就用三首歌代表吧。”
那三首歌,分别叫《生活像一团麻》、《众人划桨开大船》、《联络便是力量》。
当天,员工们集资,凑了两万元,现场的文化局领导,承诺给公司贷款2万元,算是公司的启动经费。
“我不只是个放映员了,我喜好屯子,想给农人放电影,但我得先活下去。”郭建华骑上自行车,开始跑市场,探求赢利点。
郭建华回顾,当时,红白喜事的活儿接,企业开业的活儿也接,每场可收入150元。半年韶光,公司收入到了20万元。郭建华的电影公司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电影公司并不富余,他们至今挤在一个破旧的办公楼里办公,最亮堂的透风最好的房间用来存放设备,最大的房间被用来做成了青少年普法教诲基地,放法制电影、摆放普法展板。
“在这里随着郭大姐事情,没法大富大贵,便是以为能实现点自己的代价。”已经是公司管理层的闫邦昭说。
“现在已经很好了,以前我们是拉着板车去放映,后来我们是开动手扶拖沓机去放映,现在我们开着汽车去放映。”郭建华以为,能够给农人留下一块银幕,连续给农人放电影,已经足够幸福。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郭建华带着自己的团队放映了140000多场电影。
“郭大姐又回来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屯子电影银幕次第熄灭的20多年里,郭建华带着自己的团队放映了140000多场电影。
“对市场,我不让市场适应我,而是我去适应市场,对农人,我也去主动适应农人,把不雅观影权还给他们,他们须要看什么电影,想看什么电影,我就给他们放什么电影。”郭建华说。
现在屯子留守老人多,他们喜好看贴近生活的故事片,豫剧,郭建华就给他们放《包上苍》,留守儿童没有父母扼守,为了防止他们走歪路,就给他们放法制电影。在河南省100多个屯子数字电影放映点,她组织放映《关注屯子留守儿童》,《屯子防诱骗知识》等电影3万多场,不雅观众150万人次。
开封市祥符区的农人栽莳花生,郭建华就给农人放映栽莳花生的科教片,有的农人栽种小麦,就给他们放预防小麦干热风的电影,西姜寨乡发展特色家当,栽种红豆杉,郭建华就给这里的农人放《红豆杉快成长》。
郭建华创造,农人对一些电影腻了,比如一些科教片,农人说电影太长,太专业,看不懂,郭建华就找普通点的科教片来放。
她给河南电影制片厂发起,拍了故事化科教片《咱俩花生好收成》,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农人接管起来随意马虎一些。
农人尝到了甜头,今年,开封市祥符区开展电影扶贫事情, 将一百个村落纳入扶贫工具,开展百村落千场电影扶贫活动,播放科教片。 还准备筹建一百个放映广场,广场上有灵巧的放映设备,白天是展板,晚上挂上屏幕,就可以放电影。
西姜寨村落庄民王大中说,“郭大姐放的电影不是大片,但都是农人须要的。”
朱仙镇五十多岁的村落民说,“郭大姐又回来了,三十年前,她来放电影的时候,都说,大辫子又来了,现在,都喊,老太太又来了。”
一名村落干部说,给屯子人拍电影、放电影不挣钱,这事大概只有郭大姐在做。
63岁的郭建华眼角爬满了皱纹,但依然爱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喜好系一条赤色的围巾,和曾经的辫子一样长及膝盖,她一涌现,依然引人瞩目,村落干部、村落民都会围上来。秋日,花生熟了,他们又会端出一盘花生。
村落庄广场下雨的时候,村落庄里的干部和村落民会帮忙腾出村落室、学校的教室,让郭建华放电影。
作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提出了关于支持全国中小城市数字影院发展培植的建议,“中小城市靠近农人,他们可以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电影院享受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这个建议在国家“十二五”发展方案中已有表示。
她先后三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电影家当促进法草案的搜聚见地反馈会,反响屯子农人不雅观影问题。
郭建华。
“别拍我了,拍我的花生吧”
2016年全国两会,媒体围着郭建华拍照,她见告,“别拍我了,拍我的花生吧,比我好看。”
郭建华持续四年带着花生上两会。
花生,是郭建华老家开封的特产,也是她最有感情的农产品。“我从当放映员去报到,母亲怕我饿着,给我口袋里装的是花生;放映场上,农人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的是花生;我放映的时候,乡亲们给我真个也是花生最多。”
由于郭建华的争取,开封市祥符区加速了该地花生产业化进程,农人栽莳花生收入增加四倍,今年1月,这里的50万亩花生获颁中华公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书。该地花生还登上了国际航班,成为休闲小食品。
现在,郭建华已经发起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我家花生好卖钱》,“促进农产品品牌化。”
除了为花生代言,郭建华管的事越来越多。
“在屯子广场放电影前,我们都会放一些音乐暖场,一些村落民就随着音乐舞蹈,打盘鼓,进行娱乐活动。我以为这是好事,多一个人舞蹈,打鼓,就可能少一个人赌钱打麻将了。”
她向当地干部建议,鼓励村落民发展扇子舞,广场舞,打盘鼓,她提出,“锣槌鼓槌代替法槌”,“村落民精神天下康健了,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西姜寨乡把盘鼓发展成了一项特色的村落民集体健身项目,西姜寨乡党委布告李恒志说,“每个村落都有盘鼓队,都是自发组织的。”
现在,盘鼓队还成了一种盘鼓经济,有人办红白喜事,都会找村落里的盘鼓队去助兴,一次能收入800到1000元。前几天,一个盘鼓队到兰考“走穴”,一次挣了3000元。
西姜寨乡每次盘鼓队大型排练,郭建华都要到场。
她还给一些穷苦的村落庄买了扇子,鼓励村落民跳扇子舞。
曾经,有人说郭建华不食人间烟火,郭建华不服气,“我食人间烟火,这四十多年来,看过我电影的人有一亿人次,这是一亿张笑脸,这些笑脸,值多少钱?”
现在,郭建华的电影更靠近“烟火”了。
“我越来加倍现电影对农人的好处,每创造一点,都让我多一点动力。”63岁,她停不下来,“44年,觉得放映路对我来说便是一条高速公路,只看到加油站,没有看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