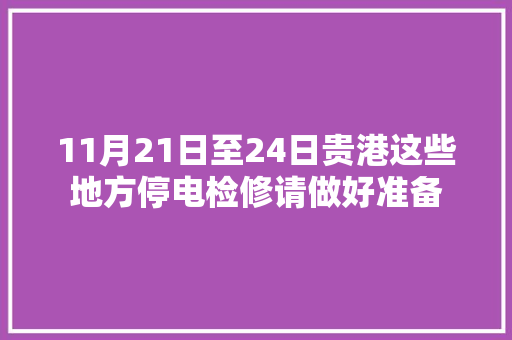小江打着口哨儿,坐在他的修鞋店,也便是他的王国里。

店面朝东,是老白城阛阓的门厅里隔出来的狭长的玻璃屋,门框都漆成湖绿色。当年小江在这路口摆摊儿时,是在大楼表面支个小棚子,风吹日晒好多年。他的活儿好,老主顾多。现在租下这间店,打理得干净利落。四只红松木箱子靠墙摆成一排,里面放工具和鞋,箱子上放着米白色的座垫儿,恰好给来修鞋的人坐。角落里搁一摞供人丁宁韶光看的杂志,被顾客翻得卷了花花绿绿的封皮。
正值早上阳光涨满的时候,早春景象,虽然还有些微凉意,但屋子里却暖意融融。这里也愈发不像个修鞋店而像个茶座了——然而只是没有茶。一个来修一双女鞋的中年男子,目不斜视地看小江修鞋,像在看一场演出。
小江用钳子起下旧鞋钉,然后垫上一张硬皮子,用剪子利落地剪下鞋钉轮廓,钉上钉子,再用小刀仔细割得贴合。做这些,就仿佛小学生第四百遍做老师留下的习题,闇练得不用睁眼睛。
小江有一张俊朗的脸,没有皱纹,只是黑,看上去一点不显老,但实在他已经是个老鞋匠了。在这车水马龙的路口,小江已经做了二十年,什么人没见过?然而什么人还不是一贯叫他小江?
一个头发染成稻草黄的女孩儿推门进来:“你快点把我这鞋缝上!
我焦急去世了!
”口气熟得彷佛是小江的外甥女。
小江斜眼打量一眼鞋子,并不举头:“缝不了呀,我的机器坏了,早上刚要修,这不,来了这么多活儿!
”
女孩儿的鞋是一双玄色磨砂平底系带鞋——系带的位置开了线,像一只鱼嘴,丑陋地张在那里。她用手按了按那鱼嘴,不耐烦地提高了音量:“你到底能不能修呀?”
小江一边用锤子敲钉好的鞋钉,一边说:“没办法!
”
女孩儿把双手插进玄色皮夹克的衣袋里,用脚踢一下小江的木箱子,露出她穿黑丝袜的大长腿:“真是!
你真不能修呀?延误老事儿了!
你!
”
小江锤子一直,也不理她。
女孩儿转身推了玻璃门出去,就让那门大敞着,扬长而去。小江放下腿上的鞋,要起身去关门,等着修鞋的男子早已起来替他关上了。
小江把鞋拿到机器上打磨,忽然又停下来说:“我的机器可没坏,便是不想给她修。这种人……”——呸地一下吐出一个小小的鞋钉儿:“这种人本色太低。不是什么好职业——对面歌厅的三陪小姐!
”
下午四点半钟,小江开始收摊,把门外的缝纫机搬进屋,把工具一样一样归置到大木箱里。
一个高挑的穿着一件玄色连身裙的姑娘提着一双细高跟鞋子,走到门口站住了,她进不去,由于有一个卖呆大叔堵在门口。她有些惊异地问:“江师傅,怎么这么早放工啊?我的鞋要换跟儿,请假出来的,还等着穿呢!
”
小江还没来得及答话,卖呆大叔说:“人家小江鸟枪换炮,有了大奇迹啦!
”
小江一边脱下皮围裙一边抿嘴笑。
大叔又说:“人家上市委大院上班去了。打更不比修鞋挣得少,便是去睡一觉,多得呀!
”
高挑姑娘失落望地说:“那是不是往后我们的鞋都没地儿修了呀?”
小江说:“老妹儿,你把鞋放那吧,我明天下了早班就过来修,担保你下午能穿上。”
高挑姑娘优雅地放下鞋子,袅袅婷婷地走开了。
卖呆大叔晃晃脑袋,说:“原来师范学院东校有个拐子修鞋,修得也不咋地,后来被一个女的把钱都骗走了,睡大街上冻去世了。长青大楼那个小梁子,得了脑血栓瘫痪修不了鞋了。现在就你这蝎子粑粑独(毒)一份(粪)能修鞋喽。”
小江用一把刷子前前后后扫衣服上的灰尘,说:“我这都没个人接班儿,往后也说不好啊。”
大叔一贯看小江锁好店门,骑上大破自行车一溜烟儿远去,才依依不舍意犹未尽地转身去看两个老爷子下象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