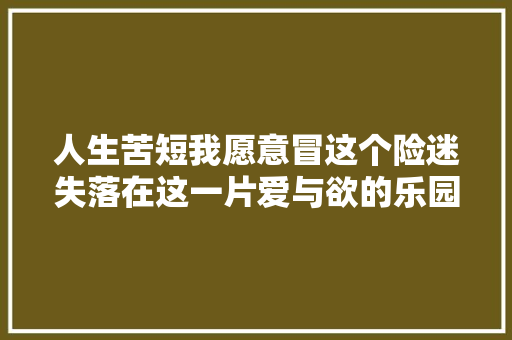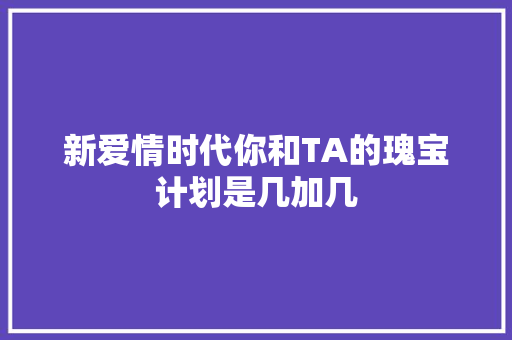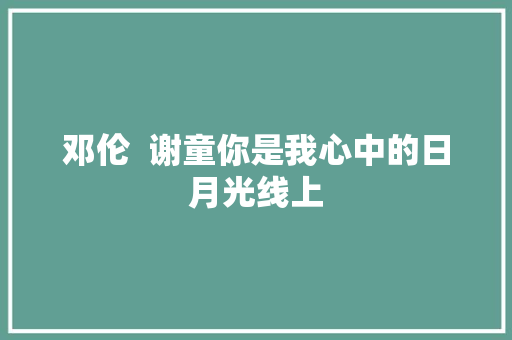最近《乐队的夏天》热播,老乐队们第一次站到网络综艺的舞台上被更广大的人群认识,新乐队也初露锋芒,越来越多的听众开始试着去理解独立音乐、理解不同的音乐类型,我们抱怨这一天已经迟到得太久,也光彩终于等到了他们发一刻光的时候。
想必不用再重复梳理一遍八十年代开始的海内摇滚乐乃至独立音告成长的历史,这条路从来都不短缺前仆后继的青春血肉,磕磕绊绊走来,中国独立音乐逐步摸索出一条道路,也学会在更大的语境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办法。“九连真人”、“刺猬”乐队在《乐队的夏天》中的表现,让我们再次由于笔墨与音乐碰撞带来的巨大能量而振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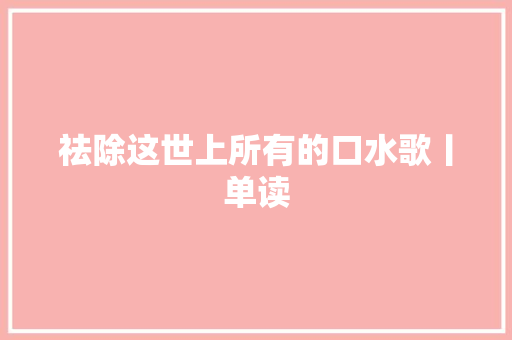
“刺猬“乐队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乐队重新拾起中文歌词的魅力,以此贴近脚下的地皮。往前倒推十几二十年,海内不乏精良的中文乐队,比如腰乐队、声音玩具、万能青年旅店等等。本日要先容的是最近走进笔者视野中的海内六支年轻乐队,他们生动于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选择用母语创作,也不谋而合地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态度去核阅现实,在变革速率如此之快的时期背景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和笔墨,瞥见当下真实的生活。而不管这是不是独立音乐的黄金时期,总是须要有人连续歌唱。
脏手指(Dirty Fingers)
“脏手指”歌如其队名,十分“脏乱差”,险些符合人们对摇滚乐所有先入为主的想象:主唱的唱腔像是学了电视剧里的地痞,音乐神奇地兼顾了躁动和软烂两种特质。在评论辩论到这支乐队时,人们更多谈到的是他们音乐中的不羁和传染力,却常常忘却他们的歌词也可圈可点。当然了,脏手指的歌词一点都不“美”,他们肯定也不愿意被当做文学作品来解读。他们的歌词多是高度口语化的念白,这天然地授予了其旋律感和节奏感,像是醉酒后在街头大喊大叫,合营混乱激烈的音乐,让最镇静的人也不禁像他们一样横冲直撞。
脏手指首专《我怎么学的这么坏》
但千万不要因此以为他们的音乐只是纯挚的个人感情宣泄,他们很多歌都直接反响了自身包括其他同代人的生活状态,间接指出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假冒的摇滚明星》中,“脏手指”唱
“假冒的 rock star/爸妈的大蛀牙/成长在太阳下/啥都没萌芽”,
对光鲜亮丽、心存抱负却四体不勤的年轻人进行了诙谐讽刺,也可能是一次无奈的自我嘲讽;在他们那首可以说最广为传唱的《我也喜好你的女朋友》中,
“我不要找份事情/我不要再去做活/什么都不想赚/能不能把你有的分我一半”
则像是在不甚公正中的一次罢工抵抗。“脏手指”发达的生命力让人感叹摇滚乐的魅力从未远去,他们就像是一块执拗污渍,用戏谑去对抗、去消解那些同样难以撼动的规则。
海朋森(Hiperson)
我的 2018 年一共有两个收成,一个是一家剪发只要 25 块钱的理发店,另一个便是海朋森在“愚公移山”的现场演出。用卢卡奇的话来说,我们身处在的是一个史诗不复存在的小说时期,在碎片化的当代生活中我们很难再拼凑出任何意义上的完全,而海朋森的音乐让我有机会触摸到一种伟大。他们在 2015 年发行了第一张正式专辑《我不要别的历史》,专辑名字仿佛就已经发布了他们的姿态,他们选择直接进入到对时期生活和日常履历的描述和书写中。
“海朋森”在愚公移山
他们写下水道工人“穿玄色的衣服去玄色的地方”;
写“穿着日落颜色的裤子和上衣”的出租车司机;
他们说“公共生活没有幻觉”,
然后将公共生活形容成一场未知的演出或是足球赛,你我则是个中的演员和运动员。而个人履历的参与,则集中表现在他们诗化的歌词上。但与诗歌不同的是,同样是搭建意象的迷宫,海朋森的歌词却并不独立于音乐存在,也并不期待在措辞中形成完美闭环。音乐在音节和句子的重复中积蓄力量并且终极开释出来,是一颗钉子,靠一次次击打刺穿血肉。当然这统统的条件是踏实的音乐合营,各个乐器分部在气氛的铺垫和推进上循规蹈矩,幕布逐渐升起,“海朋森”让我们得以窥见这场人间悲笑剧的一角。
“海朋森”首专《我不要别的历史》
丢莱卡(Wasted Laika)
很多人看到乐队名字后的第一反应以为是一个拍照爱好者组建起来的乐队,但实在这个名字来自那只在前苏联的太空实验中被送到宇宙的流浪狗“莱卡”。和乐队名字的初衷一样,他们写下的音乐是关于那些被历史的滚滚车轮无情碾过的无名之人。“丢莱卡”成立于 2017 年,是一支非常年轻的乐队,而他们的年轻也不仅仅表示在年事上,他们歌声中的热烈、浪漫、愤怒以及对生活的用力拥抱,让我看到了年轻的本来面貌。
“这首歌写的是那个工人永久消费不起的地方”,主唱在演唱《工人体验馆》条件醒我们,这首歌的主角是一个身处工体夜店的失落意中年男人,去过工体夜店的人对歌中描述的画面定不会陌生。他们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明确的创作动机,文学作品对“丢莱卡”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空响炮》来自作家王占黑的那篇同名小说,讲述下岗工人的故事,中间唱道:
“就试着忘却过期的主人翁/没法不想起赢得过一个梦”;
《燃烧的平原》则献给对主唱意义重大的作家、墨客波拉尼奥,用
“这样的夜晚你也目送过/不代表未来可以逃过更多”
致敬他笔下那些在追寻永恒幸福路上捐躯的青春骸骨。如果说”海朋森“的歌词是诗化的,那么”丢莱卡“则更像短篇小说,每个故事都指向了猩红的现在和更加刺目耀眼的未来。
\"大众丢莱卡\公众5月尾发布的首张EP《健忘的平原》
Lonely Leary(孤独的利里)
一听到“ Lonely Leary ”的旋律,你就知道这不是一支向过去致敬的乐队。他们的音乐类型属于后朋克,歌词中充满了污染、飞船、雕塑、人群这类在当代才会被书写的词汇,带来一种未来感。
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穿过公园就到了》用蜂鸣般高速低频的音乐渲染涌当代城市的氛围——这也是他们的不雅观察工具,比如
“进入城市进入焚尽的癫狂/成千成万个入口在头顶开放”;
“四面八方都是被复制的风景/没人知道那是若何的征兆”;
“倾斜在晦暗中燃烧的工厂/持续传送的画面让人感到紧张”。
这些笔墨融化成塑料袋蒙在你头上,城市生活中熟习的压迫感和窒息感迎面而来,而他们的音乐更是将这种崩坏推向边缘。
如果笔墨可以拥有色彩,那他们的歌词一定泛着银色光泽,伴有冰冷的触感,在音乐的节奏中增加了密度和重量,像是筑成城市的水泥或者雨水敲击下的屋顶铁皮,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广泛的当代病。如果用画面描述“ Lonely Leary ”的音乐带给我的觉得,那就像是独身只身站在夏季中午的城市高速上,没有一丝荫蔽,只有热浪和汽车身后的扬尘,准备不才一滴汗水落下之前就将自己撞碎。
“ Lonely Leary ”在去年发布的《穿过公园就到了》专辑封面
卧轨的火车(Railway Suicide Train)
“卧轨的火车”是这几支乐队中最“轻”的一支,比起前面几个乐队的锋利,他们不论从旋律还是歌词来看都是最优柔的。在他们一首歌的评论下他们回答说“乐队也没以前那么撕裂了,疲软是我们的常态”,这让我对他们有了更加立体的认知。年轻人常常在这两种感情中拉锯撕扯,而他们诚恳地将这个过程展示在了音乐创作里。
2016年发行的专辑《余波》
前面的“ Lonely Leary ”如果是通往一种未来,那么他们便是回到过去——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抗姿态。他们的盛行可能跟“丧”的泛滥有关,而他们的歌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逃离或者超脱的感情,比如《白色汽车》中的
“人们眼中充满欲与危险/你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什么会变得更好/你不是他怎能知他所想/你可听到孩子们的悲哀/如果我无法度过这个冬天/不要再责备我了/妈妈”。
他们在歌中不断发问:还有什么是可以捉住的呢?这展示了我们伫立在巨大时期中最无力薄弱的一壁。他们用共通的感情将伶仃的人联结到一起,也代表了音乐能通报的另一种力量。
假假條(JaJaTao)
“假假條”可能是本日先容的最为邪典的一支乐队,他们的音乐成长在这片广袤地皮的湿润泥土里,遮住太阳,逼你正视这样的阴郁。他们的歌词为我们描述出一幕幕玄色荒诞剧,比如在《罗生门工厂》中他们唱道:
“秘密的后面 事情是这样的/剪一尺抱怨 补另一寸抱怨/阳光正残酷 证人会被活埋/阳光正残酷 照耀着我们的/恶行”。
也在《冇頌》中用
“杀去世一个人的动机 有没有错/关上所有梦的经由 用不用锁/蹒跚的谎话和虚构 一说再说”
唱出最深切的痛楚和疑惑;还创作出与电影《盲山》同名的歌曲,揭示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
在“假假條”的音乐中,锣和唢呐成为了险些最主要也最具标志性的部分,不容商量地让电吉他变得尖锐和悲怆,也使他们的音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宗教色彩,狂喜和大悲构成了音乐的两面,像是敬拜、也像是在为失落落的天下出殡。
2016年发布的专辑《时期在召唤》
文丨miu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点击上图,购买全新上市的《单读 19 :到未来去》
许可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