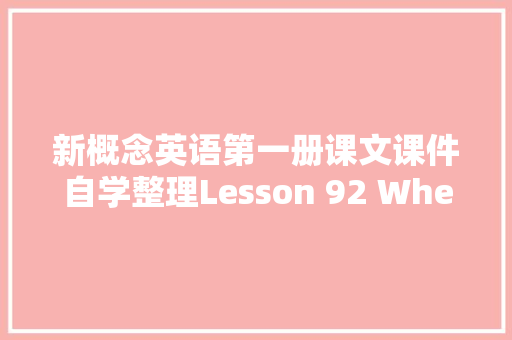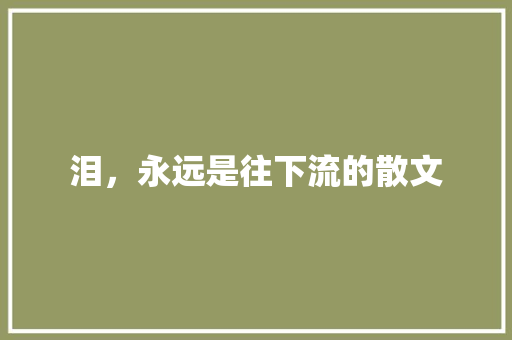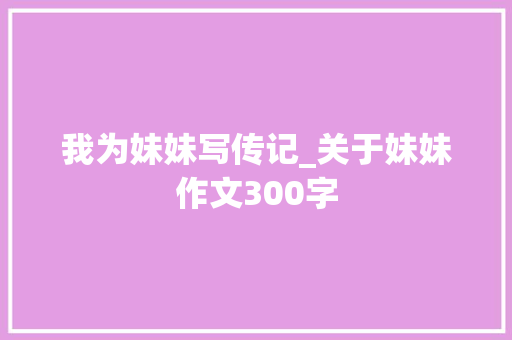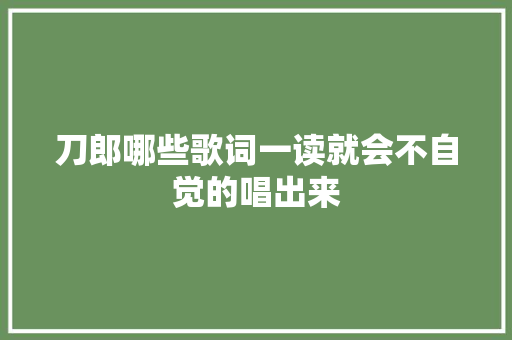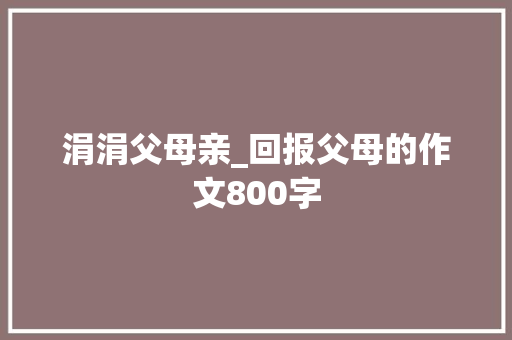其一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落,或许出生在哪个那个年代的山里人的人生都已经被设定在地皮里,传承着祖辈的生活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地皮为伴。

小时候,父亲和村落庄的人一样,关心着景象,关心着季候,春天在布谷鸟的叫声中,忙着翻地播种,夏天时候关注着景象的变革,担心着地里的麦子,秋日和霜降赛跑抢收地里的豆子,冬夜里忙着拧玉米,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寒来暑往,手头的活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对他而言,彷佛唯一安歇的时候,是坐在树荫下,和他一起终年夜的老黄牛说说话,拉着老黄牛到山里走走,看着老黄牛下劲儿的啃食着青草,吸一口焦黄的烟草,深深地压进到肺里。
小时候常跟在父亲的身后到山上去放牛,父亲把我架在肩膀上,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呵斥着慢性子的牛儿。随着父亲去地里,我在地头上的草丛里捉着蚂蚱,父亲头顶着一块儿毛巾在地里锄着地。父亲也在满天彤霞的傍晚归来,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一把柴火,捎回来满兜酸甜的野果子。那时候的父亲是壮实的男人,去地里的时候,我坐在一个筐子里,另一个筐子里放着一块儿石头,父亲就挑着这一副担子,向远处的山里走去。
其二
八十年代,父亲学着养猪,在院子后边垒了一个猪圈,搭起一个雨棚,当作猪的窝,每天又多了一个给猪割草的活儿,可惜那时候的不睬解技能,在想象中猪该当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喂食喂水就能自然而然的终年夜,猪生病去世去了一个,另一个在去集市的路上也去世了,这两头猪花费了家家的所有积蓄,想着依赖着它们可以追上步伐,但是全部赔了进去。父亲因此在院子里呆呆的坐了好几天。
父亲的牛是爷爷给他买的,那时候农忙的时候,在把家里的地全部打理完之后,父亲又开始赶着牛莅临近的几个村落庄里去给别人耕地,一亩地几块钱,父亲也很存心的把店主家的地翻得匀平均称的,好多人看父亲干活儿细致,找到门上来喊父亲去给耕地,父亲会从大的村落庄里的小卖部捎一双凉鞋,捎一把糖果,捎一些盐。
那年尾月,祖父去城里存钱被偷了全部积蓄,从此一病不起,几年之后就去世明晰,没多久,祖父给父亲买的牛也在一个夏天的夜里,痛楚的挣扎到凌晨也走了。父亲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其三
打工热兴起来的时候,父亲和村落庄里的人一起到了北京,一年多的时候,父亲回来了,腿打着石膏,只管这样也愉快的讲着大城市的楼,车,人和事,但有时候也会从梦中溘然惊醒,坐起来抽一袋烟,半天不言语。
从此之后 父亲守着他的地皮,清晨出去,直玉轮到爬到山头上的时候才回来,村落庄里人说,父亲中了邪,在地里自言自语着,家里没人相信这个谣言。
父亲还会去附近的工地上打工,不会什么技能,只会下力气,搬砖,扛水泥,在一次扛水泥时,没站稳,从高处摔下来,头部摔骨折,在病床上的父亲很沉着,没有太多的话,呆呆的看着天花板。
而今,父亲远远的离开了那个小山村落,离开了他的地皮,住进了曾经站在山上遥望的城里。
其四
如今在这里,有太多的东西是父亲所不懂的,小商贩的买卖话术常让父亲不知所措,智好手机里的缤纷天下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头顶上飞过的无人机让贰心里一惊。
父亲被困在他的那片地皮里,偶尔离家出走,到傍晚归来时候,手里攥着一把蒲公英,一把野菜,一把柴火,那片地皮,那段光阴,才是他永恒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