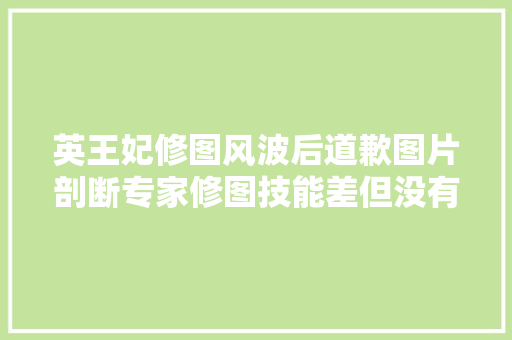——
沈妤睡了一天目前睡不着了,躺在床上病怏怏的不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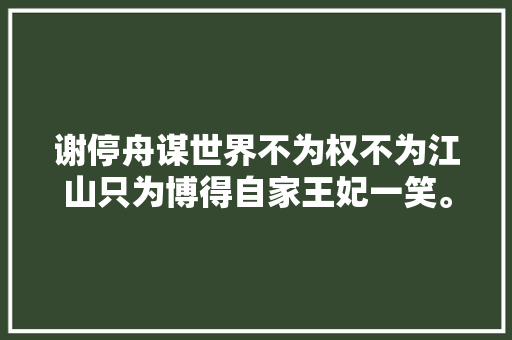
谢停舟沐浴后进屋,走到床前就着灯火看她的脸,又伸手摸了摸,“怎么不用饭?”
“没胃口。”
谢停舟刮了下她发红的鼻尖,“小样子容貌怪可怜的,还逞能吗?”
沈妤带着鼻音,不服输地说:“我是雄鹰般的女子。”
“是。”谢停舟笑了,哄着她说:“雄鹰该起来用饭了。”
沈妤逐步坐起来,谢停舟背对着她换袍子,衣裳落下,身上的疤也露出来。
这几月谢停舟总算养出些肉,看着不那么瘦削了。
沈妤指尖在他腰间的疤痕上描摹了一下,谢停舟一把捉住她的手,转头警告,“别招我。”
“我还病着呢。”沈妤恹恹地说。
谢停舟捏了把她的下巴晃了晃,“知道自己病着,那就乖些。”
丫鬟鱼贯而入,在临窗的小几上摆上饭菜。
“有些闷。”沈妤说:“开窗吧。”
丫鬟看了眼谢停舟,见他没有反对,才支开了窗。
“天开始热了。”谢停舟把粥摆在沈妤面前,“若能在立秋前办理掉宣平侯最好。”
沈妤喝了口粥,忽然侧耳听着窗外,“表面怎么那么吵?”
“在扫尾。”
沈妤愣了下,“你杀了渭王?”
谢停舟说:“我想和他好好谈,奈何他不识抬举。”
“我说呢,怎么赴宴回来就去浴房。”
谢停舟手臂支着小几靠近,“这么放心我,万一是由于别的呢?”
“别的?”沈妤拿着筷子想了想,“宴席上美酒美人,怕是‘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吧,那回来是得好好洗洗。”
谢停舟展臂,“要不要检讨检讨?”
“都洗过了还怎么检讨。”沈妤往他碗里夹菜。
“美酒没喝,美人没有,更没有白玉床。”谢停舟说:“不过听说渭王的小女生得国色天喷鼻香,但没见着。”
“听着怪可惜的。”沈妤瞧着他,“你杀了人家老爹,这还怎么博美人一笑?”
这眼神,半挑着眼皮瞧他的勾人样子容貌太少见了。
谢停舟看得喉咙发紧,一把将她捞过来,险些碰翻了小几,“牙尖嘴利,我看你精神头不错,病好了?”
“没好。”沈妤手臂抵在谢停舟胸口,“你别乱来。”
谢停舟没放她坐回去,把粥端过来看着她吃得一口不剩才放人。
表面的厮杀声响到半夜,谢停舟辰时才起来,院外早就等了一群人,要呈报昨夜战报。
谈完事,沈妤也起来了,今日精神头好了些,只是仍旧鼻塞,说话还瓮声瓮气的。
沈妤拿起下面呈上来的渭王府账册翻看了一下子。
“渭王家财万贯,王爷的腰包又要鼓起来了。”
谢停舟偏头靠过去看,就着她的手翻着看了几页,“鼓不了,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用在渭州,嫡让师长西席们切磋个章程出来。”
“妙手腕。”沈妤说:“这下渭州百姓要去世心塌地随着你了。”
“我只想让你去世心塌地随着我。”谢停舟垂眸看着沈妤。
沈妤不接这话茬,连续说正事,“其他州府的百姓怕是要坐不住了,若有人在此刻振臂一呼,州府也压不住。”
“乱是一时的。”谢停舟道:“于我们有利。”
……
京城江府
下人在院中来来往往,院子里的到处都是泥脚印。
江夫人嫌恶地避让着,“哎呀呀,怎么搞的?弄得到处都是泥。”
她举头张望,“敛之,敛之啊。”
江敛之走过去,“母亲。”
江夫人一脸忧心,“好好的湖,你把它填了干什么?”
“不喜好。”江敛之问:“母亲找我有事吗?”
江夫人点头,瞥见下人担着泥来连忙往阁下又避开了些,“过来说,敛之啊,我听说林家姑娘又来信了是不是?”
“母亲到底想问什么?”
江夫人性:“去年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林家也得以开释,你假如当真喜好林家丫头,带回家做个妾室,娘也不拦着,但是正室还是要找年夜大好人家的姑娘。”
江敛之看着江夫人,“什么才算年夜大好人家?”
“自然是家世好性子温和。”江夫人脱口而出。
江敛之想起了沈妤,前世性子温和,却因家世不好受婆母嫌弃,此生家世好,性子却不那么温和了。
江敛之无心再同江夫人多言,“知道了母亲,儿子辞职。”
“诶……”江夫人话还没说完,江敛之已抬脚离开。
林清漓去年就因大赦天下被开释,给他来了好几封信。
江敛之自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却一封未回,他已然受够了前世的日子。
林父授他学识,这情早还了,他上辈子就还了。
高进从表面回来,“大人。”
“什么?”
高进道:“谢停舟杀了渭王。”
江敛之停下脚步,“渭州那边什么情形?”
“听说谢停舟把渭王的银库都抄了,换成赈济粮发放给百姓,渭州百姓对其戴德戴德,其他州府的百姓都盼着北临王赶紧打过去。”
江敛之望着远处,“妙手腕啊,这下真是从乱臣贼子变成了正义之师,还不费半点银子。”
他话锋一转,“我书信一封,快马加鞭派人送去渭州,交给……”
江敛之顿了顿。
高进接话,“交给北临王吗?”
“交给沈妤。”江敛之笑起来,“谢停舟如今春风得意,我不喜好看他太高兴了。”
信送到渭州已是七八日后。
沈妤看完信以为纳闷,信中所书都是要和谢停舟切磋的事情,却不知怎么送到了她手里。
沈妤拿着信穿过院子去前厅,正好看见两名妇人带着一群姑娘出来。
两名妇人从未见过沈妤,但单看这衣着和气度,就猜到她是谁。
“拜会王妃。”前面的妇人连忙跪下,后面随着跪了一地。
沈妤看了眼后面跪着那群姑娘,“这是干什么?”
两名妇人对望了一眼,“奴婢是左长使府中下人,随大人来给王爷送礼。”
沈妤颔首,原来是来给谢停舟送女人的。
那些姑娘全都跪伏着,单看体态就颇为年轻,偶有几个壮着胆子举头看沈妤,眼里除了错愕和好奇便是艳羡。
沈妤抬脚往里走,走了几步,溘然停了下来。
她转头垂眸望着脚边的人,“你,抬开始来。”
跪伏在地上的姑娘不敢举头,被妇人在胳膊上狠狠一拧,这才举头。
沈妤眸光半敛,看着这张脸,既熟习又陌生,未曾想见面却是这样的场景。
前世推她入水的人,如今跪在她脚边连头也不敢抬。
“叫什么?”
“回,回王妃,民女林清漓。”
沈妤问:“王爷没收?”
妇人赔笑,“回王妃的话,王爷说王妃不喜吵闹,让奴婢把人带回去。”
“这些人准备如何处置?”
“常日是卖到妓馆,若王妃有看得上的,留下做个端茶递水的丫头也行。”
沈妤默了默,望着院中的树荫许久都没有开口。
“都带走吧。”
对付林清漓,她已无仇可报了,若没有林清漓那一推,她也不会碰着谢停舟。
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命运有它自己的安排。
妇人刚要带人走,林清漓却朝着沈妤扑了过来。
“求王妃救我。”
沈妤没有躲开,她站在原地,任由林清漓跪伏着捉住了她的衣摆。
林清漓声泪俱下,“我非家奴,求王妃救救我,我不想被卖到妓‖馆。”
那两名妇人都是人牙子,听了吓得心惊胆颤,上前去世命掰扯着林清漓的手指,边咬牙切齿地骂着。
“天杀的贱‖婢,王妃的衣裳你也敢用你的脏手碰,没得惊了王妃的鸾驾,污了王妃的袍子,你十条贱‖命都不足赔的。”
“我并非家奴,王妃!
我是被他们拐来的。”林清漓挣扎着不撒手,把面前的人当作了救命草。
“你让我救你?”沈妤仿佛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你认识我吗?”
林清漓冒死点头,“认识,您是北临王妃。”
“那我认识你吗?”
林清漓摇头。
“既不相识,那我为何要救你?”
林清漓稍愣了一下,“王妃是菩萨心肠。”
“这是我听过最可笑的话了。”沈妤俯身看着林清漓的眼睛,“我这双手沾过成百上千人的血,若是菩萨心肠,我早就去世透了。”
“王妃。”林清漓哭诉道:“王妃心慈,不会见去世不救的。”
见去世不救。
前世沈妤可正是由于有人见去世不救,才沉沦腐化到葬身湖底。
“我心慈,但我不手软。”沈妤直起身冷冷看着她,“放手!
”
妇人见王妃收了笑颜,赶忙连续掰林清漓的手指,这次用了狠劲,就算掰残了只能贱‖卖也势必要拉开。
院中的吵闹声惊动了厅中的人。
谢停舟出来时正好看见刚被拉开的女人又解脱束缚朝着沈妤扑过去。
沈妤腕上溘然一紧,被人拽着往退却撤退了半步。
扑通一声,林清漓被一脚踹到了院中,还没爬起来就咳了一口血。
“没事吧?”谢停舟半揽着沈妤高下打量。
沈妤摇头,“没事,你别动武。”
“我知道。”谢停舟扫了眼院中,眼神冷寂,“什么人都敢往王妃跟前带,这一院子人都是吃素的?”
院中下跪了一地,左长史吓出一身冷汗。
他本是渭王部下的左长史,渭王去世了,他没受牵连已是万幸。
今日原来是来送礼保个安然,没曾想却惊扰了王妃。
左长史赶紧冲身后的人摆手,“还不赶紧把她的嘴堵了拖下去!
”
又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今日惊扰了王妃,我回去立即让人备下厚礼,给王妃赔罪。”
谢停舟一句话也没说,揽着沈妤往里走,跨进门才侧头问:“这么盯着我做什么?”
沈妤抿着唇笑,“那一脚,俊极了。”
被人无条件护着的觉得真好。
谢停舟睨她,“有褒奖吗?”
“有。”沈妤取出一封信拍在他胸口,“有人给你的信。”
沈妤绕过桌子,从窗口瞥见表面的人已经被拖走,下人在清扫地上的血迹。
“那个姓林的我不管,其他的姑娘若是良家就让人放了,还有人牙子也要处置,否则拐带良家就成了风气,纵容不得。”
谢停舟刚拆开信还没看,闻言举头,“你和那个人有仇?”
“略有一点吧,不算什么大事,她曾推我落水。”沈妤轻描淡写道。
谢停舟略一思忖,想起来了,他们回京路上落水,沈妤曾和他说过,她怕水只因落过水。
“那大略,再把她扔水里就行了。”
“她彷佛也不会泅水。”
谢停舟抬着眼皮,“她推我王妃下水的时候,可曾想过你不会泅水?”
“那是……”沈妤不知该怎么和他说前世的事,就如大梦一场,对她来说实在也不甚主要了。
谢停舟道:“这事你别管,我来处理。”
“先搁一搁,说正事。”沈妤说:“你先看信吧,我已经看过了。”
谢停舟看到陌生的字迹,于是先看了题名,瞥见江敛之的名字便问:“他写信给我,怎么会送到你手里?”
“不知道呀。”沈妤想了想,“可能是怕递不到你手里,或者怕你直接扔了吧。”
谢停舟眼神浮动少焉,冷笑道:“你把男人想得太大略了。”
沈妤不明白,谢停舟已低头看信,“李昭年要下旨赏萧家。”
沈妤道:“李昭年病得上不了朝,到底是朝中的谁要赏萧家,还说不准,他一个天子自己都做不了主,挺可悲的。”
“这是离间计。”谢停舟看完信搁在一边,“如若萧家接旨,那就确定了是站在朝廷的一边。”
“你猜他们会怎么选?”沈妤撑着下巴看他。
谢停舟对着她的眼珠,心轻轻痒了一下,招手让她过来,拉着她坐在了自己腿上。
“你先替我复书。”谢停舟拿笔塞在她手里。
沈妤转头看他,“为何要我回?”
谢停舟掰正她的脑袋,下巴搁在她肩上,轻声说:“由于为夫手酸,我念,你写。”
沈妤铺好信纸,“说吧。”
沈妤的字很特殊,不是今下女子间风行的细腻规整的篆书,而是落笔流畅,行云流水的行书,笔触间颇有几分洒脱之意。
沈妤边听边写,时时问他,“这样对吗?”
“嗯,很好。”谢停舟在她看不见的地方面带笑意。
江寂故意把信送到沈妤手里,想要用这种稚子的方法来气他,也不多长长脑筋。
人是他谢停舟的,心是他谢停舟的,他江寂有什么?
想气他?他搂着沈妤让她代笔就能把江寂气个半去世,更别提两人私下是什么样子。
沈妤完备不知道两个男人之间的暗自较劲,写完晾干了墨渍准备装信封里。
“等等。”谢停舟制止,提笔在最下方添了一句,意思是身体欠佳由妻代笔。
沈妤看了差点笑出来,“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谢停舟说:“万一他不知道是我的意思呢?”
“都是用的你语气。”沈妤指着一处说:“这里还写了本王。”
谢停舟不管,淡定地折好信。
不论年纪几何,少年气不能息。
男人那点好胜心作祟,他必须赢,不仅要赢,最好能直接气去世江寂。
“你真稚子。”沈妤哭笑不得,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林清漓是江敛之的恩师之女,两人青梅竹马。”
“林清漓是谁?”
“刚才你一脚踹飞的那个。”
谢停舟想了想,说:“那你再替我添一句,就说我将他的青梅踹到吐血,又卖到了妓‖馆去。”
沈妤看着他,“谢停舟!
”
谢停舟将惧内贯彻到底,“好吧,这句不加。”
萧家军战后在赤河过了个好年。
有银子确实是大爷,粮不再是霉粮,面也是细白面。
眼下天热起来了,一眼望去关外热气腾腾。
萧长风坐在土房里,土房频年夜帐要清凉许多。
“爹。”萧河走进来。
萧长风抬了抬下巴,“坐下喝碗绿豆汤解暑。”
萧河端起绿豆汤喝了一大口,把那点燥气都压下来,“封赏的公公已经到了。”
封赏便是看他们的态度,受赏意味着仍旧是大周的将领。
谢停舟和沈妤如今风头太盛了,盛京在害怕。
他们除了想拉拢萧家军,也想用这样的办法见告百姓此番抵抗外敌,朝廷也有一份,不仅仅是谢停舟和沈妤的功劳。
这算盘,打得真是精。
萧长风颔首,问萧河:“你怎么看?”
萧河打量着萧长风的表情,却看不出什么来,只好说:“朝廷无兵,除了南大营,便再无人能压我们萧家军一头了。”
萧长风盯着萧河许久未开口,盯得萧河低下头。
萧长风道:“你嘴里吃着北临和陆氏给的粮饷,却想领朝廷的职,便宜都叫你占尽了,你当他谢停舟和沈妤是能任人拿捏的,能由着你这样陵暴?”
萧河看着碗里的绿豆汤无地自容。
往年军中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夏日哪能有绿豆汤解暑,这都是沈妤在北临拨出的军饷之外从私帐另添的,她在军中待过,知道将士们的苦。
这汤萧河是无论如何喝不下去了。
萧长风起身走到门口,“这点你不如萧川,他认了主就不会变。”
萧河自幼压萧川一头,从来都是萧川不如他,最是听不得这样的话。
想开口想辩驳,又自觉没那个底气。
说实话,萧长风对萧河还是多少有些偏幸,毕竟是嫡子。
他转头道:“现在北临势不可挡,盛京身处险境才想到了我们,一旦盛京危急解除,他们会忘了咱们曾和北临联手吗?那帮文官最是狡诈,他们会秋后算账忘恩负义,到时候我们的兵马还是吃不饱,你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呢?”
萧河咽了咽口水,“是儿子思考不周。”
萧长风望着烈日下的地皮,“封赏的,王爷和王妃知道的韶光只早不晚,但他们一贯没有来信,也没有做任何警示,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什么意思?”萧河不懂。
萧长风转头看他一眼,“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或者说他们已经笃定了只有一个结果。”
“可是……”萧河犹豫了少焉,“封赏的公公已经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
萧川远在千里之外的渭州,早就听说了封赏的公公去了赤河的,却一贯没有传来,这封赏接是没接,也无人知晓。
萧川等在廊子下,准备等幕僚师长西席们议完事他再去找沈妤。
白羽在檐下的栏杆跳来跳去,对长留怀中的乌龟虎视眈眈。
长留护得跟亲儿子似的,一口一个白哥喊得勤,梦想让白羽卖个别面。
“你跟它说没用。”萧川蹲在长留身边,“你把白羽喂饱了它就放过你的龟‖儿‖子。”
“你怎么骂人呢?”长留抱着乌龟转了个方向背对着萧川。
萧川乐了,“哥哥这是给你出主张呢,得把白羽先喂饱了。”
“没用的。”长留说:“白哥是想和它们玩。”
白羽叫了一声,萧川转头瞥见沈妤出来,随即起身见礼,“王妃。”
“我出来透透气。”沈妤看着萧川,“有事找我?”
萧川点头,“是。”
沈妤道:“这里没外人,就在这里说吧。”
萧川道:“封赏的公公早就到了赤河,迟迟没有传来,我担心……我是想去赤河一趟。”
“你想去游说萧长风?”沈妤问。
“有这个想法。”萧川迟疑道:“不过我爹向来固执,等闲不能旁边他的想法,能不能起浸染还不知道,我只能尽力一试。”
沈妤侧头看了眼萧川,“你这几日睡不好吧?”
萧川眼下挂着大大的黑眼圈,不太美意思地揉了揉后脑勺,没敢撒谎话,“辗转难眠,说茶饭不思夸年夜了,便是吃不好睡不好。”
他这几日心惊肉跳的,他毕竟出身萧氏,萧长风的选择和他息息相关,就怕结果不尽人意,让他和主子生了嫌隙。
沈妤不紧不慢道:“你不用去赤河,对你,我还有其他安排。”
“但凭王妃嘱咐。”
沈妤说:“我要你率兵拿下潞州,活捉宣平侯。”
萧川讶异地看着沈妤,半晌才回神,“王妃肯信我?”
眼下萧家军态度未明,若萧家军倒戈朝廷,身为萧家人的萧川便不再可靠。
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沈妤竟还乐意让他领兵。
萧川心口狠狠震了一下。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沈妤摸了摸白羽的毛,“我们曾并肩作战,你虽姓萧,但我眼里你与他们不同。”
“王妃,王妃。”长留小声喊着,指了指沈妤身后。
沈妤转头见萧川的表情,不由笑了,“你和常衡待久了,怎么学他动不动就掉眼泪?”
“没掉。”萧川吸了吸鼻子,却还是忍不住红了眼。
士为心腹者去世,萧川一个大男人,也不由为这样难得的信赖热泪盈眶。
他吸了口气,忽然提袍单膝跪地,“末将愿为王妃而战!
”
这是一名将领的承诺。
“萧川。”沈妤看着他,负责道:“别这样看轻你自己,你是为天下人而战。”
廊子下的风都是热的,沈妤看着萧川拜别的背影,脸上带了笑。
她朝白羽勾了勾手。
白羽张了张翅膀想跳到她胳膊上来,刚起跳就被一只大手摁了回去。
谢停舟站在沈妤身后,悠悠地说:“萧家这一代,总算还有个铁铮铮的男人。”
“我总算没有看错人。”
沈妤收回视线,瞥见白羽闹脾气地扑腾着翅膀。
谢停舟抬手接了白羽在手臂上掂了掂,说:“沉了不少,今日起断了它的肉,让白羽自己出去捕猎。”
天热白羽也犯
长留在檐下应声。
谢停舟打了声哨,刚遭受了无妄之灾的白羽展翅飞向天空,又被烈日烫回了屋檐下,目光不太高兴地盯着谢停舟。
他们停在渭州,沈昭不日就将带着萧川和常衡去潞州攻打宣平侯。
沈妤道:“辎重先行,动一次兵,就要耗费数万军饷。”
谢停舟站在沈妤身侧,“好在各州春耕顺利,若无旱灾,今年当是个丰收年,该花的要花。”
“赤河迟迟没有,你怎么看?”沈妤侧头看着他。
谢停舟垂眸注目着她的眼睛,“没有便是好,眼下最急的该当是盛京的那帮人。”
“你和师长西席们切磋好了吗?”
“嗯。”谢停舟道:“眼下还缺一样东西。”
沈妤:“什么?”
“破笼之刃。”谢停舟揽着她看向远处,“我要天下豪杰齐聚,助你我齐破樊笼。”
谢停舟眼下最须要的不再是兵,他须要人才。
铁蹄踏过之处百废待兴,须要得当的人来管理。
大周最初的衰落便是从最底下的官员开始糜烂,他们不能重蹈覆辙,必须把数州百姓的生存交托在得当的人手里。
可是谢停舟虽福泽万民、众望所归,但说到底还是谋朝篡位,如今投奔而来者多是贪利之人,可用者少之又少。
武将手握刀刃,但文人手中的笔同样是杀人的刀刃,一个诛身,一个诛心。
要想师出有名,谢停舟须要挑起文人间的风浪,让自己和大周的天子站在同等的位置上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