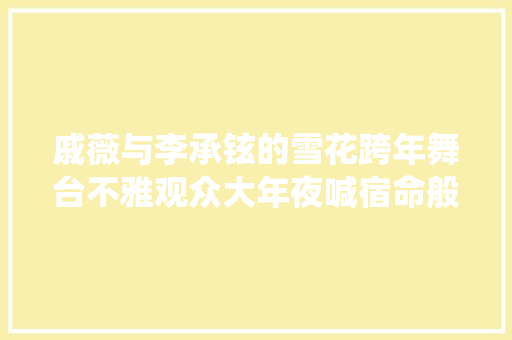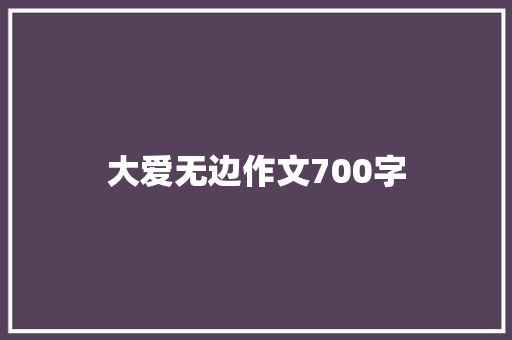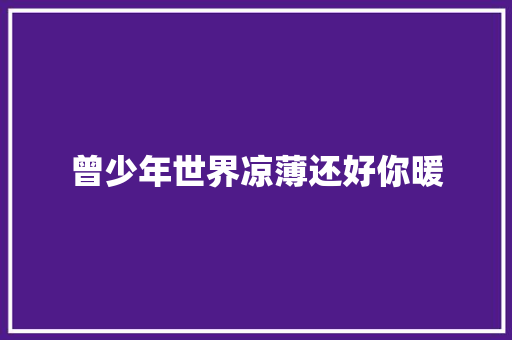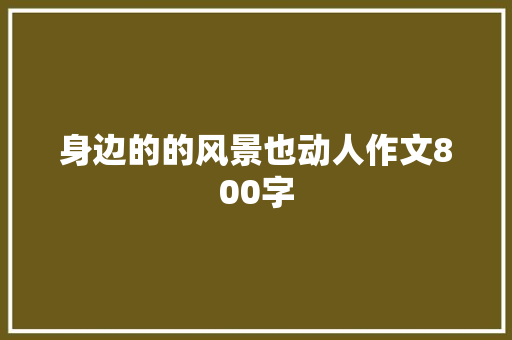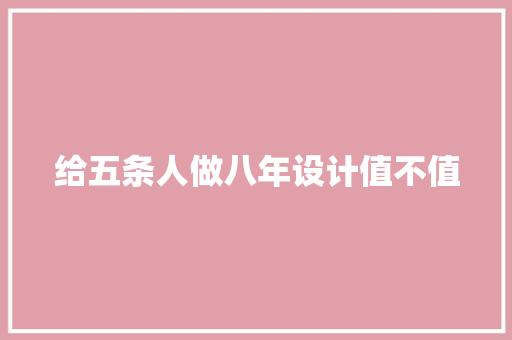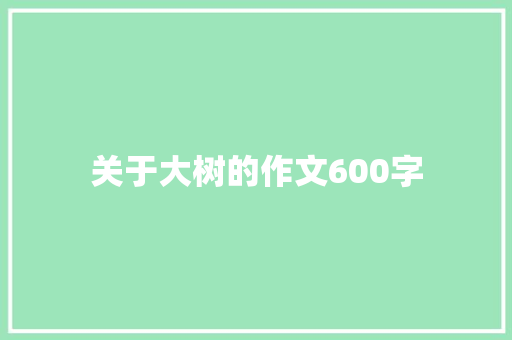“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可愉快了,没想到竟成了永别。”刘真骅说。
把“创作谈”放在 《大众日报》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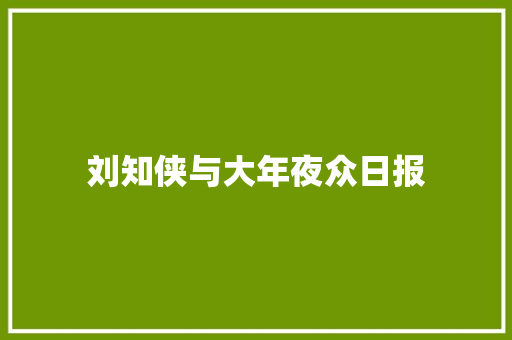
刘知侠是河南卫辉人。6月8日,陪刘真骅老师来到知侠故里,拜会刘知侠墓,听到好多关于刘知侠的故事。
刘知侠生于卫辉市庞寨镇柳卫村落,这个村落因柳毅传说而得名。刘知侠的旧居靠近柳卫村落柳卫完小校门口,已翻盖,目前是他的侄孙住着。见到了刘知侠的侄子、72岁的刘国安和侄孙、48岁的刘学军。刘学军说,自己七八岁时见过大爷爷,看过电影和小画册《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自幼家贫,跟随父亲在村落边道清铁路打工、捡煤核,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刘兆麟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以精良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
1936年,他因家贫于卫辉一中求学,到浚县教书。柳卫完小校长陈鸿溪编纂《柳卫村落志》时,曾记录了当年刘兆麟的学生张克礼老人的回顾,个中一段是:“兆麟在浚县教书,每学期开学前都要带学生到现在的卫辉市李源屯取新教材,一个来回25公里路。路上有一段是道清铁路。兆麟对我们说,我能扒火车,大家书不信?学生们都说不信。那时的火车烧煤,速率慢,假如现在的话,谁也不敢吹牛。当时兆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随着火车紧跑几米,然后,一个飞跃,“噌”地扒上了火车,还时时向同学们招手。他随着车跑了50来米,学生们都喊,‘中了,老师,下来吧!’他跳下火车,来到学生身边,还不忘提醒,这事儿可不能模拟。你们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否则,摔伤了可别找我。”陈鸿溪对说,知侠住在铁道边,对铁路熟习,以是写《铁道游击队》有着得天独厚的体验。
《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重版。小说使刘知侠一举成名。应读者哀求,1955年10月19日,知侠在《大众日报》丰收副刊刊发了《我若何写“铁道游击队”的》一文,文中说:“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这天寇屈膝降服佩服后,他们第一次的新年会餐。在庆祝胜利的丰饶的酒席上,正像我小说二十四章里所写的那样,他们因此古老的办法和气魄,来吊唁自己已去世的战友,把一桌更丰满的酒菜,摆在捐躯战友的牌位前边。他们平时饮酒都要猜拳行令的,我小说上写的‘高高山上一头牛’的酒歌,便是和他们一起饮酒时学的。可是在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都沉默地喝闷酒。隔着酒桌,望着捐躯战友的牌位,眼睛就注满了泪水。当时的情景,深深地冲动了我。也就在这次会餐的筵席上,为了吊唁去世者,他们有两个发起:一个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议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再一个便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业绩写成一本书留下来。对付这后一个建议,也便是他们所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当时是答应下来了。因此,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出自我个人对他们的敬爱,同时,由于他们的委托,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责任了。”
“创作谈”清楚地向读者交待了这本书是亲历过战役洗礼的老兵爱慕写的“委托书”。
“红嫂”形象一点点在版面上清晰起来
1937年夏天,刘兆麟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便奔赴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遂改名痴侠,后又改名知侠。1939年5月,刘知侠抗大毕业后,又留校学习军事专业。学习结束后,刘知侠随分校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分配到抗大山东分校文工团事情。查到刘知侠最早在《大众日报》上揭橥的文章是1940年3月13日的一篇短评《藏在妇女事情后面的暗影》。
文章写的是鲁南群众运动正开展,时常遭受到潜伏的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毁坏,妇女事情更易受到执拗分子等旧势力与汉奸们的打击与毁坏。“当我们在××等地将妇救会成立了,她们就造谣言说:‘参加妇救会会被提去当女兵的’!当然这虚制的谣言,由于事实的证明,是不难被粉碎的。但是她们接着又无耻地散布威吓的言语:‘谁要到夜校去就烧她的屋子’!‘再要上夜校,晚上叫她吃炸弹’!”“的确,这种威吓影响了夜校的上课,这时候我们妇女事情者便更耐心去说服那些被吓住的大娘和大姐们,最初她们确是被吓住了,如××的夜校,以前每天四五十个妇女来上夜校的,逐渐减到只有十七八人来上课了,但是经由我们妇女事情同道的努力说服和积极事情,——纵然来一两个人也不灰心地讲课,接着被说服的大嫂嫂老婆婆大姐姐们,她们都又陆续地来上识字课了,她们都逐渐觉悟到:这是可恶汉奸们造的谣言!”知侠写出了组织“识字班”的困难,文章结尾鼓励大家武断冲破各种恶势力的曲解和中伤,发挥妇女的伟大力量。
1940年7月13日,知侠又揭橥了人物特写《她母亲一样的爱着八路军的战士》,文章写的是东安乐的妇救主任,她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一个那么慈祥的老太太。“有一次,一个同道病了。她匆忙在厨房里,煮药烧茶,一天做四五次饭,端在他的面前,妈妈一样地安慰着他。她的关心和慈爱是那样地纯挚,她不是为的‘积德积善’,她很明白抗日的道理,而爱着大胆的抗日将士。她不但爱我们这几个,而且爱着先后到这里的每个八路军的同道,像爱着自己的儿子一样。”
1940年8月7日的《大众日报》上,揭橥了知侠的《筑成抗战的新堡垒》,刻画了在太平安庄战斗中,一位年夜胆的母亲在儿子捐躯后的表现,知侠是这样写的:“随着,是这次战斗捐躯了的张大的娘上台说话了:‘我的大儿子杀鬼子捐躯了,为了国家为了大家捐躯了,可是,这是光荣的!做娘的,我当然难过,我还有两个儿子可以打鬼子!早晚要打干净鬼子,看看谁能拼过谁!’台下是一阵雷动的掌声呼声:‘热心抗战模范的张大娘万岁!’”
共产党、八路军何以能在沂蒙山区坚硬的山岩上扎下深根?缘故原由可能很多,但刘知侠当年写的文章,给出了答案:首先把压在最底层的女人解放了!肃清“半边天”头上的乌云,让女人找到做人的自由。凝望女人困难站起来的身影,我想起了一句话:母亲是产生希望的希望。
1961年7月9日,《大众日报》丰收副刊揭橥了知侠的短篇小说《红嫂》的一章。《红嫂》后来被改编成京剧《红云岗》,毛主席看了,评价了四个字“玲珑剔透”。
知侠在《大众日报》上揭橥的作品,一个光鲜的特点是关注妇女命运,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了女人地位,共产党、八路军让山里的女人有了肃静。在连天的炮火中,女人们终于站立起来,她们义无返顾地把子弟送上沙场,用甘甜的乳汁喂伤员 ,这在过去看来,切实其实是惊天骇俗的事儿,这站立起来的女人的举动,让人间弥漫温暖的光泽。
一个个“红嫂”形象一点点在《大众日报》版面上清晰起来。
刻画出区长的联络力
1942年5月25日,知侠揭橥了一篇很有生活气息的特写《归来者》,一开篇就像小说:
四月的春天。
贛榆县城里的伪军哭丧着脸,像笼里的鸟样地跳着,县城外五里路的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天下了。由于离城七八里路的×庄,抗日的区公所依然可以在那里照常办公。
开会的小屋里,被薄薄的烟雾弥漫着,保长含着烟管,望着讲话的张区长,他的眼睛笑眯着,脸皮黄黄的——他的事情太辛劳了,他吃的是煎饼,讲起话来是那么“和道”,每句话都说到人们的心里。
“砰!村落外的哨上响枪了。
“你们先在这里,”区长提动手枪,“我出去看看!”
刚一出门,一个区中队员跑进来,气呼呼地报告着:“庄东头创造了汉奸!”
接着把汉奸捉住了。多嘴的张大爷在街上传诵着:“区中队捉住了汉奸。”李奶奶含着泪从家里跑出来,拉着一个区中队员的手:“在哪里,叫我去咬他两口!解解恨!”她拍动手掌对着一群女人又在诉说李大爷去世得若何惨……
“同道!用零刀割他……”这是遭过汉奸队害的人的声音。
可是区长却把汉奸拉向另一个屋子去了。站岗的区中队员并没有让喧华的人群进院子。
张区长很耐心地做伪军的事情,希望他们早日回到公民的军队中来,末了,将两个伪军放了。群众不干了。
张区长透过薄薄的烟雾,笑望着每个庄稼人朴实的面孔,很和道的在讲话了:
“……假使有的汉奸转变主张了,乐意过来打鬼子,那末咱为啥杀他呢,他掉转枪杆不多一分杀鬼子的力量么?……”
“别上他确当吧!区长,他俩一去不转头又怎么办呢?”一个中年人站起来问。
“那也不要紧!只要他们明白了抗日的军队与政权是不杀他们而优待他们的,借着他们给那些不愿当汉奸的人开一条活路……”
“啊!”大伙点着头。
果真,第二天夜里,红鼻头的青年,和其余两个,带着家属,超越城墙跑出来了,听说三个归来者还带出三把匣子枪。
知侠娓娓道来,塑造了一个富有联络力的区长形象,没有多余的废话,全是用事实来描述事实,是一篇难得的战地小品。
这不是毁坏,这是创造
知侠的、通讯、特写都写得很接地气,真实可信,比如1940年6月13日,《大众日报》刊发了他的《给抗日军送武器》,写的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杜家庄的七八个老乡相约着把十支步枪扛到八路军××营第三连来了,像到自己家里去那样安闲自然,满脸挂着微笑!
在墙角下放着的十支步枪,和在烟雾里闪着光亮的窗台上的一些子弹,这是他们以前买下来打强盗用的。鬼子扫荡鲁西南的,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杜家庄就开了一个全庄老少大会,谈论了一天,决定赶紧组织自卫团合营军队打鬼子,同时决定把有多的枪送十支给八路军,赠予给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能打鬼子的八路军。
看似大略的送枪送子弹的举动,但是他们开了一个全庄老少大会,谈论了一天才决定。老百姓是慎重的。他们看准八路军是打鬼子的,才肯把枪送到他们手上。
1941年9月7日,《大众日报》揭橥了知侠的特写《夜征的工人队》,写的是为了反“扫荡”,二十多个石匠自告奋勇要去毁坏公路上的石桥。
“这是我们修的,现在还是由我们来拆掉吧!”
人们一点也没有忘却,这座桥是韩复榘叫建筑的,同时也便是他背叛了山东公民,从桥上兔脱了,并让鬼子的铁蹄,从桥上踏过,来屠杀筑桥的人,来屠杀山东的老百姓!
“这切实其实是不法!把它拆毁吧!”
天一黑,村落后挤满了黑洞洞的人群!
斧头、镰刀、红缨枪、大刀、木棒,还有石匠所特有的大铁锤。粗重的武器合营火烈的心,这支巨流向着公路的方向提高。
巨流分股向公路、大石桥、电线杆冲去,没有等哨音发响,大家便生气勃勃地动起来了。
从玉轮刚爬上山头起,公路上开始涌现了宽阔的深沟在斧锯锵锵的声响中,电线杆一根根地倒下去,电线一盘盘地收在腕上。老张拧了把汗,呼唤着挥舞镰刀的老李。
“把这送给抗日军!”
大石桥上迸着火星,发出隆隆的音响,铁锤划着夜空,汗水点在将折断的石板上。……
腰折的电线杆一根根地躺下了十几里路,公路的创伤蔓延到××村落的东头。大石桥上已听不到响声,桥身张着宽大的缺口,桥石沉在急流的水底,自此往后,它再不会遭受残暴的敌骑的践踏了!
刘知侠在文中点题,这不是毁坏,这是创造。
堪称经典的小特写
淮海战役打响,刘知侠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机关报《华东前哨报》特派。1949年2月17日,知侠在《大众日报》“淮海战役琐闻”栏目上,揭橥了一篇特写《黄教导员与引导》,这篇特写堪称经典。
当年解放军“济南第二团”一营,一夜行军九十里,进驻固镇西某村落。这一带的百姓受到国民党军的摧残,一听到军队进庄,也不问是什么军队,连仅留在家里守夜的老汉、老婆婆都躲藏了。
一营到小村落时,看不到老百姓,军队刚住下,又接到团部电话,准备调防。为减轻战士们的疲倦,黄教导员自己先起来,准备领几个通讯员先到指定的庄子看屋子,但是找引导带路,成了麻烦事儿。通讯员走遍了庄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说是从永城逃难来的,不认识路;后来,又找到一个跛脚的青年,他说他腿上终年夜疮,又有羊癫疯病,末了找到一个老大娘,她说路不熟。黄教导员对他们都是和颜悦色地商量着,当他们说出情由几次再三表示不能带路后,黄教导员也无可奈何。溘然有人想起:军队进庄时,还看到庄东头有一个老大爷在挑水。不一会儿,通讯员就把这老大爷请来了,他蹲在灯前,向黄教导员阐述自己的难处:
“我的腿要能走,我就去。”
“你的腿真不能走吗?”
“是呀!说着是:……”老汉要赌咒了。黄教导员沉思了一下说:“给你马骑,可以吧?”听说骑马,老汉一怔:“我骑不好,也没那个福。”
“我们扶着你上去。”
“弗成!马不诚笃可坏了。”
“给你牵着走。”
老汉对黄教导员仍连连摇头:“我真弗成呀!”
“送到后,我们用马再把你送回来。”
这样,老汉没话说了,只半信半疑地呆望着油灯,黄教导员认为他已经应允,就高兴地嘱咐通讯员:“快走,把马牵来。”
一出屋门,老汉就被扶上马,通讯员前边牵着,黄教导员后面随着,按着老汉所指定的方向,向宿营地走去,老汉在立时低低地说:“哪有这样好的军队。”
到了目的地,黄教导员正要实行自己的诺言,叫通讯员牵马送老汉回去时,老汉匆忙上去回绝说:“别!我能走!我能走……刚才是我……”转身便向回家的路上走去。
短短几百字,就活灵巧现地还原了一个军民关系场面。老百姓先从不相信,到半信半疑,到末了全部相信,经由了一个思想斗争过程,比较、鉴别,担心、害怕,欣慰,都写进去了。一个小故事,就把军民鱼水关系是怎么形成的,阐明清楚了。
《大众日报》给知侠供应了平台
刘真骅说,《大众日报》给知侠供应了平台,解放前如此,解放后又刊发了他的好多作品,除了《红嫂》,还有描写老区公民社会主义培植的随笔《旧沙场 新战役》等。“知侠平反后,陈沂同道,便是《大众日报》老社长,当时担当上海市委副布告兼宣扬部长,想请刘知侠到上海担当文联领导,那阵子,山东文联还没有规复。陈沂同道指示,请刘知侠带着夫人一块来上海,我和刘知侠就去了,住在东湖宾馆。陈沂的夫人叫马楠,上海文艺局局长。最热闹的是,那天晚上,吃完饭,陈沂跟知侠谈,马楠跟我谈,谈的实在是一个事儿,让我说服知侠到上海事情。马楠跟我谈的目的是说服我,跟知侠一块来上海事情。知侠回来一说,我说知侠你现在六十多了,如果你五十岁,还可来干点事儿。都这把年纪了……末了我们就没去上海。刘知侠跟陈沂的友情是解放前在大众日报社那时候结下的。”
刘真骅回顾,刘知侠去世后,为了整理《知侠文集》,她找到《大众日报》老总编朱民的夫人余林,请她帮助查找解放前刘知侠在《大众日报》上揭橥的作品。余林曾担当读者来信组组长。“我找她的时候,她退休了。大姐高度近视,戴着眼镜,趴在报纸上用放大镜找,把散落的稿子一点点凑齐了。旧报纸灰尘刺鼻,还有霉味,翻一上午双手都是玄色的,我们一起翻了一个星期,我想起余大姐就想掉眼泪。”
本报于岸青在整理报史时,创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大众日报社传唱的一首歌叫《困难是炬火》,她多方考证后,写出《探求<困难是炬火>》一文,于2012年7月11日揭橥在《大众日报》,在文章的“补记”中她说:“第二天晨,苗得雨来电,他查到了确切的资料,《困难是炬火》这首歌为1941年11月,日寇‘扫荡’沂蒙根据地最为艰巨的期间,创作于沂南布袋峪,词作者刘知侠,曲作者艾力。”
《困难是炬火》的歌词是:
困难是炬火把我们磨炼,
我们是坚钢越炼越倔强。
困难是我们的,
胜利也是我们的,
艰巨是我们的,
胜利也是我们的。
谁能熬过这艰巨斗争的磨炼,
谁就能得到末了的胜利。
谁能熬过这革命斗争的磨炼,
谁就能得到末了的胜利!
这是艰巨的开始,
这也是胜利的开始,
再艰巨我们要挺进!挺进!
挺进到胜利的来日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