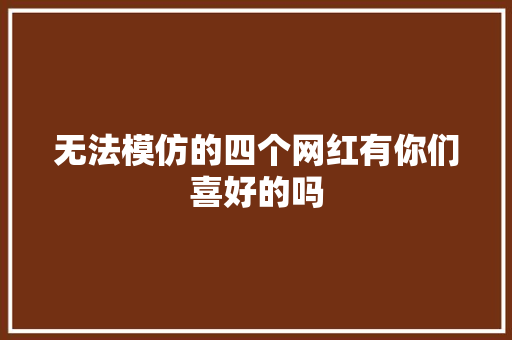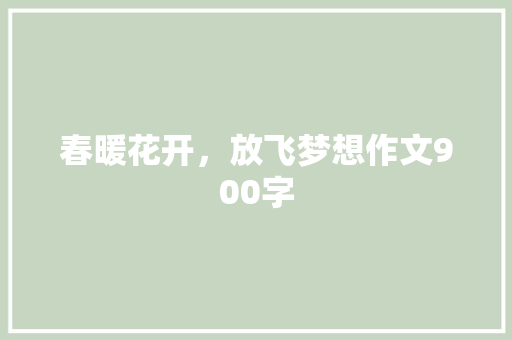小老虎喜好闲步,他“坐不住”,乃至在家里也闲步。从北京搬到上海,是由于以为上海是一个更适宜闲步的城市。不久之后疫情到来,他回到北京的家中和父母待在一起,很快就对不能出门的生活感到厌烦。他决定去日本,以为出去一趟再回来疫情就可以躲过去了。没想到一去便是三个月,从最开始二十多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牛杂碎到后来餐厅、博物馆都不开门,疫情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在环球范围内爆发了。
去年夏天,小老虎难得参加了一次综艺节目,是帮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助演。更多的人因此认识了小老虎,更多人开始关注所谓的小众音乐,音乐节的门票开始猖獗涨价。说唱和摇滚,借助综艺和商业,逐渐从亚文化走向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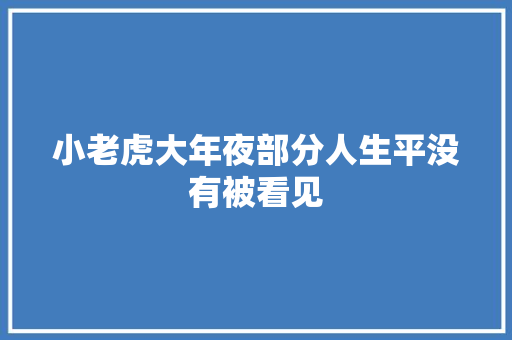
我不经意间提起最初喜好小老虎的缘故原由,是一首叫做《无人叫好》的歌。在这首歌里,他唱道:“大家都成了编剧、演员和监督,大家都化了妆、上了场、走进灯光,大家面面相觑,谁来鼓掌?”本日的小老虎提起那首歌,竟感到时期久远。嘻哈音乐曾经不那么被人关注,但是现在,统统都不那么一样了。“现在这个时期给你一种假象,彷佛你很主要,你是时期弄潮儿。但是我也以为信息爆炸至此,能有机会,让自己相信的东西被人看到,是一种幸运。”
他和朋友互助了一个叫“说统统”的项目,约请普通人一起通过说唱的办法来表达各自的生活。“说统统”最开始在微信小程序中进行,后来来到线下。他说,就这像是一个拆盲盒的过程。在“说统统”中,小老虎考试测验抵达他人的内心,瞥见一个个人。这些来说唱的普通人,讲点自己的故事,纵然不带来什么,大概什么没发生,没什么叫好,但是总是会产生一点心怦怦跳的觉得。最近北京一场演出当中,有个说唱爱好者上了台,迟疑半天,说了一句话:“我就看着你们,我以为我离开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像你们一样站在这打开自己。”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起来。
小老虎感到很激动,他以为大部分人,可能生平没有被太多人瞥见。”但是在短短的一两分钟里,我记住了他们的嗓音,他们的故事。”
2021 年可能是他最勤奋的一年。和朋友土摩托一起跑了几个城市,放映《说统统》记录片。从 4 月到 7 月,他在上海 TRI 第三空间做一场叫做“点动怒,伸开嘴”的系列演出。他想考试测验更加纯粹地讲故事,像最初那样围着篝火把故事唱出来。
对付“火”的兴趣,来自几年前他在火人节上的直不雅观感想熏染。“我越来越以为体验这件本家儿要,没法只凭逻辑去相信。当我亲眼瞥见几万人围着篝火安静地哭泣,放弃各自的身份、放弃平时的烦恼。真的慢下来,谈天说地,火光在眼睛里闪烁。我能看出音乐的纯粹的魅力。”
一样平常的商业音乐节依赖扩音、专业的设备和舞台,而火人节都是 DIY。没有金钱,都是交流。小老虎说,没有电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革。“手机的旗子暗记不太好,最好的便是一把火,一张嘴。我能知道他们都在这里。”
第一场演出叫做《火中的鸟鸣》,现场他说了一个饕餮蛇的故事——他有一天走在路上,手机屏幕摔坏了,想起路口有一个修手机的人。可是修手机的人对他并不理睬,专注于手中的饕餮蛇游戏,直到城管要把他赶走的前一秒,他把手机交给小老虎,说:“兄弟,帮忙照顾一下它,这也是生命。”小老虎接下这条生命,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善于照顾饕餮蛇的朋友,并把手机交给了他。没想到饕餮蛇越来越大,从手机到平板到投影,饕餮蛇一次次超越屏幕的边界,朋友被饕餮蛇支配着,眼冒金星,生命垂危。直到他的朋友 Howie Lee 前来“指路”,他说:“蛇属于大自然,要让它生活下去,最关键的是树林。”随即从屏幕中抓出饕餮蛇,放入头顶的发丛。
这个像是出自卡尔维诺之手的、充满隐喻的故事让我听得入迷,科技、希望、动物、自然,疫情以来很多人的思考彷佛都搜集在了这个故事里。小老虎说他的朋友们也以为这是整场演出中最精彩的一个部分。他说,这个反馈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由于这个部分音乐很少,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故事,一次比较纯粹的讲述。
在当代社会里,我们还可以创造性地生活吗?小老虎大概会帮我找到一些答案。我们发言的过程中,“危险”这个词频繁从他口中跑出来。在他的词典里,“危险”不是一个负面词汇,而是意外的温床,也是某种火光。
作为说唱歌手,他的确不太范例。喜好诗歌、文学但不喜好被称为说唱墨客,喜好音乐但不喜好被商业化、标准化的演出办法,喜好创作中的自由但并不追求生活中的放浪形骸。那种“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形象,小老虎以为大概已经由时,或是投射着我们对付创造力不切实际的想象。他以为生活可以过得平常一点,在创作时得到自由就够了。“如果由于事情和生活的情形,以为(创作)是生活以外的一件事情,乃至远得像外星球一样,这很让人遗憾。”
“别睡得太晚,起得太晚。”他这样对我说,“我紧张想,现在的这些人能有多离经叛道呢?”
《出色WSJ.》:最近你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系列演出“点动怒,伸开嘴”,是不是和之前的演出有很大的不同?
小老虎:我一贯有一个想法,便是想让演出更加戏院化。由于我对传统的 hip-hop 演出,比如一首歌接一首歌的形式不是那么感兴趣。我一贯想考试测验这种偏故事性的,或者有一个整体氛围的演出。可能也是我坐不住,我不想逼迫别人坐在一个地方。我希望整场大家都在一个气氛或者场景的引领下走来走去。
这场演出更多地依赖文本和讲述,而不是音乐。实在真恰好的讲述也不会让人走神。或者说,可能真的认负责真地讲一个故事,还是有魅力的。我觉得现在也是故事稀缺的时期,虽然各种手段变多了,但是很难讲好一个听起来就不错的故事。
《出色WSJ.》:为什么叫“点动怒,伸开嘴”?
小老虎:火是一个核心的观点。这几年我对“火”越来越感兴趣,可能紧张是篝火的觉得。大家围着篝火,回到最初讲故事的场景,人和人相处的实质。由于我在火人节就体会过这样的东西。
火人节有两个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火人(一个人的木造像),一个是庙,然后庙平时它便是一个空间,每年主题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一个中式的塔,有的可能是一个繁复的巢穴,反正每年都挺艺术的。然后常日是大家到里边去冥想和寄托哀思,你可以把一些亲人的遗物放在里边作为纪念。以是你会看到里面摆着各种日记本、丝巾、照片,都是一些过去的回顾,但到末了一天它们会被付之一炬。
火人节的倒数第二天,会烧木头的人,烧这个人的时候是狂欢,几万人全都围着这个东西。然后有上百辆、上千辆花车都在那,音乐震天响,还会放礼花,大家就看着这东西就在闹。但是到末了一天烧庙的时候,还是这么多人围着,就没有那么多的喧华的声音,大家都在静默,然后有人开始哭,像传染似地散开,然后你就听到这旷野当中充满了模糊的抽咽。
我以为这哭不仅是悲哀,它是一种沉浸在此刻的觉得,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情绪。你就在这个时候就尽情地去想一下这件事,体会一下生命的逝去,陷入到一些回顾当中去。我以为这是挺主要的,由于我记得当时我生命中有几次主要的亲人、朋友的离世,当时那一刻乃至都没有去反应这件事情,听到以为震荡或者可能立时要出门了,要去赶飞机什么的,有一次还在跟自己说,我没办法,我得连续往前走,机场的这个路是停不下来的,拖着箱子往候机大厅里进去的那种。但是可能过些日子,溘然一天中午吃着吃着饭就想起这个人来,把筷子放下,当时就哭了,哭得吃不下饭了。
《出色WSJ.》:我特殊能理解你说的沉浸在此刻。实在前几个月我去看了一次生理年夜夫,由于当时我觉得非常焦虑,到了会不经意掐自己的地步。我的生理年夜夫当时就指出了一点,说我的思想和身体没有在同一个当下,我身体在此刻,可能脑筋里却在想很远的事情,以是她给我一个最紧张的建议,便是要去感想熏染当下这一刻的这个天下上在发生什么,真正意义上去关心你的朋友在想什么,而不是现在我们在谈天,我一直去想下个星期我要干什么事。
小老虎:我这些年也越来越以为体验、在场这件事特殊主要,就像有些事我没有办法只凭逻辑去想象,我得要觉得到实实在在的刺激。就当亲眼见过这几万人,就在旷野当中围着火,一起哭泣,没人说话,这么安静,这么纯粹的场景,也见过这些人放弃了身份,放下了他的日常烦恼,跟你坐在火边,真的慢下来,谈天说地。然后火光在眼睛里闪烁着,听你的说唱或者你的故事,类似禅定的那种觉得,但又没有那么玄乎。
那种气氛和那种专注中,能看出真正的、纯粹的音乐故事和即兴的魅力。在那个时候就让我对火这个东西格外的感兴趣,真的就相信了,以是我以为有这种体验。“火”便是来源于此。乃至于也不一定是当时就彻底地被这个东西震荡和改变了。有一些意思你在当时没有明白,然后这意思后来逐步转变成灵感和成为你后来非常相信的事情,大概是这么一个觉得。
《出色WSJ.》:在当时的场景下,你感想熏染到音乐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小老虎:我以为它和一样平常的音乐节比较大的差异,就在于一样平常的商业音乐节大多是依赖职业的演出,专业的舞美、灯光、舞台。火人节的统统都是 DIY 的,你所有的吃喝拉撒,都得自己准备,自己去整顿你的残局,然后演出更多的是自发的。它便是在荒原里,以是实在发电本身便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如果是一个商业音乐节,你要到一个边远的地儿,可能准备大量的发电机什么之类的。阔别城市,我以为是有考虑的。没电的时候,人和人便是的关系也变了。你有个小音箱,或者最好是能弹吉他,唱歌都不太依赖电器,最好的实在便是一把火、一张嘴。你可以唱,你可以讲述,你可以模拟一个敲击,你也可以学风,学动物。你的声带、你的脑筋和你的呼吸,还有你的肢体,可以做的事情实在是挺多的。
最好的还是大家在那时候就比较沉浸,由于手机可能旗子暗记也不太好,大家便是在这待着一个人干什么,其他人很负责地对待。当他负责对待的时候,他也有别的觉得,也给你一种不一样的鼓励。给我的觉得是比那种一场专业的演出,乃至于是那种万人的音乐节更好的体验。由于我能知道他们都在这了。
《出色WSJ.》:你是不是现在有些迷恋那些原始的东西?还是一贯都是这样?
小老虎:一方面我是个所谓的科学主义者,我不以为“原始”意味着真善美和更高的聪慧。但在这种偶得的瞬间里,能够得到一些现在比较稀缺的把稳力或者人真正放松的状态,我就会以为很充足。有的时候,我也不敢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比较过去便是一个完备的进步,尤其对付一个日常的人来说。就像是我们如果可以真的花韶光去看书,去获取知识。互联网里有多少东西?但是我们又有多少韶光会真花在这上面?
《出色WSJ.》:你有没有觉得到疫情之后身边人的改变?大家是不是对自然有了重新的感悟和热爱?
小老虎:我的朋友李厚辰,在他的播客“翻转电台”里有一期讲《心灵奇旅》,里边他有一个不雅观点,我以为有点意思。便是那哥们末了看着叶子飘下来,展现出自然给人启迪的浸染。李厚辰说,这个东西的门槛实在非常高,不比你欣赏艺术低,比如你听个交响乐大概有一些门槛,但是你真的到森林里感想熏染到了一些格外的启迪,尤其是像涉及到生命,涉及到这种有点宗教的、终极启迪这样的东西,它实在是很难的。我是赞许他部分的说法。
我们看到的这些宗教故事,像《悉达多》,包括毛姆的《刀锋》,这些故事里的角色可能都是在某一个日出时候或者在大自然里,溘然感想熏染到了彻底的喜悦,然后他看万物都是那么的故意思。他以为眼睛像被蒙蔽了一样,重新睁开了看这个天下。这是很难的,就像《心灵奇旅》里那哥们坐在台阶上看纽约街道的落叶,他是经历了死活,经历了很永劫代的求索,带着他所有对艺术的神往、失落望还有去世亡,夺复性命,可能还要再次失落去的心情。他就看着这些东西,他那一刻可能感想熏染到了一些东西,我以为这确实是有一个语境跟一个根本。
现在人们可能对付大自然有一种神往?我以为由于出不去,再加上长久的城市生活,现在时髦的轻奢的这种露营,户外的生活,确实可能跟消费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且说到自然,你说什么叫自然?尽可能的保持它的危险性跟原始性,实在这是自然。但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这种有点自然的觉得。而且真的自然,真的舒畅吗?对大多数人来说大概反而是个障碍。
《出色WSJ.》:我最开始喜好你的音乐是由于听了《无人叫好》这首歌,在这首歌里我听到了一种对自我中央主义的质疑。大家都当了演员,编剧和监督,然后没有人做鼓掌的角色。彷佛也有很多人会把它解读成嘻哈音乐的落寞。你在最初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小老虎:实在有点久远,想不太起来了,也不是一个那么逻辑性的感想熏染,我以为是一种感情。但如果现在再说落寞,和当初的落寞已经很不一样了。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解读成一个娱乐化的时期,或者说说唱它本来便是一个极其小众的东西,但是经由成本、娱乐工业和机缘变成了一个大众领域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没问题,就跟你曾经喜好的某一部小众的电影、小说,它有一天由于什么事情被推到了大众的层面,好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一样,这是特殊正常。我以为才是这里边真正的意思,便是说彷佛谁都想去当这个时期的弄潮儿,而现在这个时期也给人一种假象,彷佛我真的就很主要,我这么主要,为什么别人就没有看过我?
另一方面,信息爆炸至此,能有机会被人关注一下,确实也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我以为“说统统”也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即兴说唱人的思维和口头的这种艺术,它能够到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人的这种创造性到底能够怎么样。但在 TRI 第三空间的演出或者是“说统统”的放映结束后的 open mic,大家都可以上来说会儿。那个意义便是瞥见一个人,实在便是让他们用身体参与音乐,更主要的是,便是想要说点什么,想要让别人瞥见他。
我以为大部分人可能生平没有被太多人瞥见,之前这个被瞥见的权利已经从明星“下放”到了选秀节目,但现在有了选秀之后依然没有办理,大部分人想被人瞥见,我以为不一定在电视上,就台下四五个人瞥见那个人,我以为这是很主要的。
《出色WSJ.》:这种被瞥见是不是跟被放在全民关注的焦点上还挺不一样的?更像朋友之间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社区里的一个人的生命被大家看到,而不是被符号化或者被成本包装成一个抽象的东西?
小老虎:我以为它是有差异的,而且它便是即时的,它便是一下,没准不带来什么后续。有的后续大概便是你下来了后会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很认同你,乃至咱们交个朋友。但大概就什么也没发生,没准也没什么叫好就下来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心怦怦跳的觉得,回到家里回忆这一刻是什么觉得。当我去想象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第一次上台和我在很漫长的青涩的岁月中,一些上台的时候。乃至于到现在,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有些寻衅的演出,我会觉得到生理有些紊乱,它也不一定是激动,但你彷佛有些东西难以平复,你也说不清楚。要赶紧抽一根烟或者喝一些酒,乃至于跟别人聊的时候也有点心不在焉,总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溘然产生在你体内了,我以为这是故意思的。
《出色WSJ.》:我好奇,人天然地就会说唱吗?还是他须要有一些方法?
小老虎:我见到的情形便是谁上来都能说上几句。首先,我以为是不是符合制式化的合辙押韵,是不主要的。我总以为他们供应了一种新的办法。没有一个标准,由于他们也在拓宽我的标准。好多拥有技能的人,包括现在可以有资质和成本去演出的人,乃至受到追捧的人,大部分人说的东西我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正好这些素人,每一个上来,我都挺期待他们会说些什么,乃至像抽奖、开盲盒,然后事实创造“开”出来的大部分,我都会以为故意思。
只管有个别的我也会打断他们,由于我以为借助一些限定,像是韶光和规则的限定,实在有助于他们真正专注在此刻要说什么上面。至于音乐的帮助,我也时时时地会把他们的音乐关上。我以为,既然我都不在乎你的这些押韵和节奏,为什么还要给你一个貌似有节奏的东西?我创造,有的时候音乐给某些人一个躲藏的空间,彷佛躲在里面就有了勇气,或者说给他另一种身份的想象。他认为自己在合辙押韵地说,而不是站在这跟你玩一个《艺术人生》那种真情流露。便是不一样的感情,可能他会给他一种新的勉励。如果躲在音乐里能够更好地开释,那也是好事,这不也便是音乐的魅力吗?以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我也没想清楚,我也以为很神奇。
《出色WSJ.》: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认为音乐是给你躲的。“躲”详细是什么意思?
小老虎:前段韶光发生了一件事。我五一回北京参加了一个叫“囍市”的小型音乐节,在隆福寺大厦的顶层。晚上我们在那做了一场即兴的演出。演出的人是之前《说统统》记录片里选出来的那些素人。我把他们聚在一起,不知道演什么,可能就跟不雅观众互动一下。这已经很危险了,由于他们不是专业演习的、有演出履历的人,演出的内容也都是未知的。
结果立时该上台了,创造音响效果很差,麦克风没声。不雅观众等了20分钟,已经开始焦躁不安了。在这种寂静当中,我站在后边,想起我很多次也碰着过这样的情形,我也常常疑惑自己的演出的意义到底在哪。由于我始终认为,我跟其他说唱一个差异是,我紧张的专注点不在身体性,比如带着大家在一块舞蹈。我便是想说东西,你一定要知道我在说什么,乃至比较之下,音乐都不一定那么主要。
那一刻,我看着这些更年轻、更没有履历的人,在前面被设备蹂躏。我深知他们的魅力便是他们说的东西。然后我再拿起麦克时还没声,就把麦给扔了。我说咱们肉嗓子试试。干嘛就躲在这些扩音当中?看看没有这些你行弗成,还有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便是你的代价。没有任何音乐,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以为有点不适应。你能看出他们的胆怯,一没有音乐的衬托,他们的声音也变得无力了。
看到这个状态,我就以为我们到底是不是躲在音乐里了?为什么没了音乐,你就一下觉得就泄了气了?它是一种习气,一种生理的反应,一种不雅观念的东西,还是当代工业化的音乐场景里的存在办法?
《出色WSJ.》:在做“说统统”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普通人的说唱那么主要。
小老虎:隆福寺演出当天,有个哥们一贯拿着相机,觉得是说唱爱好者,他要跟我拍照片。我说一下子再说,当时脑筋也是挺有压力的,不知道该怎么弄演出,怎么样跟不雅观众互动,怎么样调度这些人,怎么样刺激他们。
结果,终极他上来了,说了一小下没说完,然后底下鼓励他,他又再抢过来麦。还有人可能说你先别说了,末了他还是抢过来,这是断断续续的。大部分时候在冷场,但他溘然迟疑了半天说了一句。他说:“我就看着你们,我以为我离开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像你们一样站在这打开自己”,然后他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这一哭觉得为这句话增长了分量。这种东西我会以为确实挺有力量的,那是很自然的哭泣,而且他的觉得大概别人不一定理解,但是我以为我能明白它是一个什么意思。
《出色WSJ.》:对你来说,创作的灵感来自哪里?
小老虎:我以为如果从更宏不雅观的角度来说,灵感便是信息和连接。乃至有点像机器事情的办法,只不过现在电脑的信息处理速率和它能够产生这种奇特连接的能力还远远低于人脑,以是这便是人类进行一些创造活动的名贵之处。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性能非常神奇的东西。我也没有完备搞清楚这个事理,但我是按这个逻辑去看,想要灵感便是要只管即便多地获取信息,书本、电影是信息,走在路上听小鸟、看路标,和别人大量地交谈,都是信息。大量的信息之间溘然会产生某些连接,当有一些连接建立起来的时候,便是羚羊飞过大裂谷的瞬间。我迈过去了,所有的这统统联系起来了。
《出色WSJ.》:对付现在疲于 996 和内卷的年轻人来说,创作是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你来说,创作的实质是什么?
小老虎:我以为至少该当一试。这是对人来说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如果要说其余一件同等主要的事,可能便是爱了。或者说,创造力本身也是爱。
我乃至以为,每个人都该当把创作当成一件特殊核心的事。创作者也好,艺术家也好,他是不是一些工种,一个职业,乃至一种特权?如果它是一种能力,一定有高低之分,但也是谁都可以拥有的一种能力。你意识到你可能和创作有间隔,或者说它让你苦恼,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由于事情和生活的情形,以为这是生活以外的一件事情,乃至远得像外星球一样,这很让人遗憾。
以是“说统统”里面大部分人能够上台来试那么一下,我以为那便是少焉的创造。他的经历和此刻的所思形成措辞,和音乐产生某种关系,并且直接传到别人的耳朵和眼睛里,在别人的脑海里激起一些波澜。至少,这些创作都闯进我的生命里了。他们既不是音乐人,也不是作家,乃至不是好朋友,但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边,他们即兴地说出了一些东西。我记住了他们的文本、嗓音,他们的情绪和故事。我以为这便是创作。
通过创作,他们跟我产生了这么强烈的连接,我以为这是很棒的。
《出色WSJ.》:分享对付创作是不是主要的?
小老虎:我以为肯定要拿出去给别人看。不是说要放在小摊上出售的意思,但是绝对须要一种分享,要和别人发生一些关系。故事须要被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