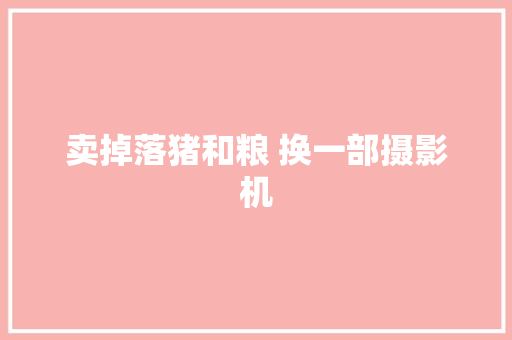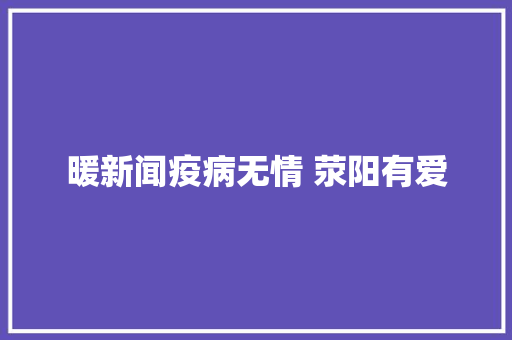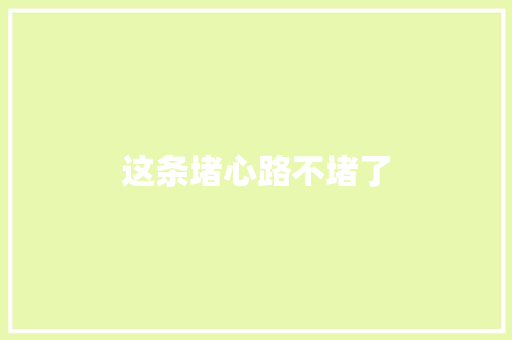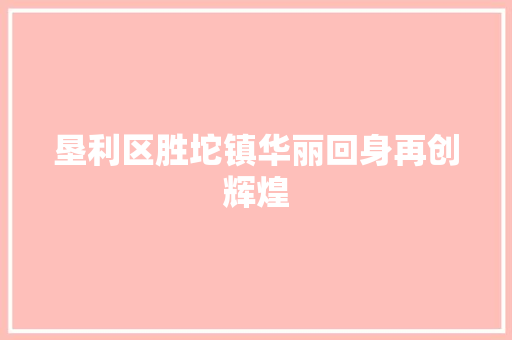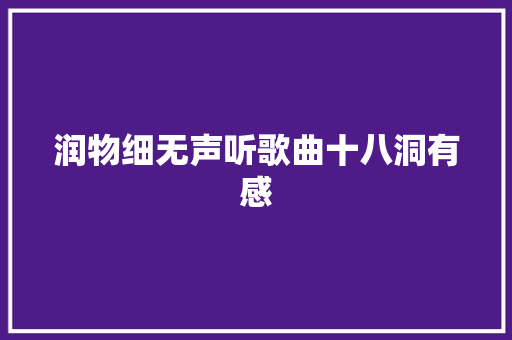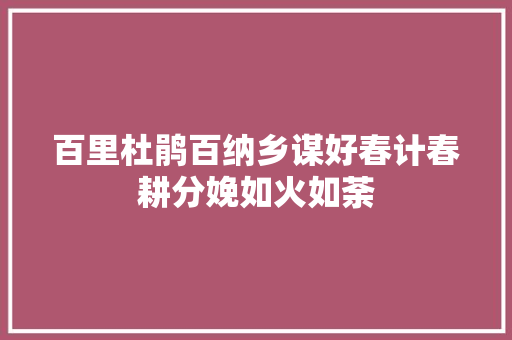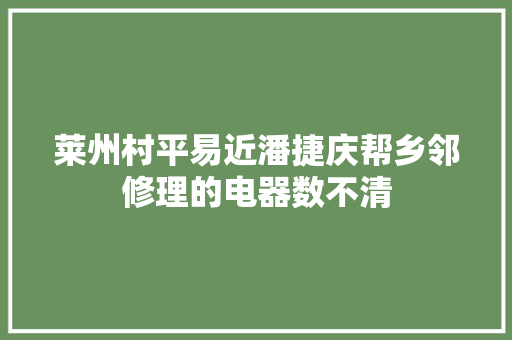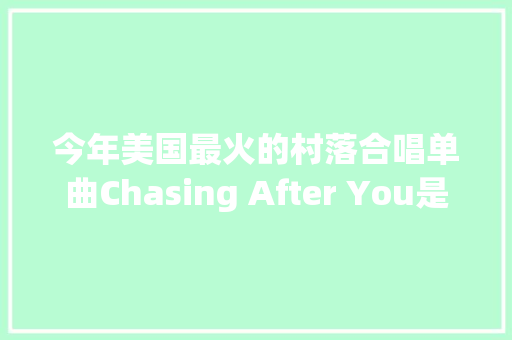文:陈清木 南天一剑编发
图片: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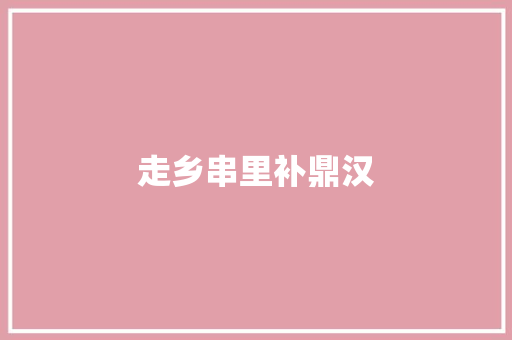
中等清瘦的个头,一身田舍式粗布衫,头戴笠帽,打着赤脚。肩挑有多层小抽屉的木制箱子,每个抽屉里分别装着各种工具,上架一个小巧风箱的补鼎担。一起风尘,一起艰辛,走村落庄入角落,专事补鼎、换锅底、修雨伞、弯门钩、磨锁匙……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三十多年间,蓬莱、金谷一带沿途乡民深深的影象。这个中年男子叫“补鼎汉”,人称“汉师”。
“汉师”,安溪县蓬莱镇同盟村落人,农人,多子女(他最小的儿子是我上届高中同学),算来该当是一百岁旁边了。“汉师”农忙上山下地劳作,清瘦的体魄康健而机动,棕赫色的皮肤乌黑而发亮。农闲凭一手祖传手艺到处补鼎,这个行当使他肤色更加显得黑里透红。朴实诙谐的谈笑是他的江湖人的特质。乡民老少都亲切的称他叫 “汉师”。
小时候不守规矩的我,常跟在“汉师”背后,拿起他的由五片钢片做成的广播器,嚓、嚓、嚓……声传遍山村落,学着吆喝:“补鼎锅、补生锅、磨锁匙了!
”通知布告亲堂赶紧来补鼎。
以前的锅全是由生铁铸造,生铁不耐用,加上柴火熊熊,铁锅很随意马虎开裂、穿孔漏水,于是,“汉师”走街串巷修理各家各户的漏锅、破鼎,很受人们的欢迎。风雅的工匠大师手艺深得主妇们的相信。他是那个年代炊具维修的“工程师”。
走入各角落,或树下或厝角是他的工场最佳选择。架起风火炉,套上风柜,放生铁,顿时炭火吞红吐绿,吱吱有声。帮拉风箱是孩童们的最爱。碰着有人来补锅,只见“汉师”把鼎竖举对着光芒一瞧,娴熟举着小尖锤敲打几下,小老婆点变成大孔洞。倒出红彤彤的铁水,然后浇在锅内的穿孔处,在穿孔的下面,平铺一块湿布,冷却浇下来的铁水,将裂孔补充铲平。补好后,再把锅烧红,抹上桐油灰,使其平整。
如果裂纹比较小,则用铁粉修补。首先把鼎架在火炉上,加入铁粉烧熔化,顺着流动的铁水用工具割几下,就完成了。
“汉师”补鼎,价格合理。不分大孔小孔;不论有生(主人有供应生铁)没生;好坏成份,一律两毛。心里有底,客户放心。记得有一次,宗叔拿来一只破大鼎,求“汉师”修补,经锤子一敲,实在孔似天窗,引得众人笑声鼎沸。你看这个都破成啥样了?
住足看“汉师”换锅底,修雨伞、弯门钩、磨锁匙,手艺博识,行云流水,令人折服。
汉师”人缘好,常常是自带粮食,饭点向村落民借鼎煑粥,也为主人免费补鼎以当柴火费。有时也会在好友的激情亲切呼唤下就一餐,因路途迢遥,一次到东溪总要住宿一星期旁边,才能基本做完成。曾记得要回家的前一天,工场都设在晒谷坪街道的榕树下,利于各角落的众人漏补。标牌昭示“末了一天”。越日再想补鼎,村落民只好等下回了。那有象当代的商店匆匆销,“末了三天”连挂一个月,再来个“末了一天”!
连播三十天。
“汉师”为人谦和,在东溪内有很多茶友加朋友,有德叔、等叔、光明叔……空余一支烟,工间一杯茶,讲古话仙,讲天捉天子,话天文说地理,讲先贤论光滑油滑,议民风说算命,甚是有趣。记得有一次,几个顽童戏耍邻居一小弟弟,把人弄哭了。汉师连忙放下手中活,把小孩带到跟前,拿出一块糖果以示褒奖。尔后,有传说“汉师”会算命,知道此小孩有贵气,日后定出头,对这个小孩疼爱有加。
1974年我曾到过蓬莱他的家中,出于好奇问起这件事,他笑着对我说:那小孩是地主的孙,大孩都会陵暴他,将来便是会出头。令我久久思虑着这个问题,至今对“汉师”印象特殊深刻。
他曾负责地为我看过相,笑着说:“聪明在线人,贵在精气神。”细细思想,我今生几度历险皆无恙,至今眼不瞎、耳不聋。全赖“汉师”当年的神机妙算,令我笃信不疑。
随着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门谋生。与“汉师”的谋面机会越来越少。末了一次是1983年的农闲,见他依然矫健走四方,嚓、嚓、嚓……声依然入耳,“补鼎锅、补生锅、磨锁匙了!
”依然亲切。
现如今经济条件优胜,产品五花八门,过度丰富而物贱,坏了就扔,扔了就买。很少有人把用坏的锅碗瓢勺俢补再利用。想当年“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用三年。”的俭持之风已荡然无存。
补鼎这一老行当,也像“九佬十八匠”中的大多数行当一样,渐行渐远,已在我们的视线里难觅踪迹。
老人念旧,往事重提。啰嗦几句,请君莫笑!
2020.7.1日陈清木写于福建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