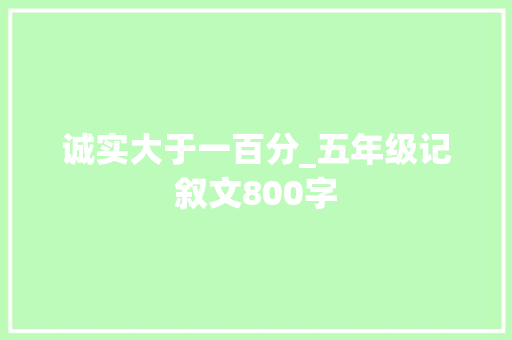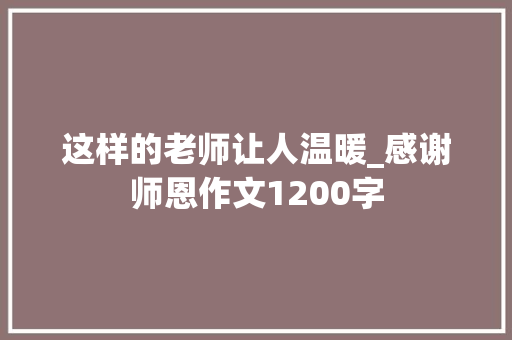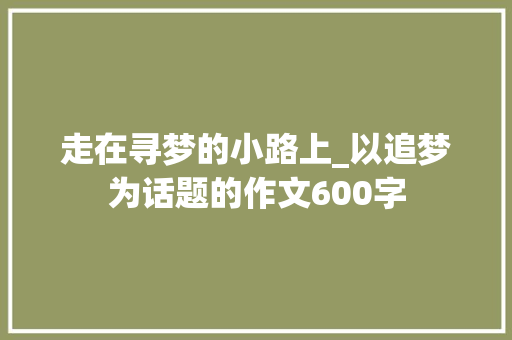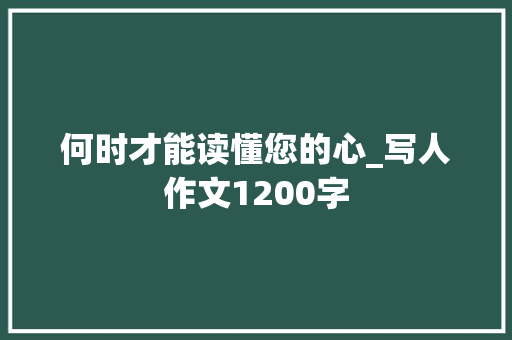在中学校庆百年庆典演唱《山楂树》
3月24日,中学母校四川省大竹中学百年校庆广东地区庆典上,我演唱俄语歌曲《山楂树》。“Вечер тихой песнею над рекой плывет,Дальними зарницами светится завод(歌声轻轻荡漾在薄暮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着光)”一时哽咽,与俄语30多年的缘份顿时浮现。后来一位参加庆典的老学长说,她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是学俄语,听了这首歌,勾起美好回顾,当晚回去激动得睡不着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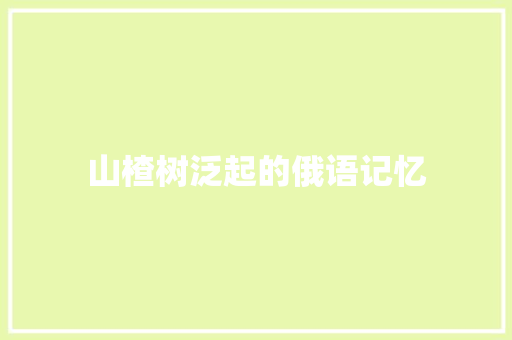
1985年,我在大竹中学上初中。年级共四个班,三个班学英语,一个班学俄语。我分到了俄语班。上课第一天,教俄语的张宝文老师讲了一通道理,“中苏关系正在解冻,学俄语大有出息”,意在打消我们和家长的顾虑。那时完备服从分配,没有一个同学闹换班的,就这样一贯学了六年。张老师又说“苏联是一个俏丽的国家,我没去过,大概没机会了,希望你们能去看看。”莫斯科、圣彼得堡、红场、克林姆林宫、冬宫,往后从教材知道了乌拉尔山、伏尔加河、西伯利亚……前年一名同事从俄罗斯旅游回来,愉快地讲起俄式风情,一众人等听得怔怔的。我不禁说:“这些地方我没去过,但30年前就知道呢。”
为什么我们中学有俄语班?这是历史遗留成分所致。中苏友好时,全国中学以学俄语为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学英语成了主流,本校还有两名俄语老师坚守岗位。张老师教完我们便转岗搞行政,此后再无俄语班。俄语生在校史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它同学看我们,彷佛认为我们有“特异功能”。实在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非主流的失落落感,看到课外读物都是英语表明,心里难免打鼓。好处是转不了班,同学从月朔到高二分班,有些人六年乃至补习班,都在一起。同学感情特殊深厚。
2016年春节,中学同学返乡看望俄语老师张宝文
作为“独苗班”,外语的传授教化效果没有比拟和竞争,老师要敷衍的话,是很随意马虎的。但张老师视我们为他的作品,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传授教化极为负责严格,对词汇、语法、书写的每一个细节都抠得很细。俄语属东斯拉夫语系,没有音标,入门随意马虎,但语法繁芜,变格变位形动词副动词折磨人。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学得很吃力。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常常在早读课时,他叫停朗读,讲解近期的疑点。早上影象力强,我们受益匪浅。
课文的内容,多是先容苏联的人文地理、培植造诣、英雄人物,以及俄罗斯童话、寓言,也有人类文明史上的代表人物。有篇课文先容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文笔幽美,文末“很难说,列宁格勒到底是夏天俊秀还是冬天俊秀”,意味深长。一篇课文体裁是话剧,讲述女革命者丹妮娅智斗警察的故事,生动活泼。一篇课文设想机器人的天下,很启迪我们的思维,现在看来已经成为现实。当时已是八十年代,课文题材走出了意识形态的窠臼,先容了不少天下各国的人物,如数学天才高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奏响《月光奏鸣曲》的贝多芬。
作为一门课程,俄语自然也在高考指挥棒的笼罩之下。可能是为了发掘小语种人才,高考的难度相对低一些。张老师说:“你们不考90分就算白学了。”(满分为100分)很惭愧,本班高考考过90分的百里挑一。我没给老师丢脸,考了96分,但没有考上俄语专业。北大是提前批次录取,为了进北大,我以为报俄语可能竞争小点,还是未能如愿。
不过我能考上中国公民大学,也是托了俄语的福。我的成绩和一逻辑学英语的同学不相上下,报志愿都是第一志愿公民大学,第二志愿四川大学。我只比他高四分,结果他去了川大。如果不是俄语这96分,我的总分肯定是低于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俄语改变了我的人生。
读过的高三俄语课文《月光曲》
实在张老师最得意的弟子不是我,而是一名措辞天赋极高的女生。她六年一贯保持着俄语成绩第一的上风,高考考了98分,入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另一名同学复读考上西南师范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到胜利油田从事俄文翻译,没多久就当了“北漂”,扔下了专业。全班40多名同学,终极没有一人以俄语为职业。想来挺遗憾,多年无颜见张老师,
上了大学,学校把学俄语的学生编成一个班,有50多人,北方省份居多,南方省份的,居然贵州也有。此时创造,张老师打下的根本确实好,我学大学课程很轻松,过完四级就不再管了。
及至到广州事情,南方沿海完备是英语的天下。我在大学自学过英语,大略的还能搪塞。翻译软件问世,技能填补了个人的知识短板。但我和俄语还没有告别,考职称外语,轻松过关。读在职研究生,考了两年才过。第一年从网上买了几本资料啃,创造走了弯路。第二年找来当年中学教材,把张老师教的内容温习到位,如神医药到病除了!
读在职研究生时,背诵《山楂树》歌词
从应试角度,我大概没有再学习俄语的刚需了。但我和俄语的缘份,必将伴随生平。我珍藏着中学和大学时期的教材,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暗号,有恶搞插画的涂鸦,印记住的,是金子般的少年和青春光阴。俄语为我开启了一个独特的天下,是我人生前行的独特动力。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带着这些教材,容身在深邃的贝加尔湖、溜达在无垠的西伯利亚白桦林、流连在悄悄的顿河、徜徉在莫斯科郊野的晚上,唱起《山楂树》、《红莓花儿开》、《三套车》……
本文写于2018年3月28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