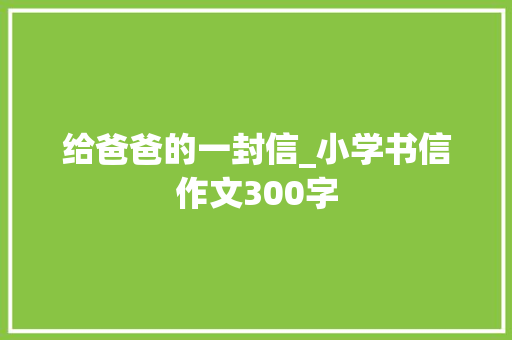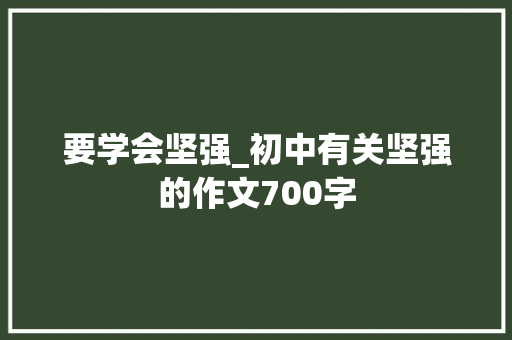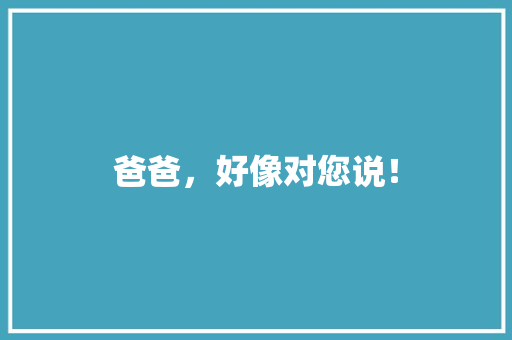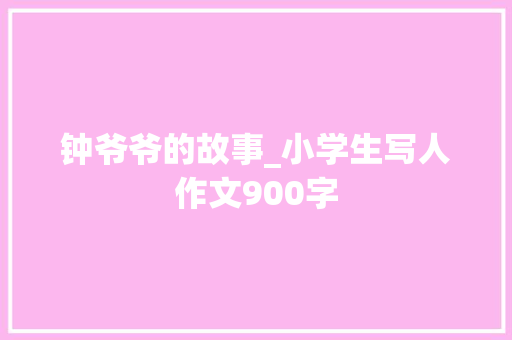街道上依旧马车穿梭,汽车在这里显得扞格难入。小镇的原始风貌让当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都显得无用武之地。
我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目光落在她身上。

只管她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我并没有像躲避某些自认为不只彩的事情那样,急忙避开她和她试图与我互换的眼神。我并不打算像上次那样哀求她,由于天色已晚,她须要回家为孩子们准备晚餐并知足家人的需求。
抱着瓜果的女人向我走来,她勉强地笑着对我说:汉尼玛,你是不是要娶扎达瓦家的女儿?我的女儿已经终年夜了,你也娶了吧。她的话音刚落,便低头紧张地盯着自己怀里的青瓜。我从未见过她的女儿,乃至疑惑她是否真的有女儿。我问她为何要这样做?她阐明说:“实在我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汉尼玛,你看这样,你娶扎达瓦家的女儿,我的女儿给你做二妻,或者做仆人也行。只要你能让她吃饱肚子,这孩子太大了,家里养不起,让她跟你一辈子。你只要让她吃饱,可以吗?要不我现在就带她去你的阁楼。
听着她的话,我感到一阵迷茫,想象着那个女孩可能和她母亲一样端庄,但我还是以为那个女孩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沉重,于是婉转地谢绝了她。我不想再连续谢绝她,只管她的话听起来让人不悦,但她为了坚持家庭,为了成为一位能让孩子吃饱的母亲,为了赚取那份双倍的青菜钱,已经付出了很多,我不应该对她有任何责备。
我见告她,如果雨不大,就让她女儿来吧。女人的眼中急速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她高兴地说:今晚无论雨多大,都会让女儿去我的阁楼。说完,她就像上次离开我的阁楼时那样,脸上带着喜悦转身拜别。
回到那阴暗的阁楼,我点燃油灯,将被酒精麻痹的身体毫不顾忌地扔向那厚重的床铺。闭上眼睛,油灯的光芒透过眼皮映照在我的脑海里。我思虑着那个卖瓜果的女人,想象着她的女儿终年夜后是否会和她一样,只管我闭着眼睛,但我还是喜好大脑里有光的觉得。在含糊的意识中,我觉得自己已经睡着了,不知道表面何时风雨大作,隆隆的雷声和电光闪耀,让我的大脑陷入昏睡,逐渐滑向更深的怠倦。
溘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苗条的黑影,随即被阴郁吞噬。我警觉地翻滚到床下,侧卧着抽失事先绑在床腿上的瑞士钢刀,当心地不雅观察着阁楼外的情形。我这才意识到,很可能是那个卖瓜果女人的女儿。我心里发急,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房门。
一个瘦弱的女孩,在狂风雨中紧抱着双臂,她的头发和衣服像薄纱一样贴在脸上和身上,我想这该当便是那个女人的女儿。我的阁楼原来有屋檐,宁静垂直落下的雨不会打湿避雨者,但今晚这恶劣的景象,却让这个小家伙饱受风雨的洗礼。
我向她挥手,示意她快进屋来。她犹豫了一下子,彷佛想动又不敢动。我很焦急,知道她可能害怕,再次用力挥手让她进来。风雨和闪电仿佛在责备她不听我的话,变得更加狂烈。她对风雨的恐怖终于降服了对我的恐怖,开始犹豫着,逐步向我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