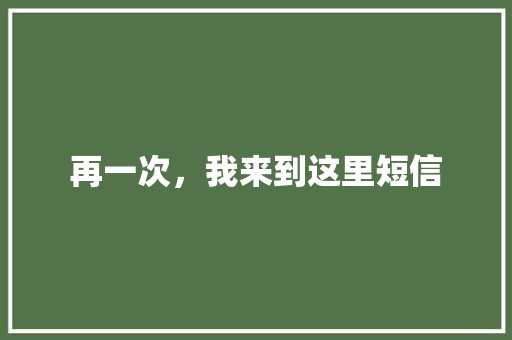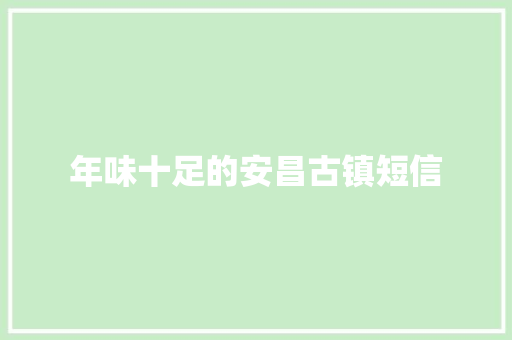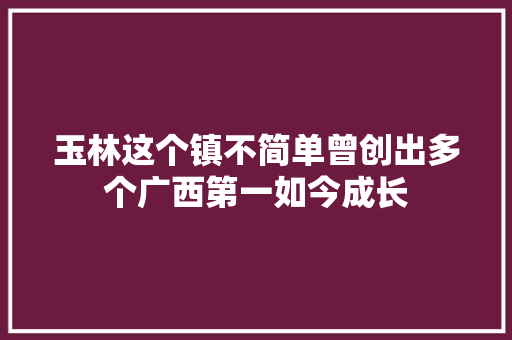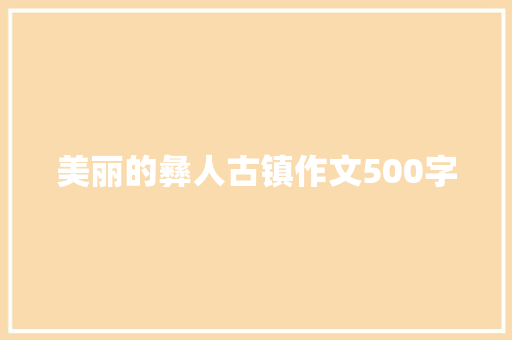古镇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历史积淀,长治有四大古镇:
1、荫城镇,荫城镇从属于长治市上党区,是上党区东南部经济、文化互换中央和主要的商品集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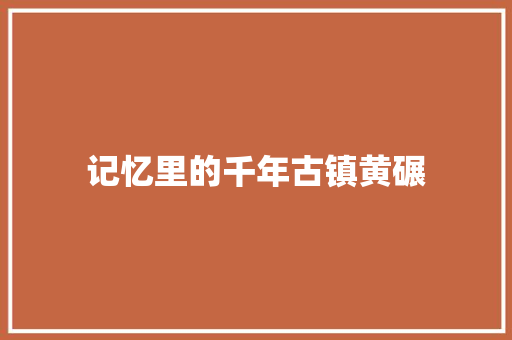
2、鲍店镇,这个古镇已经有了大约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古代是晋豫和秦晋之间的交通要道。
3、黄碾镇,从古代便是长治北交通要道,东西是屯留至潞城,南北襄垣至长治交通要道。
4、韩店镇,韩店镇作为全县的文化中央,具有相比拟较完善的文化举动步伐、教诲举动步伐、休闲娱乐场所,成为县城居民紧张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
黄碾,一个人们曾经渴望五谷丰产、放飞梦想的千年古镇。位于长治市潞州区北部,不含周边辖区村落落,仅主镇区人口就有一万之众。它东依潞城,西接屯留,曾经是长治市的主要卫星城镇。千年流淌的浊漳河与上党盆地的沃田沃土授予了黄碾太多的文化传承,从而使这座地形酷似柳叶的北方古镇早在宋元期间就名噪一方,成了我们探寻上党历史文化的一个主要缩影。
黄碾古镇是中国北方古镇的一个缩影
在晋东南这片地皮上,有几人能不知道响当当的黄碾古镇?在许多当地人的眼里,黄碾古镇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座具备中国古典风格、有着浓郁北方特色的商业重镇。其紧张依据是其坐落于浊漳河边,为晋豫冀陕十字交叉的枢纽所在。于是就形成了开放原谅的姿态,独特的古镇文化,曾经声名远扬,一年里的三个大庙会构成了黄碾古镇商贾云集,繁荣昌盛的辉煌历史。同时,也符合古人“择水而居,依河而生”的生存哲学。从古镇现存的碑碣考证,这座古镇的历史至少可以推算到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该镇“南佛寺”中所供奉的大型石佛就属那个年代的神像。
而从当地人代代相传、津津乐道的一段“野史”中,我们不难创造这座古镇的另一条线索,那便是大宋开国天子赵匡胤正是在这座古镇的 “撒金桥”头与护国智囊苗广义缔盟成义、共打江山的。
据【潞安府志】、【潞城县志】记载,苗光义,名训,字光义,潞城宋村落人。其少年时很有抱负,西上西岳,拜当时著名羽士陈抟为师。由于他聪颖好学,才智过人,深得恩师喜好,对他格外爱慕教诲。数年的刻苦努力,苗光义已学的文韬武略,满腹经纶。 他还乡后,在柳叶镇(今黄碾镇)耍金桥搭一简棚,算卦相面,坐诊看病。不分远近贫富,等量齐观,岐黄济世,药到病愈,休咎祸福,推断如神。一韶光人来人往,棚门如市,随后发生的一件奇案,更使苗光义声名远播。
一日,在江湖上闯荡的赵匡胤路经柳叶镇,见卦棚古人头挤攘,便翻身下马,将马栓在桥旁柳树上,分开众人走进卦棚探视究竟。苗见赵匡胤紫面丰颐,气宇轩昂,有帝王之相,忙起身相迎。待一交谈,更觉其肚量胸襟博大,志存高远。二人交谈很是投契,相见恨晚,都有推翻残暴统治,重修伟业救民于水火的青云之志。于是,苗光义收摊,领赵回村落,设酒席招待。苗剖析了天下大势,见告他:目前,汉水以南场合排场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应在北方广结天下英雄豪杰,扩展势力,审时度势,待机遇成熟掲杆发难,并见告他现在河北邺都任后汉最高军事主座郭威是位英雄人物,可前去投靠,见机行事。赵匡胤听后,拱手谢曰:“苗师长西席高瞻远嘱,乃当今奇才,实在是诸葛孔明再世,我心悦诚服”。临别时双方依依不舍,苗见匡胤衣衫破旧,便赠予了金钱作盘缠路费,匡胤感激不尽,热泪盈眶。他和苗光义约定,待机成熟,定与师长西席共谋大业。
这里且不论这个故事本身的真伪性,单说古镇的这座上世纪90年代前还保存无缺的古桥路面上那千年形成的深深的车辙,就足可以见证这座古镇的沧桑岁月了。
黄碾古镇,历史悠久,古老繁荣。说其古老,不外乎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证,即:石桥、寺院、民居、宗教、街貌、集市等。
影象中的黄碾古镇,是一条南北狭长的古老街市,其主干大街长约1.5公里,北段、中段分别有两条直通浊漳河的雨季排洪沟,每当行雨时节,那滚滚山洪就会通过这两条排洪沟注入漳河。因此,黄碾古镇的主干大街上就有了两座连接南北、气势如虹的石拱古桥,且桥面宽广,形制宏阔,使街道彰显出玲珑剔透的艺术之美。街道两侧是依次排开、门当户对的数十家老式店铺:铁货、粮行、布匹、鞋帽、油坊、酒馆、理发、农具、医药、日杂……可谓搜罗万象,一应俱全。这便是黄碾古镇街、桥相伴的特色与风貌。
黄碾镇上的古庙为数不算太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镇北、镇南、镇东各有特色的三座寺庙。
镇北桥头的“三官庙”属玄门活动场所。所谓“三官”,分别为“天、地、水”各一官,奉于正殿,旁边偏殿则供奉着太上老君和药王扁鹊。
其与古老的“撒金桥”呈90°直角,在桥头的开阔地段陡然立起。并且,因阵势形成一座四米见高的高台。人们登庙拜会,须拾级而上,可谓气势雄伟,居高望远,曾经是这座古镇的图腾和骄傲。
镇南古街的尽头则是一座佛教活动场所——“南佛寺”,“南佛寺”以供奉一尊北魏古老石佛而久负盛名。据史籍和碑文记载,该寺庙曾“僧侣数人、喷鼻香火兴旺”。寺正南广场为古式戏楼,寺东南街口为入镇古阁,曾被视为黄碾古镇的南大门。
在镇东的丘陵高地上建有一座尼姑庵——“白衣庵”,曾有尼姑数人。为古代镇上人们祛病拜药、祈福求子的宗教活动场所。
南寺、东庵、北庙、西河遥相呼应,水岸相依,两座古桥穿街而过,且建筑布局风雅玲珑、形制讲求,构建起了古镇人与自然和谐完美的、不俗的文化品位与内涵。黄碾古镇,人杰地灵。古镇上也曾呈现过名噪塞外的一代晋商。清末民初,镇南的城墙沟巷就曾拥有过一支颇具规模的 “驮邦”,并且是由清一色的骆驼为承载工具。驼铃声声,列队行进。每当那十几匹骆驼打着鼻响,晃荡着叮当的驼铃声,踏着沉重而坚实的步履,出入于这古镇大街时,总会引得人们惊异的目光。因此,这驮邦的主人就在他们那个原来并不起眼的沟凹里筑起了两院连环、偏正构造的高大宅院,看上去酷似远古高大古老的城墙,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成了“城墙沟”。堪称从古至今的古镇首富。
黄碾古镇,开放原谅。约一百多年前,这座小镇溘然来了一拨“洋人”,他们是西方的传教士,有神甫,也有修女。为穷汉布施,为病人看病。并在镇子北头的沟岸高地上建起了一座准欧式的泰西建筑——圣家教堂。天主教的传入,使小镇忽然间有了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气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小镇的石板街上因有了“洋人”的出没,也成了一道当时国人罕见的风景。
集南北于大成,取中西之短长。在人们的影象中,黄碾古镇也曾有不少属于自己品牌的精美小吃让人大饱口福。如:那堪称一绝的“黄碾荞面溜圪垯”;那层层脆、层层酥的“黄碾驴油小火烧”;那少女街头提篮小卖的 “黄碾干饼卷子”……这些都是属于黄碾独占,别处没有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公民公社在黄碾古镇成立,名曰“长治市东风公民公社”,可谓东风浩荡,满眼葱茏。新成立的“公民公社”举全社之力,集辖区内几十个村落庄的财力、人力、物力,在黄碾主街中心东侧,修起了一座可容纳千人的“公民大礼堂”。随即,中学、邮电、医院、银行、工商、税务、公安、阛阓、粮站、摄影馆、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等一大批城镇配套机构在黄碾设立。加之长治市的六七家大中型省营、市营及集体企业在黄碾的落户生根,一时使古镇声名鹊起,掀起了其新一轮的崛起与繁荣热潮。
黄碾,无愧于古老上党的商业重镇。在其南五里,有一个叫“故驿”的村落庄,推测为黄碾古镇旧时的一座古驿站,当属南路客商进入黄碾的桥头堡;在其北五里和北十里处,既有一个叫“王里堡”的村落庄,又有一个叫“店上”的村落庄。由此破译,古代的王里堡实为“五里堡”,古代的“店上”村落实为“十里店”。由于,大凡古时重镇古官道旁均有“五里堡”、“十里店”之说,为北路客商进出黄碾的主要立足点。
一年三次的物资互换大会 (农历仲春初三、五月月朔、七月十六),险些涵盖了小镇商贸集散地的全部主题。每逢此时,必是人头攒动,人隐士海。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内蒙、陕西的商家不惜远道而来,为的是能在这声势浩大、气度非凡的千年古镇上创出品牌,选取头筹。
这便是我们影象中那个流光溢彩、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那个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大码头——黄碾古镇。
二、古镇文化——因浮华而沉沦,因忽略而自殇
时期在变。经由几十年的改造与发展,如今的黄碾古镇已经完备改变了原有格局,变得让人不敢相认了。该当说,无序的发展和短缺对古镇保护意识的盲目方案,是对这座古镇的致命侵害。再便是战乱和人为的侵害,使这座古镇的文化标志不觉中就变成了本日这个样子。
先说古桥,如今已经踪影难寻。上世纪90年代,主街中央和主街北侧的两座石桥,特殊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撒金桥”,其两侧已经被砌成涵洞,彻底填埋后变成了东西走向的狭窄街道——被无情埋没在了现代人们的浮华之中。
再说古庙,古庙曾经是小镇上的传统文化之魂。那耸立桥头的“三官庙”,曾经是古代官绅由官道进镇时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的首拜之地。如今却没有按照原貌进行修复,而是将石头台阶包入新建的单面平民式二层大略单纯小楼之中,将寺院的南配房改造成了老年人活动中央和书屋,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失落去了原有的飞檐斗拱和原有的图腾代价,也就失落去了小镇独占的古老文化。
南佛寺及其古戏楼、过街古阁的建筑群,毁于抗战初期,也便是1938年日寇派八架飞机对黄碾的那场轰炸,现仅存主殿。解放后寺庙前殿被修成市房用作屯子供销互助社的蔬菜营销场所。上世纪90年代被当地信众重修,并将早已身首异处的石佛找回重新组装成像。遗憾的是,由于文物保护知识缺少,一尊文物代价极高的古代石雕佛像被油漆描述涂装,将其变成了一尊金身彩塑,大大失落去了原有代价。寺院本身也没有得到完备改造,前配房依然为商业用房,且安装了当代的卷闸门,让古人蒙羞。
镇上唯一的异国风情建筑——圣家教堂,在“文革”中被拆除了主塔塔尖,“文革”后,被信众按原貌修复。
“公民大礼堂”,这座曾经的古镇新地标,在2000年后,被所在地村落委拆除,变成了一座庭院式构造的农贸市场……
城墙沟卫家晋商大院,其前院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曾被改造为黄碾地区医院门诊楼,上世纪90年代后被摈弃,现三进院的中院已被拆除,后院保留。
长途汽车站,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人去楼空,后便被拆除建成了饭店。火车站、邮电局、摄影馆、银行等已经没了踪影。
就连那些黄碾古镇独占的名优小吃也正在失落传或已经失落传。
那些木板槽插式的古老市情已经绝迹……
乃至,就连享誉周遭百里的中药铺,百年迈字号——“大生魁”,也已在上世纪80年代后匆匆退出历史舞台。
眼下,我们所能感想熏染到的只有古镇文化逐渐远去的沉沦的背影。抑或在昭示着一个时期的结束,一个时期的开始。
随着时期的变迁,经由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长足发展,黄碾古镇亦同广大中国屯子的集镇一样,有了质的飞跃和变革。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原有的农耕文化的黯然落幕,这座古镇却涌现了当今的尴尬和低落,其区域中央地位的逐渐失落去却是不争的事实。南有长北中央区域的异军突起;西有长治钢铁公司和王庄煤矿弘大人流的集群发展;东有潞城城市的突飞年夜进;北有店上煤焦工业的村落镇嬗变……加之交通的发达,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古镇那种原有的“日中而市,日落而息”的古老商业模式,早已被时期所冲破。它曾经的繁荣早已被周边的经济强势所粉饰,寸土寸金的时期业已不再。
初冬时节,登高俯瞰,曾经的千年古镇如今纵有高楼崛起,一派新貌,但却也难免一声长叹。
它的文化传承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