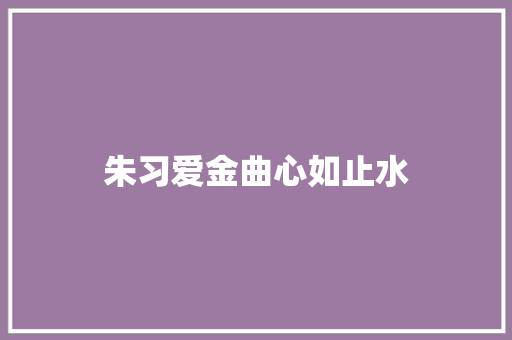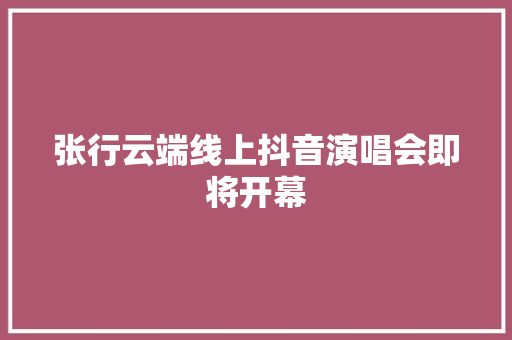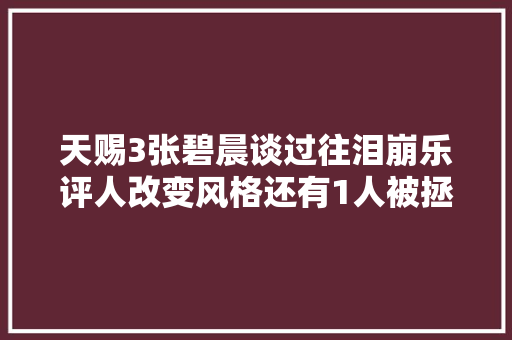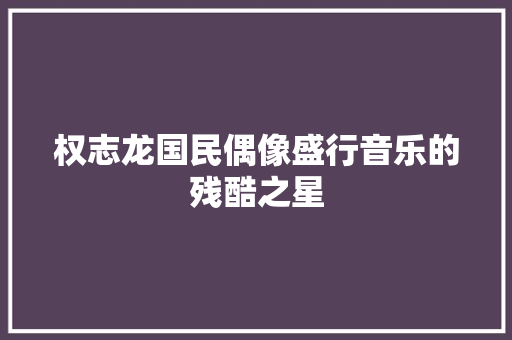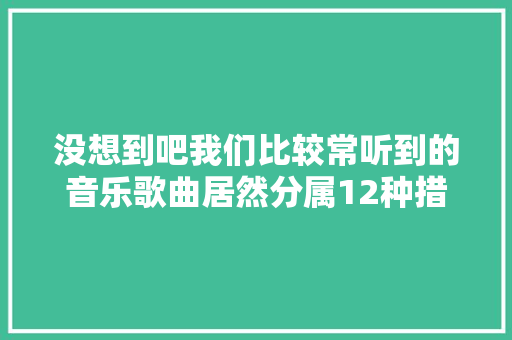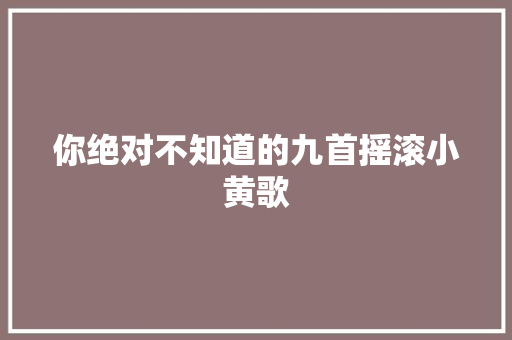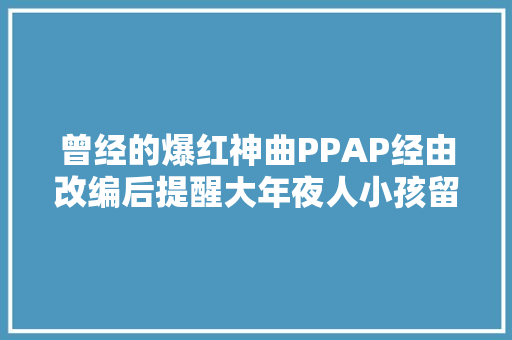先推举一首《风起天阑》 :
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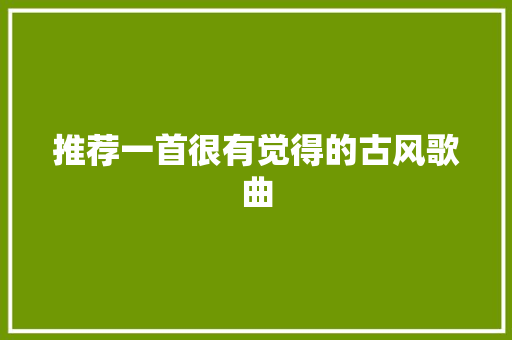
崇宁七年七月,白炎军攻城,是为乱始。守将谢婉率众苦战,不得援。七月廿六,城破,婉力竭被擒,不肯降,为炎军枭首。八年春,炎夺王城天岁,鸩敬帝,清朝堂,废宫室。仲春登基,定国号周,改元永初。
永初十年冬,周帝崩,朝野翻覆,诸王皆谋自主。时有乱军夜袭,见婉散发执枪于城上,肝胆俱裂,乃退。十一年,新帝彻平乱登基,改元太业。
太业后,城中始有谣歌传唱。歌曰:安危何所系,天阑谢将军。太业三年,城东设谢婉衣冠祠,祭拜者众,喷鼻香火终年不绝。
——《天阑城志·谢婉传》
看完歌曲的文案,再看看歌词,然后听歌,歌曲前奏直接把人带入那段悲惨的往事当中,谢婉在城墙上,默默的守护着城中万千百姓,而城下守夜的人,也只能默默是注目着城墙上,那遥不可及的人,浊世之中,性命尚且无法顾及,何来情爱之说?
再来一首《倾尽天下》 :
文案:
周帝白炎去世在称帝十载后的一个雪夜。
这个草莽出身的天子不喜奢华,逼宫夺位后便废弃了前朝敬帝所建的富丽宫室,而每夜宿在帝宫内的九龙塔,去世时亦盘膝在塔顶石室几案前的蒲团上,正对着壁上一幅画像。
倘有历过前朝的宫女在,定会认出,那画上艳色无双的女子,正是前朝敬帝所封的末了一位贵妃。
原来在倾国的十年之后,白炎究竟追随那人而去。他身后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于是所有关于周朝开国天子的谜团,都与那悬于九重宝塔之上、隐在七重纱幕背后的画像,一并被掩埋进厚重的史籍里。
这首歌是河图最经典的歌曲之一,歌词如同一首诗,虽没有过于华美的辞藻,但是字里行间的起承转合悠远绵长,声线低沉悲哀,气息哀伤凄凉,意境寂寥深远,深情而又清澈的唱腔搭配着悲壮的歌词,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苦处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
第三首《不见长安》
长歌一曲如画卷,梦里花落知多少?金乌虽遥昂首见,不见梦中长安城。
鲜衣怒马少年时,一日看尽长安花。歌尽悲欢诗三百,熙熙攘攘长安街。
这首歌写的是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城,当昼夜兼程,跋山涉水到达这里后,却创造这重重楼阁浩浩殿堂,都不是梦里所想象的一样。心里彷徨,梦里徜徉,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长安,只是梦想和现实究竟是有差别的。
“长安与日孰远?”
“长安远。”
“何故?”
“昂首见日,不见长安。”
第四首《伶仃谣》 :
这是一首以“赶尸”为题的歌曲,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那是一个视生命如草菅的年代。战士捐躯疆场,不能魂归故里,于是有了赶尸人将他们的尸体如赶羊一样平常引回家乡。而远在他乡的亲人,那白发苍苍,告别时便惦记着早日归来的人,对镜梳弄的,更似丝丝缕缕的顾虑。然而未曾想到,如今却换来去世亡的音信。那歌声悠远绵长,仿佛此时此地穿越千山万水,传给山那头的人,声泪俱下。但是,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只能在纷乱的人间嘲笑这浮华,将他深深埋葬。内心的苍凉,如白色,白得彻底,如深冬之洁白得寒冷至极,透彻心扉。
即便如此,河图依然把这首歌唱得如梦如幻,给人一种安详、宁静的觉得,柔柔的腔调寄托着对亡者无限的顾虑和物是人非的惆怅。
第五首《第三十八年夏至》 :
这首歌是本人最喜好的古风歌曲。
“我记得第三十八年夏至,你说过会带我去台北。”
一位戏子喜好上了国民党军官,军官说战后会带他去台北,其副官也喜好军官,军官怕被误会想向戏子阐明清楚,不料遭人暗杀,副官也独自亡命,无所依托的戏子就沉浸在戏剧的天下中孤度余生。“三十八年夏至”的含义隐蔽得很深,从1912年民国建国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北,恰好是三十八年,故意思的是,这首歌不只文案和三十八有关,歌曲里副歌结束后的第三十八秒恰好换成河图的声音,而且歌词也恰好是三十八句。
歌曲开始即传出沙哑的京剧声,颇有岁月的气息,相继伴有河图独特的古风演唱,个中与京腔混搭相和,韵味十足。
以上只是河图的五首歌曲,河图其他的古风歌曲也非常好听,喜好的可以去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