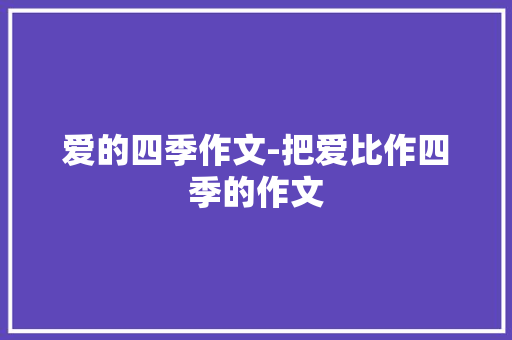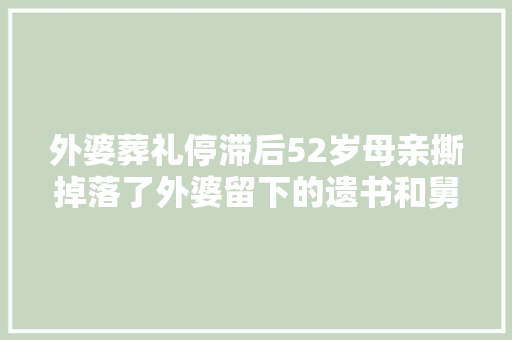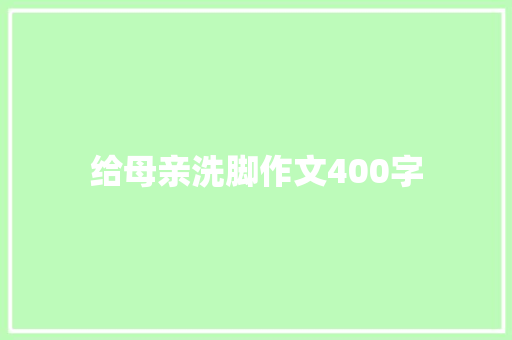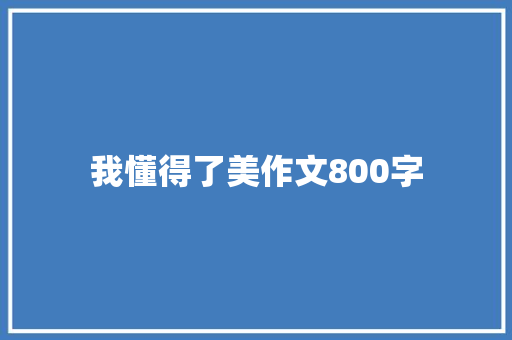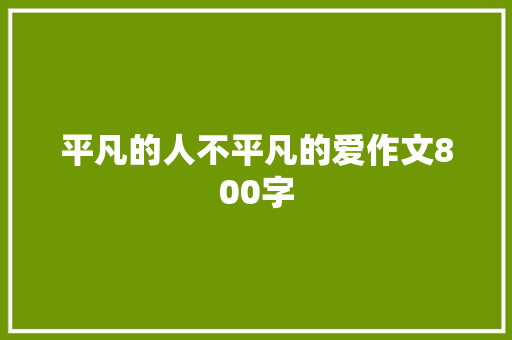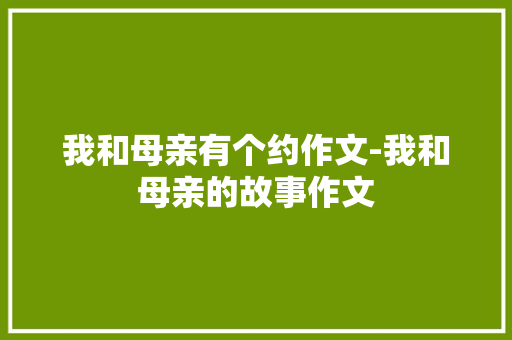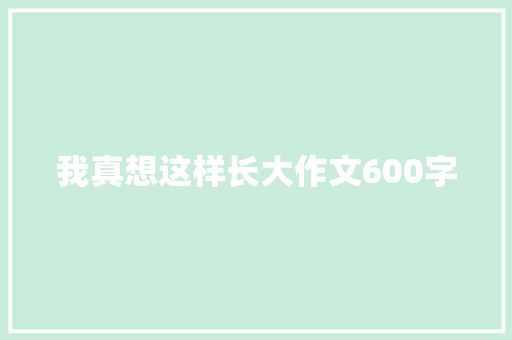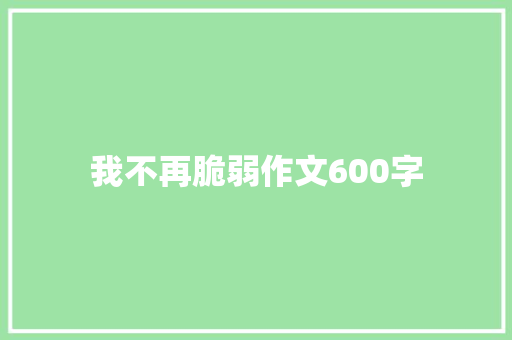文/刘哲
我是汨罗人。弼时镇尖塘村落那个叫坳上屋的小屋场,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母亲是裁缝,父亲是木匠。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出身身分问题,父亲挑着一担箩筐,一头装着我们兄妹俩,另一头放着缝纫机,做木匠须要的锯子、刨子、曲尺、斧头。父亲徒步两百里地,辗转来到平江县长庆乡一个叫桃花洞的小村落。那时我四岁,妹妹刚出生不久,我们百口自然也就跟随落户的主家姓了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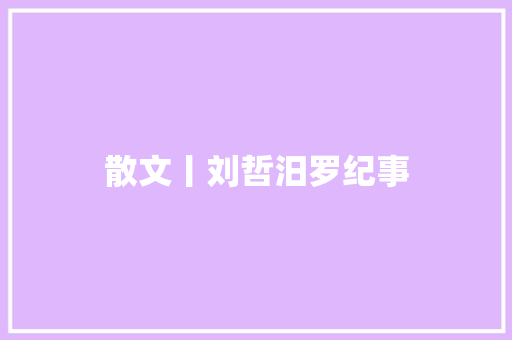
然,水有源,木有根。水木尚有根源,岂可人不敬宗念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我们又随父母举家迁回故土汨罗弼时镇尖塘村落,之后又规复了刘姓。
起屋
回家乡,首先要办理的是住房问题。家乡公民用宽阔的肚量胸襟收受接管了流落在外的游子。生产队的保管仓库,借给我们作为立足之所。虽然屋是漏的,帐子顶上要搭个大脚盆接雨,地面坑坑洼洼,桌子都摆不平整,我们依旧其乐融融;锅是破的,饭也是红薯丝为主食,我们依然餐餐吃的精打光。
父母虽然是裁缝木匠,也算手艺人,但那时做手艺的要上交工钱给生产队,抵公分,才能换复临盆队发的口粮。可能有人会说,工钱不晓得不上交,有钱还买不到米?还真说对了,那个时期,什么都讲操持供应,买粮食须要粮票,有钱还真买不到一个包子,哪怕是一粒米。刚回来,手上也没有余钱,要起屋,从何谈起?砖瓦、基脚石、椽皮、檩子,从哪里来?
母亲是个坚毅的女性。她说,独立重生,丰衣足食。我们自己起屋。没有砖,我们请村落上的劳力扮砖。扮砖,是家乡土语,便是用一个木模子,将泥土用水和湿,家里有牛的就牵牛打圈圈,依赖牛脚将泥踩软揉细,变成熟泥。我家没有耕牛,我们三娘崽就打赤脚踩。然后将熟泥往模子里塞满,用铁丝抹平,取出模子,砖的雏形便出来了,经几个日头晒干,即可用作起屋的砖。扮,是指做砖的动作,要用力将泥往模子抛甩,很形象。家乡很多农活,都要用到扮字,比如扮禾,便是在扮桶摔打稻谷,使之脱粒;扮茴藤,便是指打猪草;扮药,便是指打农药。我们村落叫尖塘,便是由于门口那口塘,头尖尾宽,以是从古到今一贯叫尖塘。尖塘一到夏天,灌溉用水多,头部尖尖处就开始干涸,正是扮砖的利益所。
炎酷暑季,唧唧鸣蝉。人们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少年,在和生产队的男劳力一道,扮砖、切泥、退模、码垛,脸上、身上四处糊满了赭色的泥,满是泥垢的脸上,却是乐开了花。梦境中的华厦,在等着我们,一想起就会有家,干劲自然十足。
瓦,好办,临近生产队有瓦匠师傅,可做上门工。父母是裁缝木匠,兑工办法可以办理。兑工,当时屯子常用的用工办法,便是不付工钱,手艺互换,下次到瓦匠家做上门工,等价交流。椽皮,檩子,我们举家从平江县迁回时,平江县林区的乡亲们半卖半送支持了一部分木材,一部分作檩子,一部分加工成椽皮。父亲自己便是盖匠(汨罗土话,盖匠即锯匠,家乡话“锯”读为“盖”),不用求人,“杀”椽皮(汨罗土话,杀便是切割之意)是分内活,父亲向师父求援,实在师父便是他的妹夫,两郎舅“杀”了几天几夜,五间房的椽皮“杀”齐了。
最难的是基脚石。别人家的基脚石都是清一色的麻石,从玉池山上錾回来,结实耐用。可是我家当时“袄袋里布挨布”(汨罗土话,口袋空空,不名一文之意),没有购买麻石的能力。母亲又发挥了她的聪慧,那便是捡拾石头目,用水泥拌石头目浇筑基脚,代替基脚石。于是,一把烂锅铲,一担烂箩筐,便是我们母子三人的标配,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每当晨曦初启,就出了门,捡石子,西边最远捡到了隔壁大队华盖山,南边最远检捡到了唐家桥的冷水井,北边最远捡到了周家冲,东边是野外和白沙河,没有石头捡。每到深夜,母亲都要用热毛巾帮我敷肩上因挑石头磨破的皮,在母亲的蒲扇摆荡中,我在竹铺上进入梦乡。捡了一个月,石子堆成了小山。石头捡完了,就去白沙河挑河沙,沙又挑了半个月。然后母亲通过兑工的办法请了桐家塘的杜砌匠,上门来浇筑基脚。杜砌匠听说娘带着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捡石头做基脚,硬是靠锅铲捡足了五六吨石子,人工挑了两吨沙,开始不相信。看到那一堆堆颜色互异,大小不一的石子,还有还带着湿印的河沙刹时神色凝重起来:“这石头里,有你们的血和汗,白手起身,不随意马虎嘞。”
砖瓦、基脚石、椽皮、檩子都齐了。1980年夏天,我们的土砖屋终于开工了。生产队的社员们都来帮忙,挖地基、安顿水泥基脚、砌墙、铲墙、树檩子、搭椽皮、盖瓦,一气呵成。五天砌成,我们搬出了一下雨就饱受淋漓之苦的保管房,住进了新居。
由于瓦、椽皮、檩子不足,两间厢房的檩子只能用竹子代替,没有瓦,就地取材,用稻草铺盖。五间瓦房,两间茅草房,终于竖起来了。那两间茅房,一贯伴随我们。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考上大学,参加事情后经济条件有了改进,喷鼻香港回归那一年,我用自己的积蓄,将茅草房改建成了瓦房,并将里外粉刷上石灰。
从砌屋子这件事,母亲让我们兄妹俩认识到了没有钱也能办好事的道理。在后来的人生岁月里,不管碰着什么困难,我们都泰然处之积极想办法应对。在母亲眼里,除了死活,世上是没有难事的。母亲的言传身教,一贯在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伴我们发展。
捅马蜂窝
少年时期,我很顽皮。钓鱼、掏鸟蛋、打雹枪(汨罗土话,拍浮之意)、撩祸(汨罗土话,斗殴之意)、逃学、偷黄瓜、照嘎蚂(嘎蚂,汨罗土话,田鸡之意,用手电筒照住田鸡眼睛,田鸡就不会跑,束手就擒)、捉蛇、偷摘板栗,坏事做尽,常常有人上门告状。告状的结果便是,被娘老子用条刷(竹枝条)打得青红紫绿。母亲从不护短,管教很严,她老人家的口头禅便是“莫瓦(汨罗土话,莫说之意)只一杂(汨罗土话,一个之意)崽,便是只有一边崽,也要打!
”,“细来偷针,大来偷金”,“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世名声臭到老”,一套一套的,我似懂非懂,顽劣依然。
有一次,惹了大祸。
酷暑的一天,闲得弗成。在村落里四处游荡,创造尖塘边上的村落道踏水桥处有一棵苦栗子树,树上又一个马蜂窝,有脸盆样大。村落道是通往唐家桥的必经之路,来往行人较多。我看过电影《不许动》,电影里,一群日本鬼子被小小游击队员捅了马蜂窝,被蛰得鬼哭狼嚎的镜头依然历历在目,有一种快意恩仇之感。一个动机闪过:我何不也客串一回游击队员?我带着妹妹,开始行动了。我头上套了一个化肥袋,抠破两个洞,以便露出两只眼睛看路。妹妹卖力不雅观察敌情,有人来了我就捅马蜂窝。不一会儿,一对母女翩然而至。靠近踏水桥,妹妹发出旗子暗记,我便举起竹篙作去世地一捅,只听得“嗡”的一声,马蜂四散飞出,我撒开两腿,飞也似的溜了,跑到安全地带看热闹。被蛰的是一对母女,住在唐家桥,刚从岭背冲走亲戚回来。只听见母女俩凄厉无比的叫声,妹妹走近一看,母女俩的脸肿得比我家舀水的瓜瓢还要大,肿得红彤彤的,有几个地方还渗着血。惨叫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手足无措将母女俩抬进临近屋场保婶的堂屋,又是冷敷,又是挤毒。母女的家人闻讯赶来,用土车子送到公社卫生院,才分开危险。
母女的家人经打听,知道闹事者是我,按图索骥找上门来。我躲在后背山的红薯洞,硬是藏了两天两夜。扛不住年夜肠告小肠,偷偷溜回家后,挨了史上最严厉的一顿条刷,竹枒箕打脱两根,罚跪两小时。后来才得知,母亲卖掉了三只鸡婆,四只鸭婆,赔了医药费,好话说了一箩筐,才将风波平息。卖了鸡婆鸭婆,就没有蛋生了,本来就没有油腥的炊事就更寡淡无味了。
经由这件事,我幼小的心灵开始反思:损人不利己的事,是一桩赔本买卖,搞不得,对我往后也是一个教训。
我从小便是个十足的毁坏大王,母亲说可能是出生时没有“洗三朝”(汨罗风尚,孩子出生三天要沐浴,洗了就会听话,乖。),内心栓着一个小恶魔,作的孽也就不计其数。好在那个年代没有智好手机可以玩,只能玩一下这种可以亲近大自然的小把戏,聊以丁宁那些孩提岁月。从某种意义上讲,幸亏没有手机,不然也不会有这些惊险刺激的童年糗事,也不会留下那些珍藏于心的影象。
响底皮鞋
我是在铜盆寺县四中读的高中。高中阶段,人逐渐长高了,人也爱索利(汨罗土话,爱打扮,爱俊秀之意)了。很多同学每天将琼瑶的小说藏在抽屉里偷偷读,《六个梦》《金盏花》《一帘幽梦》《在水一方》《昨夜之灯》《只有云知道》《昨夜星辰》,篇篇耳熟能详,而且常常将自己比拟成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人也一每天多愁善感起来。我也不能免俗,暗暗地将自己当成朱诗尧、卢有文(《昨夜星辰》里的男主人公)。朱诗尧、卢有文是什么人?人家可是巨室公子,多金多情。我是什么人?穷小子一个,有上顿没下顿,每天吃的是用家里废旧药瓶子艳服的酸菜剁红辣椒下饭。朱诗尧、卢有文,这些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西装革履,鲜衣美食,我是没有成本比的。但穷归穷,生活的苦楚不能阻断我初开的情愫。后来,学校转来了三个长沙伢子,我们叫他们“三朱”,朱西,朱步,朱先锋。他们穿西装,打领带,脚蹬贼亮的火箭式皮鞋,手中提着一个双卡录音机。更要命的是,“三朱”有绝活,能跳一曲曲很好看的迪斯科,屁股扭得那个真带劲,一到傍晚,就在操场上跳起了《月光迪斯科》:没有七彩的灯,没有醉人的酒,我们在这个时候,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还有《阿里巴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吸引了无数学生们的容身不雅观看,很多青年迈师也加入了尬舞的行列,像模像样地跟他们学跳迪斯科,扭起了屁股。特殊是元旦或国庆学校与班级文娱汇演中,“三朱”及他们带出的团队粉丝大包大揽,大出风头,俨然便是琼瑶笔下朱诗尧、卢有文的活化身。很多女孩子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小情调所折服,男同学女同学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成了名副实在的“人气王”。我们这些穷小子只有干咽唾沫、靠边站的份。自惭形秽之余,只能躲到琼瑶的小说里与怀才不遇、潦倒穷困的落难公子“诉衷肠”,惺惺相惜,去小说里探求抚慰。一天到晚病怏怏的,竟也自觉人比黄花瘦了。
“三朱”的从天而降,给沉寂的校园带来了一股旋风,沉着的水面陡起波澜,搅得民气不得安宁。西装,领带,火箭式皮鞋,成了学习时髦青年的必备行头。更要命的是,穿皮鞋就穿皮鞋吧,“三朱”居然还在皮鞋后跟底钉了一块铁皮,学名叫“响底”,踩在校园的石头地上,一步一响,声音清脆,铿锵入耳,金石碰撞,声声击打在人的心上,叫人念念不忘。
一韶光,男同学以有这么一套行头为荣。特殊是皮鞋上钉响底,也成了标配。首先从青年迈师开始,皮鞋钉起了响底,然后蔓延到学生当中。我虽然斯人独干瘪,囊中羞涩只能向隅而泣,但也不能免俗。西装,领带,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我做梦也没有,但皮鞋响底的金石声,却让我魂系梦牵。没有响底,食之无味,寝之不安。只有回家找母亲哼着要。
我寻思着怎么向母亲做事情,让她给我买一双火箭式皮鞋而且是带响底的那种。让我也在学校里“拽”一回,风光一次,找回朱诗尧、卢友文的觉得。
家里还有一半是茅草房,自然没有余钱剩米去知足我的虚荣心。那时湖南台正播放《昨夜星辰》,我总是去蹭看大队任布告家里的黑白电视,有一集,没一集的看过,对剧情还算熟习。我就向母亲撒了一个谎:“学校要搞合唱比赛,我被挑选成合唱队成员,演出须要,每个成员要一双皮鞋。便是电视里朱诗尧穿的那个模样形状。”
“我只晓得猪要喂食,不晓得你电视里那个舀猪屎(朱诗尧谐音)的鞋子,还要用猪皮做,解放鞋一样的可以上台唱歌。”母亲将我的偶像朱诗尧误解为猪屎牌子,母亲每天忙农活,没有韶光客岁夜队任布告家看电视,不晓得朱诗尧,也不能怪她。我也
“学校演出还要自己置行头?”母亲将信将疑。
“汨罗今年要撤县建市,要搞大型庆祝活动呢,建市,千百年才一次,汨罗要大搞呢!
”情由很充分,不由不信。
一份爱子之心,让母亲妥协了。母亲决定去镇上(那时,家乡弼时公社已改为弼时镇)的福利皮件厂赊一双火箭式皮鞋。恰好我有个叔叔在皮件厂食堂当厨师,可以作包管,母亲便一大早去了镇上。
我在家望眼将穿,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回来,便往镇上方向走去。在皮件厂门口,我碰到了正在徘徊的母亲。母亲见我来了,便定了定神,去找叔叔了。半小时后,母亲出来了,笑逐颜开。手里拎着一双皮鞋,正是我心仪已久的火箭式。带着我去修理皮鞋摊,花两角钱,钉了一副响底。
后来才知道,母亲一贯不进厂,在门口徘徊三四个小时的缘故原由,便是由于脸皮薄,不敢开口求人,为了一双皮鞋赊欠,难为情。
过年时,送了猪,我妈第一件事便是到皮件厂,将鞋款还了。
母亲为了我的皮鞋,在皮件厂徘徊了三四个小时,而且举债提前消费,母亲的宽容和慈爱,让我内心愧疚。穿新皮鞋的喜悦也减淡了许多。
赊皮鞋,让我体验了生活的困难,也让我体会到了提前消费的坏处。自那往后,我做什么事都会考虑量入为出,不由于虚荣心作祟而自寻烦恼。
叫家长
在学校犯了事,最严厉的惩罚,除相识雇、留校察看,便是叫家长。叫家长,是丑事,能不叫就只管即便争取不叫。
叫了家长,所有的糗事都会曝光,家长挨训,学生挨骂。更主要的是,家长还会秋后算账,回家还要轻则挨一顿老骂,骂得蚊子睁不开眼,重则挨一顿老打,打得鼻青脸肿。
我也被叫过两次家长。叫家长的缘故原由有一次是成绩不理想,搞了倒数第二(本是倒数第一,有一位叫伏思的同学因家里有事缺考两门,他排倒数第一),拖了班级后腿。
有一次是犯了事。
那次犯事是有缘故原由的。住宿,学校只供应蒸饭,没有炒菜,寄校生都是用瓶瓶罐罐从家里带的酸菜辣椒,没有油水,常常饿得发晕。有一次,晚自习后,我们饿得慌就发起去偷住校彭老师菜地的菜瓜吃。偷了菜瓜用书包装着,潜回宿舍,准备和大家大快朵颐。没想到当天碰到查寝,被樊校长逮了个正着,菜瓜没收,人写反省。第二天,全校大会上,我被樊校长叫上台亮相。站完台,便是被关照叫家长。
怎么办?偷东西,叫家长很不只彩。绞尽脑汁,我想了个主张,何不叫上表弟,由他伪装舅舅去学校?
表弟经不起我的再三要求,答应了。于是,表弟来到学校,说刘哲同学的父母出去抓副业了,过年才回来。自己是刘哲母亲的弟弟,本日代表家长来开会。在校长办公室和班主任办公室煞有介事地接管了批评,并信誓旦旦答应回家好好管教后,表弟回家了。
我志得意满,这一关总算过了。
年底了,学校搞家访。班主任邹慕清老师来我家,和我母亲拉起了家常,提及舅舅的事。邹老师说,你那个弟弟年纪小很懂事,干事有条有理,待人接物得体诚恳。母亲一头雾水:“我没有弟弟啊?是不是搞错了?”
一句话,我的谎话穿帮。
自然又免不了挨一顿条刷。
自那往后,我不再耍小聪明,由于耍小聪明,一时得意,不能长久。踏踏实实做人,才是王道。
无论父母亲是去他乡钻营生路,还是回故乡白手起身,父母亲那份与生俱来的坚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一代人勤奋朴实、勇于吃苦、务实求进的精神内核。他们在先祖留下生命之源的地方开启了我的聪慧。家乡的每一寸地皮都是滋育肉身和精神的原乡,作为出生在这块赤色沃土的我始终对这里充满眷恋。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春华秋实,千年循环。
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是祖辈一砖一瓦堆砌而成,他们在故土付诸了生平的心血,正如吾辈也终将会把发奋图强的精神传承给后人一样: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薪火传后人,都付笑谈中……
(原载于“新汨罗”公众年夜众号)
刘哲,七〇后,汨罗市弼时镇人。毕业于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出版有报告文学集《武陵风骚》,诗集《城市舞会》,随笔集《我的政协情怀》《从经典故事领悟领导艺术》,著有作文传授教化专著《让经典故事成为你的作文好素材》,政协理论专著《公民政协培训教材》《政协委员培训教材》。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毛泽东文学院(湖南现当代文学馆)班子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