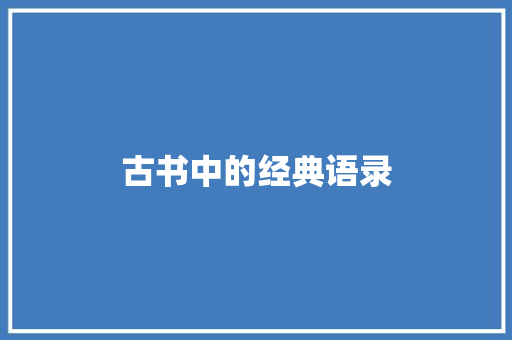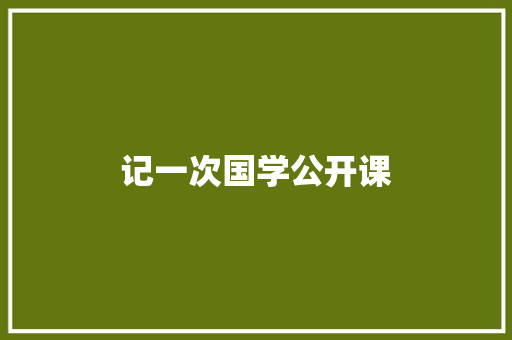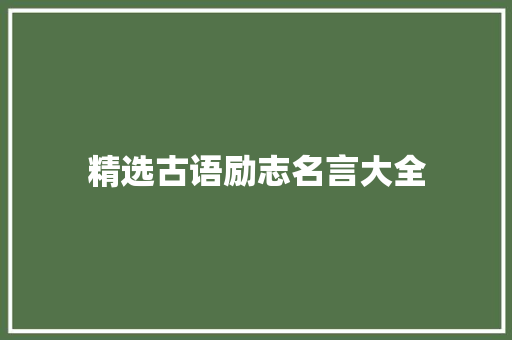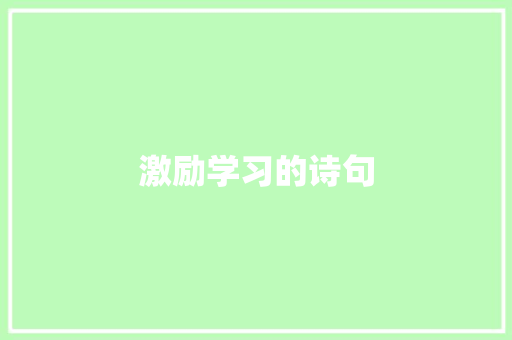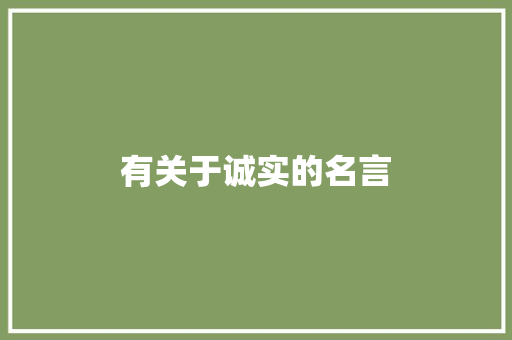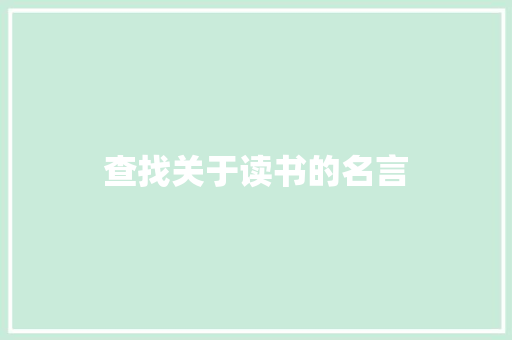役夫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对《乐》进行了整理规范,使《雅》和《颂》各自归属于得当的种别,并确定了各自适用的场合(进行演奏)。”
孔子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我们看起来轻松,但仔细想想,就以为事情量还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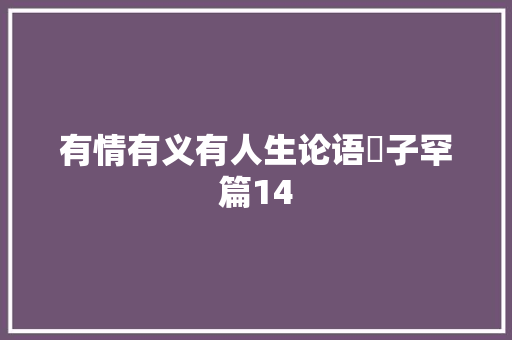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把重复的去掉,选取可以用于礼义教养的部分。……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把它入乐歌唱……)
最要紧的是《诗经》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央,南到长江北岸,如十五国风共160篇,周南11篇、召南14篇、邶风19篇、墉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来自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陈风有10篇等。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口音,不要说这些诗歌都能唱了,能听懂,就已是很难得了。以是说,乐正是一个相称麻烦的事情。
有人从本章句《论语》的字面上理解,说孔子回到鲁国后用了五年的韶光。实在,我想说的是;孔子可能从年轻时到齐国就开始做这样的准备事情了,尤其是漫游列国期间,孔子每到一地,不仅是“必闻其政”(《论语·学而篇》),而且熟习当地的文化传承。
试想一下;孔子一行每天拉着一车子的竹简,在列国之间奔忙,风餐露宿,是怎么样的艰辛吧?如果没有一种义务在里面,我想一样平常人是坚持不下去的。
我们先看“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这句话。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其明年……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又过一年,恰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备了礼物来欢迎孔子,孔子就回到了鲁国。)
公元前484年冬天,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漫游列国。
“反”的本义是手心翻转。《说文》给出的阐明是:“反,覆也。”这里通假“返”字,是返回;回归的意思。
想当年,孔子离开鲁国时,第一站去的是卫国,他怀着满腔激情亲切,多么希望实行仁政,造福天下苍生。然而,漫游列国十四年,他四处碰钉子,要想干成一番奇迹是多么困难啊!
谁曾想;转了一圈儿,他又从卫国不得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鲁国!
孔子回到鲁国后被奉为“国老”。由于孔子不支持季康子实行的田赋改革,自然不会得到季康子的重用。
有一句话叫做“失落之东隅,得之桑榆”。如果真地被季康子重用,孔子大概会成为一名政客,或者是政治家。每天忙于政事,恐怕是没有充分的韶光整理中华文化文籍的。由于不参与政事,这也给孔子更多的韶光去整理中华文化文籍。他删《诗》《书》、赞《易传》、著《春秋》,把这种构筑“天下大同”之“道”,通过笔墨传承下来。《论语•子张篇》中记载:“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文武之道,没有掉在地上,没有失落传,仍在人间流传。贤德的人能认识文武之道的根本,不贤德的人只能理解它的末节,哪儿没有文武之道啊?)由此可知,“先王之道”,不仅仅记录于文章典藉当中,更是在圣贤的心里。
孔子开始做的第一项事情:“然后乐正。”
“然后”,表示接着某种动作或情形之后,相称于现在的“才”。
“正”的本义是不偏斜,平正。《说文》给出的阐明是:“正,是也。从止,一以止。”东汉许慎认为;“正”便是纠正,使恰当。《吕氏春秋•君守》记载:“有绳不以正。”注:“正,直也。”
“乐正”是“正乐”的倒装,“正”是订正,使音乐归正,使其合乎规范的意思。
我们这里须要说说“乐”的。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最早追溯到周代的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礼记》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所表现的是天地间的和谐;礼所表现的是天地间的秩序。由于和谐,万物能化育成长;由于秩序,万物能显现出差别。)
由于音乐对民众具有教养浸染,因此,周朝统治者对“乐”非常重视,并将其列为官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乐”是排在第二位的。《论语》中,对“乐”的记载大概多。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等等。
后来,周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天子失落威,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是这个年代一个显著的标志。“礼崩乐坏”指的是诸侯与士大夫僭越礼制的行为。这种说法出自于《论语•阳货篇》“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一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荒废。)
“乐坏”在当时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乐章、乐谱、音律错乱或遗失落。如《论语•阳货篇》记载的:“恶紫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我厌恶紫色夺去了朱色,厌恶郑声扰乱了雅乐,厌恶利口倾覆了国家。)二是乱用音乐。如,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篇篇》)(孟氏、叔氏、季氏三家举行敬拜时,命乐工唱着《雍》诗,撤去俎器和祭品。孔子说:“《雍》诗上说:助祭的乃是四方诸侯,主祭的天子神色肃穆!
这样的诗句,怎么能用到三家的庙堂里呢?”)第三、会演奏的乐师都离开了。《论语•微子篇》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孔子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养功能,“乐坏”就须要“正”,“正乐”便是对音乐的订正。孔子十分鄙视低俗的郑国的音乐,《论语•卫灵公篇》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乐则韶舞,放郑声”,这便是范例的“正乐”行为。
“乐正”是摒弃那些对人有害的代价取向,把音乐中蕴含的中和之道,如人性中的光明引发出来,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君仁臣忠、兄良弟悌、朋友有信等。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来教人,就学的学生大约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一样平常很受到孔子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学生,为数也很不少。)
孔门弟子中最长于把音乐付诸于教养功能的是子游,他在出任武城宰期间,实行礼乐教养,城中弦歌之声不断,因此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论语•阳货篇》是这样记载的,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役夫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序言戏之尔。”(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以前我从老师那里听说过:‘做官的学了礼乐就会爱人,老百姓学了礼乐就随意马虎使唤’嘛。”孔子说:“弟子们,言偃的话说得对,我刚才不过是句玩笑罢了。”)
仔细思来,孔子所谓的“乐正”,看似进行整理文化文籍的行为,实在是通过“正乐”的办法,来“正”现实的政治,来正的是世道民气!
最让人遗憾的是,孔子教养弟子采取的教材之一——《乐》,在汉朝遗失落了。
我们再来看“《雅》、《颂》各得其所”这句话。
针言“各得其所”出自本章句《论语》,意思是事物或者人都得到适当的安置。
一看“《雅》、《颂》各得其所”这句话,就知道孔子整理《诗经》这项事情已经是大头落地!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这些人摇着木铎深入民间网络民间歌谣,把反响公民欢快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卖力音乐的官员谱曲,末了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在宫廷仪式上奏唱的乐曲;《颂》是在敬拜的时候奏唱的乐曲。
孔子的所处时期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不是“自天子出”了,僭越礼制的征象时有发生,《雅》、《颂》有些时候就没有用到得当的位置上!
《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等,便是最好的明证!
面对这种情形,孔子不仅仅表示愤怒一下就算了,他积极进行《诗经》的编删事情。
听说;春秋期间流传下来的诗有3千多首,孔子编纂《诗经》之后,后来只剩下311首,个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颂》有40篇,《雅》有105篇,《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天真。”“思天真”便是心中没有任何的邪念,便是“正”。
“《雅》、《颂》各得其所”,实在是指“《雅》、《颂》各得其本”,孔子通过整理,明确规定;在朝廷上,宴会上该用什么音乐,该用什么歌词;敬拜的时候该用什么歌词,舞曲,都安排好了,各就其位了;否则,便是不正的行为。把《雅》、《颂》这些诗,本来要表达的诗义之美,也便是人性中追求光明和大道的良善特性显发出来,得到归正。
正的文化教人向善,与人为善,勾引人们走出狭隘的自我,走向光明。分享到这里,我深深明白了朱熹那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永夜”话的妙处了。如果没有孔子等圣贤传道,我们真地恐怕都要生存在阴郁之中。这里的“阴郁”不是详细的入夜,而是说我们看不到前行的方向,看不到光明的方向。
“正”是孔子思想中一个很主要的观点。
针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现状,他通过“乐正”和“《雅》、《颂》各得其所”的详细行为,使已逐步遗失落了的传统,如礼乐制度,得到了规范,这便是“正”。只有民气“正”了,音乐“正”了,政治“正”了,社会才会“正”,统统的出发点都是心在起浸染!
我们在现实中是不是能够心“正”啊?我们靠什么“正”心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浩瀚如海,说的都是如何“正”心。当你心“正”了,用儒家的话讲,你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用道家的话讲,你便是真人,你便是“仙”;用释家的话讲,你便是菩萨,你便是佛。想要造诣一番奇迹,造诣自己,赶紧把自己的心“正”起来;否则,真地可以用唐朝墨客李白《蜀道难》中的开场白:“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上苍!
”得“道”不要说比登天难,至少比翻越蜀道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