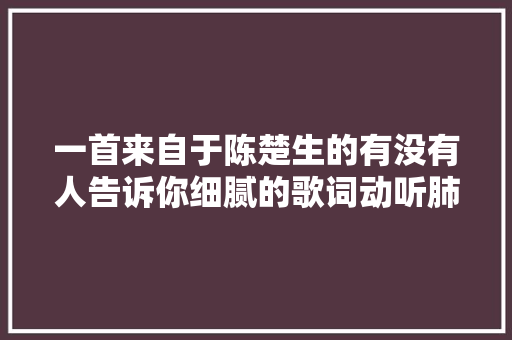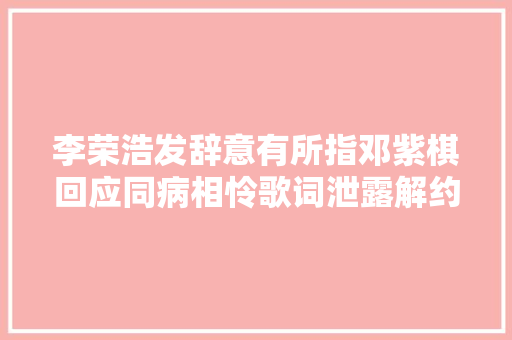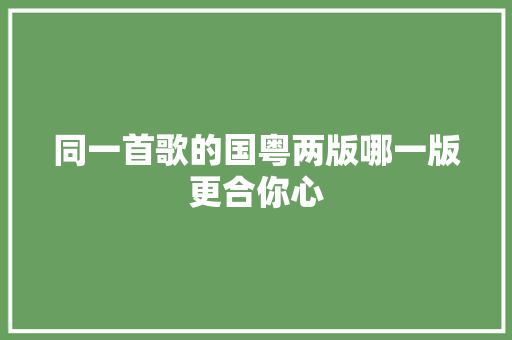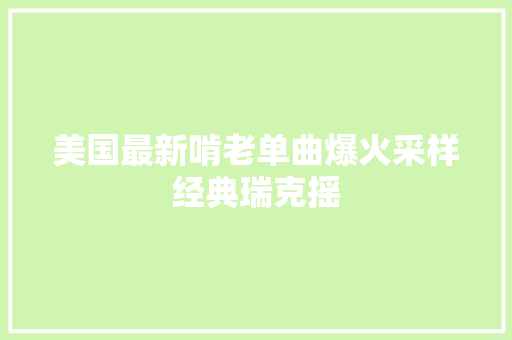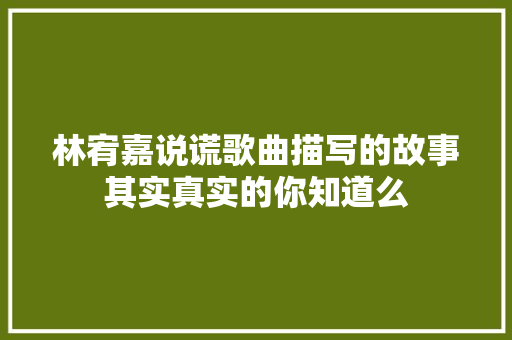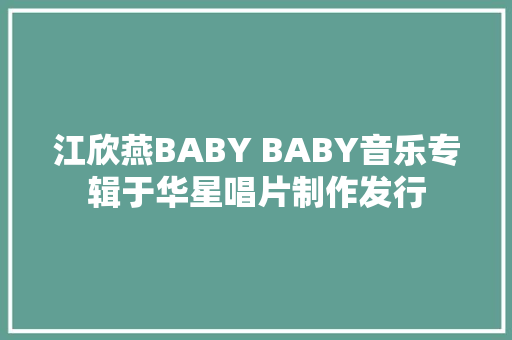南非、作词人赫伯特·克雷茨默因病于伦敦去世,享年95岁。克雷茨默是音乐剧《悲惨天下》的英语作词人,他重新编排这部法语音乐剧的歌词,帮助作品成为环球最随处颂扬的音乐剧之一。他生平与笔墨为伍,曾说自己“先是新闻人,才是作词人”。由于对时势与社会的不雅观察,克雷茨默的笔墨作品隽永深刻。《悲惨天下》的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在悼文中说,克雷茨默为《悲惨天下》留下的非凡词句“将永久活在人们的影象中”。
赫伯特·克雷茨默(左)与法国歌手夏尔·阿兹纳乌尔谈论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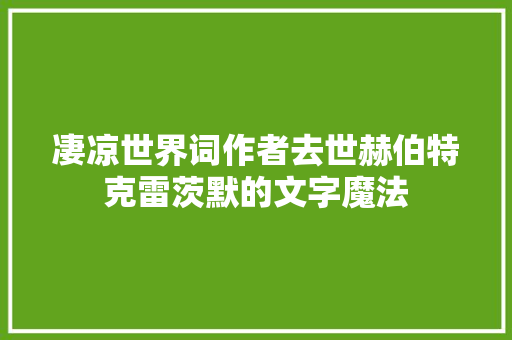
从巴黎搬到伦敦的第一天,赫伯特·克雷茨默身上的钱被小偷偷走了。为了糊口,他同时为伦敦数家报纸写作。这个热爱音乐的异域人也涉足歌词创作。1985年,克雷茨默受邀为法语音乐剧《悲惨天下》撰写英语歌词。一年后,他的创作一炮而红,随后被认定为官方版本。在伦敦西区与纽约百老汇的剧院里,在巴黎街头的示威中,在迈阿密的集会现场,《悲惨天下》中的歌曲一次次涌现。克雷茨默的措辞邪术让《悲惨天下》成为当今最卖座的音乐剧之一。10月,他因病于伦敦去世,享年95岁。克雷茨默生平与笔墨为伍,曾说自己“先是新闻人,才是作词人”。《悲惨天下》的制作人卡梅隆· 麦金托什在悼文中说,克雷茨默为《悲惨天下》留下的非凡笔墨“将永久活在人们的影象中”。
克雷茨默(左一)在《悲惨天下》20周年庆祝现场。
笔墨的共鸣
在涉足歌词创作之前,克雷茨默曾为伦敦多家报纸撰写歌剧、影视评论。他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自己“生平都是新闻人,有时才是词作家”。他生性诙谐,爱打羽毛球也爱看莎士比亚。他的同事回顾,他“总是活气勃勃又风趣”。克雷茨默出生在南非,他的父母是立陶宛人,为逃离沙俄的屠杀来到南非,经营杂货店,买卖越做越大。克雷茨默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他的大哥埃利奥后来成为约翰内斯堡的市长。克雷茨默童年时,南非依然处于种族隔离期间。他回顾:“我在发展过程中就亲眼目睹了不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30与1940年代的南非,你无法躲避残酷、歧视的现实。黑人被视为廉价劳动力与二等公民。我很快意识到,即便我只是一个穿短裤的男孩,我也能享受更多特权。”
“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但我当时没有动力、决心或勇气加入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克雷茨默说。美国的文学与音乐成了克雷茨默躲避的渠道。他听着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等人的作品终年夜。从未受过一天音乐演习但自学了钢琴与手风琴。克雷茨默在南非媒体的采访中回顾,他的父母在家说意第绪语,学校教的是南非语,他却对英语有最浓厚的兴趣。他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好莱坞音乐剧《淘金女郎》。
“由于学习英语,我学会简洁地用词。在新闻与歌词写作中,直接与简洁至关主要。”克雷茨默回顾自己从小就想当,由于那样就能更靠近自己的音乐偶像。在南非时,克雷茨默就为当地报纸写过影评,在学校时为社团音乐剧撰写歌词。为了追求梦想,毕业后他卖掉自己的手风琴来到欧洲,在巴黎的小酒馆里靠弹琴为生,想当小说家却没有成功。
1954年,克雷茨默来到伦敦。他为伦敦当地刊物撰写采访与评论,后来在《逐日快报》做了16年的戏剧评论家,又在《逐日邮报》做了24年的电视评论家。在这段韶光里,克雷茨默采访过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史坦贝克,杜鲁门·卡波特,歌手朱迪·加兰,爵士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与弗兰克· 辛纳屈等文化名人。1979与1987年,他的宣布还曾摘得两项英国新闻奖,获评为“年度电视评论家”。《逐日邮报》评价,克雷茨默的时期是一个可以拿起电话打给电影明星,无需经由层层公关职员把控的年代。克雷茨默采访的文化名人也成为异日后发展的基石。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评论家。”克雷茨默曾说,作为他追求真实。“我认为自己只是不雅观众,为其他不雅观众撰写不雅观影建议。就像消费者指南。我最关键的浸染是指出一部戏是否值得不雅观看。特殊是在票价如此昂贵的本日,我的态度未曾变过。《悲惨天下》上映时,我从未指望评论界的同行会对我部下留情。有时为了撰写评论,我与别人的友情可能会受到磨练。我曾失落去过一些朋友,但他们总会明白我的用意。”
《悲惨天下》在巴黎的演出现场。
比新闻奇迹更辉煌的是克雷茨默的歌词创作生涯。他曾对《逐日电讯报》说,写新闻稿件与写歌词类似,都须要遵守严格的基本原则。“就像被关在牢笼里。这正是吸引我的地方:那被束缚的、笼子里的自由。”1964年,他为歌剧《我们的克里克顿》创作歌词。他曾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配乐写词,也曾为法国歌手夏尔· 阿兹纳乌尔创作。比起新闻生涯,写词更像是克雷茨默的兴趣与发泄。他回顾自己当时“乐意为任何付费的人创作”。克雷茨默将新闻人的敏锐触角与艺术结合。1963年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遇刺数小时之后,他就根据这起悲剧创作了歌曲《他的夏日光阴》(In the Summer of His Years)。
大概正是这种对现实的敏锐帮助克雷茨默在艺术创作上走得更远。1984年,舞台剧制作人麦金托什找到克雷茨默,约请他为法语音乐剧《悲惨天下》撰写英语歌词。《悲惨天下》根据雨果小说改编,描写19世纪法国公民叛逆的故事。克雷茨默的任务是将这个夹杂着政治、历史、战斗、去世亡与爱的两小时音乐剧“英化”。但他谢绝直接翻译法语歌词,由于那些法语词句“像诗歌一样奇妙,充满典故与俚语”。
“你不能翻译一首歌,但你可以重塑一个故事。”克雷茨默说。“‘翻译’这件事使我颤动。措辞可以在一种文化中产生共鸣,但到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就失落去力量。以是我读了原著小说,然后用自己的办法讲述这个故事。”他与麦金托什将两小时的音乐剧拓展为三小时。为了更好地完成创作,克雷茨默向他当时事情的报社申请停薪留职。他把自己锁在家中五个月,思考如何遣词造句。
“写歌词与写新闻是很好的搭配。两者都是在一定约束下操纵措辞。你不能改变旋律。”在著名的《你听到公民的歌声了吗》一曲中,克雷茨默重新编排歌词。他在《逐日邮报》上撰文回顾创作过程:“原版法语歌词中有一种警告‘公民的意志’的意思。对我来说那彷佛是一种政治上的旗子暗记。以是我重写了歌词。将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与歌曲本身联系在一起— 你听到公民的歌声了吗?”
《悲惨天下》电影剧照,克雷茨默为本片撰写了英语歌词。
“我希望我的歌曲能展示鼓舞民气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影响数百万人,让人放下武器。我相信这首代表联络同等的歌曲不仅在1830年的法国有用,在我们这个时期也有用。请大家记住,我的歌词写在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前、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
克雷茨默称,自己从未想过这首歌会红遍环球。“人们问我为什么这首歌如此受欢迎。我的回答是,由于我试图在歌词中戳穿有史以来社会最关键的原形: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让男人与女人变成奴隶,引起社会愤怒,让人屈辱、摧毁人的精神。但歌曲的结尾是‘来日诰日终会到来’。由于我相信真正的希望永久不会消逝……就像我在发展过程中目睹的那些不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成名后,克雷茨默常为黑公民权运动组织和南造孽律声援组织捐款。
1985年,《悲惨天下》首次在伦敦西区上映。它之后成为天下上公演韶光第二长的音乐剧。麦金托什与克雷茨默回顾,两人都没有想到音乐剧会得到如此成功。《纽约时报》的剧评人写道,正是音乐与故事的力量“拨动了第一批不雅观众的神经”。1987年,《悲惨天下》在纽约百老汇舞台亮相,之后连续演出了16年。2012年,好莱坞拍摄《悲惨天下》的电影版本,克雷茨默参与了编剧事情。电影的环球票房终极超过4.4亿美元。他创作的歌词被认定为官方版本,被翻译成22种措辞在环球上映。到2020年,环球有超过8000万人不雅观看过克雷茨默的作品。在61岁这一年,克雷茨默终于得到了他初到伦敦时所希望的那种成功。他在伦敦买了屋子,在《悲惨天下》的纽约首映仪式上认识了后来的太太。他将《悲惨天下》的成功称为“一夜之间涌现的奇迹”。
《悲惨天下》之后,克雷茨默还为英国与法国的电视节目与歌手创作。法国政府曾付与他艺术及文学勋章。2011年,克雷茨默得到英国大英帝国官佐勋章。音乐剧的法语作词人Alain Boublil 与Claude-Michael Schonberg在克雷茨默逝世后写道:“由于有克雷茨默,《悲惨天下》在英语天下中发出了它的声音。”“他收受接管了原始版本,再将它变成能与全天下沟通的作品。他充满朝气、勤奋,有非凡的道德力量。他是最好的作词人。”
撰文— 林湃 编辑— Y 图片— Ge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