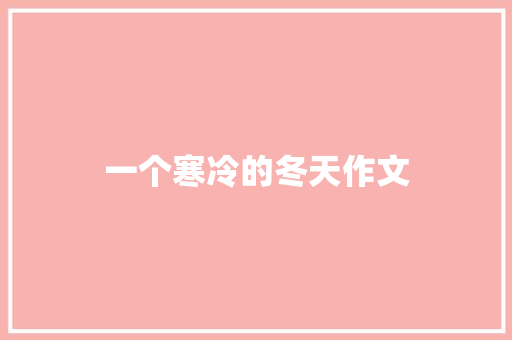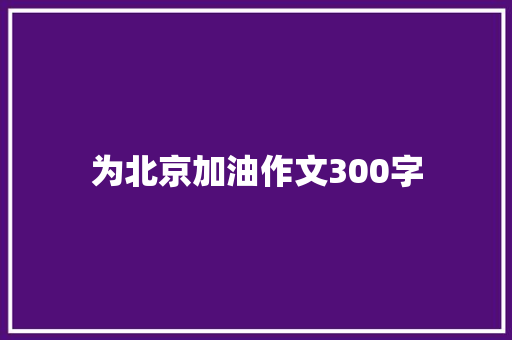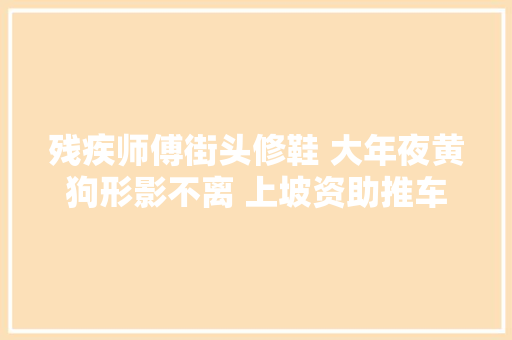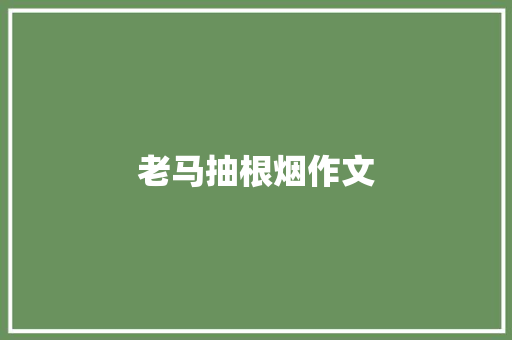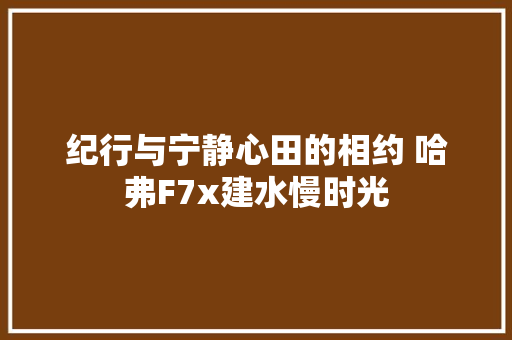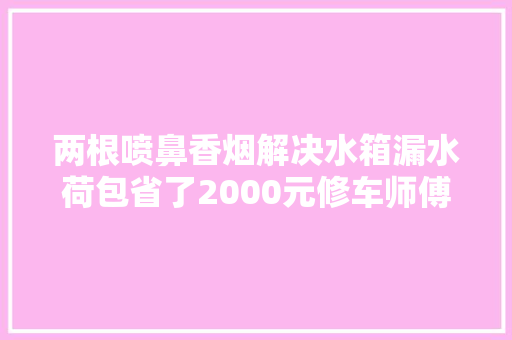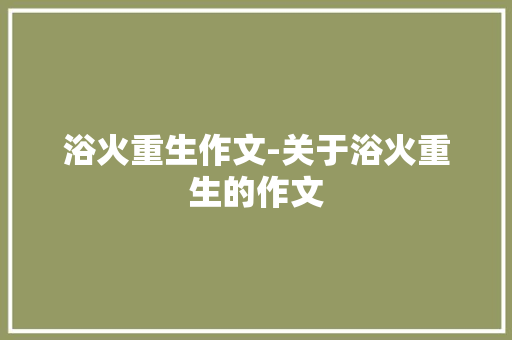云南红河州这座地处西南的边陲古城
用它千年的历史惊艳着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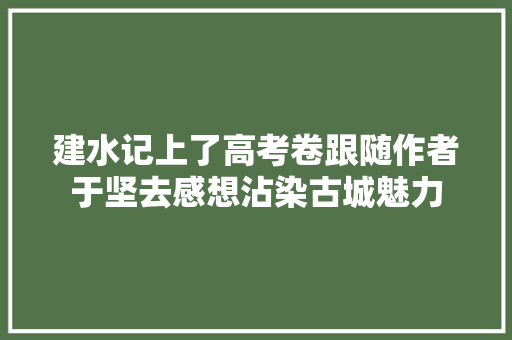
建水朝阳楼
建水上了高考卷
这两天,建水这座边陲小镇,又被高考带上了朋友圈热搜!
刚刚结束的高考语文全国Ⅰ卷中,有两道题目出自云南省著名墨客于坚的《建水记》,两个主不雅观题一个是“剖析大量描写饮食的效果”,另一个是“剖析空间和韶光双线索描写的效果。”
于坚生于昆明,20世纪80年代成名,是“第三代”代表墨客,曾获鲁迅文学奖、公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代表作有《诗六十首》《于坚集》《印度记》《昆明记》等。
对付自己的作品上了高考试卷,于坚表示很意外,谈到详细的题目,于坚表示:“想都没想过,我都答不上来。”
建水文庙石牌坊德配天地
对付建水这座千年古城, 墨客于坚非常钟爱,几十年间,他不断穿梭在建水的大街小巷,体悟建水的建筑、手艺、生活办法。
《建水记》是于坚在2018年出版的散文作品,是一本关于古典生活、建筑、手艺的沉思录,是于坚追问作甚“诗意地栖居”之作,搜集37篇文章及134张照片。
该书曾获2018年 度“书喷鼻香昆明·好书评比系列活动”之“云南十大好书”等奖项。
“人类为什么会有建水城这样的栖居地?它又为什么掉队于时期?又为什么因‘掉队’而鹤立鸡群,不同凡响?数十年来我一贯在想这些问题。”在《建水记》中,于坚如此发问。
于坚表示,这本书,不是一个墓志铭,也不是旅游宣扬广告,我希望见告读者我们到底失落掉了什么?现在建水古城的生活办法恰好是中国人神往和探求美好生活的借鉴。“我写了《印度记》《巴黎记》,加上这本《建水记》,我想写五本书构成一个系列。”
感悟
可以说,《建水记》在古代文化和当代汉语之间搭建了桥梁,生动呈现了云南古城建水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阅读《建水记》,可以让人学会理解一座古城、一座建筑、一种仪式,学会如何安顿、庇护人类的心灵。这次借助语文高考试题,考生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墨客于坚,理解于坚秉承的汉语传统,以及其作品中蕴含的诗意与情怀;于读者而言,可以进一步理解建水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一起通过
于坚的散文
感想熏染临安古城
《建水小记》
作者 | 于坚
云南建水县,古称临安。当年,“临安之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鱼螺之产,不可殚述,又有铜锡诸矿,辗转四方,商贾辐辏。”这是古人说的。有朋友李,退休后回家赋闲,将祖传的四合院老宅重新维修,画栋雕梁,规复旧貌。还整顿出客房两三间,置竹子、金鱼、怪石、古董多少,名曰“静庐”。
朱家花园
春节期间,我和几位朋友前去小住。逐日起来,就在花厅前面读书一阵,在东厢房写字多少,到太阳照到照壁,花厅深处李家的先人牌位逐一亮起来。才逐步磨蹭到街上,喝一碗过桥米线,就去城里面逛。建水还保留着几片老区,小巷像蜘蛛网一样,四通八达,豪门大院,小家独户,比比皆是。只是豪门大院,都成了大杂院,土改的时候就四分五裂了。
人来人往的建水街道 卢维前/摄
有一院的花厅,隔成两半,两家人住,六扇雕花门,一家分三扇,院子中间砌起墙来。仔细看门,大惊,雕得那么精彩,完备在已经公认的清末建水木雕大师高应美之上,有一扇雕的是怪石,石涛的风格,已经进入形而上的境界,超凡脱俗。高应美的作品,写实有余,表现不敷。这样的门如果文化语境不同,完备可以叫做伟大的门,只是伟大这种词,用在中国雕花门上,总是以为造作,中国文化实在不喜好伟大这类的当代时髦名词。
叫圣门可能好些,人皆可以为圣贤嘛。是谁雕的,已经不可考,放在个人主义的西方,这个作者可以名垂青史,但在中国,这个大师只是个木匠,还没有屋子的主人有名呢。作者已去世,罗兰·巴特惊世骇俗的思想,乱套过来,在中国很自然。在民间天下中,文化不是作者的文化,而是无名者创造的文化。景德镇那些伟大的瓷,作者是谁啊?旧时王谢堂前院,飞入平凡百姓家,无边无涯的画栋雕梁,作者又是谁啊?想起我的大学老师张文勋师长西席把庄子的“吾丧我”与西方的“超越自我”联系起来讲,很有道理啊。
人来人往的建水街道
这家的两个娃娃在里面看电视,瞥见我蹲着看他家的门,也不奇怪,已经有好几拨人来看过。这个门像它被雕出来时那样,被用着。它只是门而已,白天开着,晚上关起来。有人出几十万要买,不卖,也没有就取下藏起来,依旧任娃娃开来关去,偶尔还抹点鼻涕什么的。我们与这个门的关系不同,我们是把它当卢浮宫来看。中国过去没有卢浮宫 ,卢浮宫就在人们的家里面,日常生活里面。字画、古玩都是家什,家什也是作品。天人合一。
日常生活不但是过日子,也是修身养性。我们这些被四合院开除了的人,只好把人家的家当成博物馆,自己没有这样的家了么,那样的家就成了审美工具。去世皮赖脸,敲开这家进去看人家的水缸,敲开那家去看人家的窗子。建水真是个活着的博物馆哪,居民好客有古风,你进去参不雅观他们很高兴,节日里,客都贵,还请你吃年糕什么的,只是看罢出来,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假如住在这院就好了。
建水古城一瞥
活的博物馆与西方博物馆不同的是,那些博物馆,你没有住的动机,无数去世者的遗作陈设在那些空荡荡的大厅里面,有些阴森。我很害怕博物馆里空无一人的时候,前年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博物馆,被吓着了,刚刚还瞥见大厅里面有人,忽然就不见了,转头一看,一张表现主义的画正在朝我狞笑。进了这家瞥见一排美奂美仑的栏杆,而主人一家正在桂树下打麻将,只是歪头笑笑说坐嘛,坐嘛。进了那家瞥见人家的中堂挂着钱南园师长西席的字,供桌上摆着建程度易近国期间的制陶大师之一戴得之做的黑陶花瓶,上面的梅花画得那个残酷,字写得那个云烟乱飞。而人家正在忙着宰鸡,亲戚朋友坐了一院子,都咧嘴笑呢。
不知不觉,就看了一天,从某个故居出来的时候,已经太阳西斜了,只是途中在一个大妈开在自己家院子的小吃一人吃了一碗豌豆粉。这一日幸好是建水的云老师和老马领着,这是熟人社会,陌生人可找不到门。云老师是个画家,以前画画,要去西双版纳那边写生,现在不去了,看出了自己老家的好。老马毕业于艺术学院,不画画了,做些设计混日子。活得像个古人,不求上进,没有手机电话,只是读书、修身养性,吹散牛,朋友来么陪着耍耍。
老马说他一个月只用几百块钱就够了。我开始有些不相信,怎么活嘛。后来创造了,老马这么活,穿个可以穿一百年的皮茄克,穿到起包浆,越穿越好看。早上窗外日尺迟的时候,起来在别家的墙外发阵呆,看红杏枝头春意闹,然后去巷子里王麻子开的米线馆吃碗潺肉的过桥米线,四块钱一海碗,倒进肚子一上午就饱饱的了。然后去赵家大院看他家养在石缸里的金鱼。
建水古城的慢生活
金鱼好看,石缸更好看,正面用柳体刻了两行诗,又是书法,又是文学,又是浮雕,又是养鱼的池塘,真是天人和一到和进去又化出来成为天成。那诗刻的是:初日照林莽积霭生庭闱。见金鱼拨开水草帘子,逐渐下了,又顺便与主人下盘象棋,三打两胜。伙计小陈找来说有个花园要设计装修草图,又去事情室画个草图,人家老马没有弱智到使电脑,只用自己的脑。草图让小陈用电脑做着,自己又去云老师家看他的新作,顺便说说世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已经中午两点,肚子有点儿空了,就随便找个小摊,吃几块烧豆腐。
建水的小块臭豆腐驰名云南,吃法也很好玩,中间支一个火盆,火盆上架个有木边的铁烤架,碗碟作料什么的就搁在边上,中间烤豆腐。四边支着矮条凳,供客人入座。烤豆腐的姑娘用一个小碟放着许多干包谷干蚕豆,其余几个空碟就代表客人,豆腐是客人自己夹,想吃哪块吃哪块,你吃一块呢,她往代表你的那个碟子扔一粒包谷。又好玩又好吃。建水的豆腐块,做出来是乳黄色的,火上一烤,就金黄起来,很好看。阁下还烤点猪脚、腌鱼、牛肉、小瓜、土豆片、韭菜、茄子什么的,再喝两口姑娘的婆婆自己泡的梅子酒,那个叫做享受。
西门豆腐
每个人的“吃得喷鼻香”都与大家共享,坐下去就不想走了,总是越吃越多,超过胃口的极限。老马总是在包谷往碟子里响到第十的时候就打住。大概他不吃烧豆腐,刚好朱家院子的梨子熟了,大妈摘两个给他,用井水涮涮连皮吃掉,也就饱了。朝正蹲在水井边洗衣的姑娘们瞅瞅,忽然想起没烟了,又折到燃灯寺旁的铺子去买,干脆到寺里的老柏树下坐坐,看看茶花开完了没有。
建水人世世代代割舍不掉的古井情怀
或者去老李的四合院里找把躺椅小睡一刻,或者去朝阳楼看各式各样的闲人在那里喝茶、敲棋。挨晚,老马回到他母亲的老宅子,老母亲几千年如一日的晚餐已经摆在桌子上,正盼着儿子呢。晚上他读书,不看电视,以是说话呢,都是大家没有听过的,自己琢磨出来的。老马也只有在他故乡可以这么活,古代中国,天下便是家,还有这个意思,家家户户的家都是一个,画栋雕梁、茂林修竹、小桥流水、户户垂杨,明月古井都是家,彼此借景,你家的竹子是我家的窗子前的水墨,我家后花园的桃花是你家前厅的小景,大家共享,家里家外都是家,也就无所谓家了,都是好在的地方。
在昆明你可在不下去,这种家只有孤零零的二三处,而且是重点保护,出了大门,表面就没有什么画栋雕梁,明月清风。钢筋、铝合金、水泥、玻璃、汽车、废气、工地、塑料袋……过条街吓得跟老鼠似的,那么多汽车猛兽般一排地虎视眈眈轰隆响着,油门一踩就冲过来,绿灯的韶光又短,只够跑得快的人飞过去。走个巷就那么宽,汽车跟在你后面按喇叭,要你缩进墙里去让他先行。
建水古城街道 来源:上善建水
打开西边的窗子是西边的大楼,打开南边的窗子是南边的大楼,电灯比玉轮还亮,还一夜地亮着,烦不烦啊。一家一个门,老去世不往来,站在公寓白得像医院停尸间的楼梯过道里发呆只可能是被家里赶出来了或者正在发病。老马这种活法在沿海地区或者我们昆明市恐怕要被送进精神医院里去,居然不为钱去忙,不加入为先富起来而誓不两立的浩荡大军,走投无路啊。老马也不来昆明,难在。他说。说罢走过建水新建的仿古街,那里原来都是老宅,当年要拆迁的时候,曾经引发居民的抗议,电视台也宣布了,以为临安府可以从此逍遥于时期之外了。
建水人的慢生活 临安新视力纪实拍照
事过境迁,创造还是拆了一批。人家以为传统这些旧东西,拆掉还可以再建,古是仿起来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凡百姓家”“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生活天下也消逝了。改成水泥本色仿古外壳,一眼看上去都是格子雕花门,颇有画栋雕梁的效果,细看创造都是用模子浇出来的铁门,有股子去世气。
马云指着一处说,这些羊毫字写得太丢脸了,是哪个胆子这么大,敢写啊。是啊,当今天下,有几个人还在使羊毫?一人骑摩托飞驰而过,我说,便是这个骑摩托大叔写的噻。一行人都笑倒。当年人家建朱家花园,用了四十年。这一条大街,百把间屋子,不过年把韶光,真是一天即是二十年哪。我说。老马,别以为你可以躲到建水,我们逃不脱的事情,你想逃得?一干人听了,都不说话了。
建水文献名邦牌坊
有条街拆得还剩个大夫第,一座遗址,门口还贴着标语。得以鹤立鸡群,想必经由惨烈的斗争。昔日与周围打成一片,和谐亲爱的老宅现在与周围的假古董街道对照光鲜,仿佛站在一排小伙子中间的古稀老者,风雨飘摇,恐怕抗不了多久了吧。这种抵抗并非完备无效,建水现在还剩下的老区,听说已经不拆了,而且还有政策,如果你维修的话,政府还要给你帮助。临安毕竟是文献名邦,文化在这里是有底气的,不像昆明,当年拆得翻天覆地,那么多文化人,没有谁吭一声。
老马又领着去看地皮庙,地皮庙便是过去供奉的大地之神的地方,现在已经不供了。但庙还在。在一个单位的院子里面,闪出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者,听说我们对地皮庙感兴趣,很高兴,立时喋喋起来,又领我们去看,门锁着进不去,只能隔着窗帘缝瞅瞅。里面已经改造成一个会议室,但梁还是老梁。
老者说,建筑专家认为有唐代的风格,这一指示,果真看出那黑洞洞的大梁大气古朴,构造独特。又说个故事,有一天夜里他瞥见地皮公公睡在松柏树下哭,他本来是坐在庙正中间的神龛里面的,天亮后,庙里面的大地之神的塑像就被砸掉了。老者说完,忽然就不见了,实在他和我们作别,还握过手,但觉得便是溘然不见了,我以为他便是那位被撤职的地皮公公。
晚上又随着老马摸进一古董商家里,他从春凳下拖出一个石狮子,面前一亮,当即抱着不放,定睛再看,可没见过雕得这等工夫的,已经发黑了。后面几个里手都瞪大眼睛,等着我放下来,开玩笑了,我怎么会放下来呢?问他要多少钱,说了个数,我大吃一惊,那叫便宜到下贱的地步,这个石匠是个大师啊。当场付款,抱着就走,一起狂喜。里手们跟在后面,悻悻地说,疯掉了,切实其实是疯掉了,我暗想,在1966年的革命后,这个文明古国在文化上,真的是疯掉了,疯到样样都向小年轻看齐的地步。
建水临安府衙
静庐主人的父亲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刚继续祖业,就解放了。就被送到小龙潭煤矿去劳改。二十年后回来,就去世了。主人原来姓唐,也不敢再姓,随着母亲姓李,兄弟几个各自亡命去也。老宅就几十年荒凉下来。重修后,老李工字画,花厅前置一匾,刻大字四个“善与人同”。又在壁梁间补上山水、花鸟、虫鱼、美人,很是养眼。一壁书重修记云“唐氏宅第建于清同治七年,为三坊一照壁。
年久失落修,墙基剥落,多处倾斜,屋顶渗漏,近于坍塌,祖业将毁,忧心如捣,遂发宏愿,倾囊修葺,换大梁二十多,椽八十余,历十月始杀青工,望子孙永宝之。”我读罢感慨,到底是中国人,兴亡多少事,九去世生平,只不过“年久失落修”一笔划过。过去以为“宏愿”指的是建筑长安、罗马这样的伟大工程,谬也,这便是伟大的工程!多年未写古体诗,越日晨憋得一首,为主人抄在宣纸上:“日落竹多影,春高星有光。故宅活气在,主人曾姓唐”。
城里在得烦了,就出城去走走。老李说,带你们去看建水最美的石桥。哎,这个时期,谁还带你去这些啊。真是碰着古人出来领路了。从建水城到大地上也便是几分钟的事情,大地还没有被赶得远远的。风好,光多,花刚刚举头,春天的身影在大地的边上一欠一欠的。有些地方出了绿苗,大部分还是新翻出的黄土,考虑着种什么的样子。远远地瞥见那桥在上苍下诚笃巴结地躺着,土黄色,与周围的泥色同等。
三个孔,中间有个朱赤色八角阁楼。走近才看出是大青石砌成,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快三百年了,桥面的大石块已经被磨得亮堂堂的,桥上有几块石碑,个中一块是临怎知府栗尔璋(便是县长)书写的“天缘桥”三个大字,写得大公至正,气势非凡。在古代中国,一个干部便是一个知识分子,便是墨客、书法家、散文家、画家,他要会这些,他才治得了地方,地方上的秀才、百姓才会口服心折。另有《天缘桥碑记》,说,“三水交汇,旧架桥以木,每夏秋淋雨时,集彭湃奔驰,其势难支。
建水天缘桥
郡人傅翁、王琨倡议,劝众输金,兴工两载,连成此桥”。简洁有力的几十个字,就把事情交代清楚了。这个桥的阁下,还有一道水泥桥,由于天缘桥已经划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再通车了,以是其余修个桥让汽车走,那个桥修得实用,便是一横两竖的水泥东西。当初,修天缘桥的人只知道是要让人和马车可以安然而过,但他们用了十倍的功,所往后来便是大卡车来了,它也是岿然不动。
而且修桥也不但是有个过过路的实用代价,还要赏心悦目,让大家便是过桥也可以修身养性,以是这石桥是当造作品来做的,把人的想像力和实用结合为一,天人合一,与那个赵家那只石缸的做工是一样,以是桥不用了,就成为个玩处看处,附近村落庄里的农人,得闲就来桥上坐着,有石、有书法、有文章、还有神像、石雕的龙头、狮子……看日落月生,听树啸鸟啼。那些百年大树,垂老但繁荣,风吹过,啸声低沉苍凉。中间的阁楼,没有楼梯可以上去,很神秘,想像一番是谁住在上面,脊背忽然凉下来。在此桥上看彼桥,忽然可怜那桥晚景悲惨,一朝弃了,恐怕鬼都留不住一个。
建水天缘桥 来源:建水旅游
下桥连续漫游,瞥见远远地涌现一个村落落,就往那去。先是桥和大树,后面才进入村落庄,鸡站着,猪躺着,狗卧着,人们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说着闲话,有人在修理屋顶,拔房头草,整理瓦片。有一家的门上的门神是清代留下来的,色彩依稀,线条还是很清楚,又是精品,叹口气,担心它不在了。又一笑,想到作者说不定便是刚才牵着转过去的老倌。人家本地人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历史上多少村落庄一把火烧了,门神还不是传到现在。
经历了1966年的文化革命,还能见到这些,将来什么也是小事一桩了,不必操心,天不灭,到亦比灭。这村落庄老李来过多次,他像是他自己的博物馆,领我们看这家的栏杆上的石狮子,看那家院子的檐子上的飞鸟。有一个院子曾经是满院生辉,梅花蝙蝠,棋琴字画,宋词唐诗,现在凋敝冷落,满地的猪粪,一匹神骏在木梁上翘起来,就要逃遁了。
建水双龙桥
先前的主人想必知书识礼,修身养性已经有些工夫,他的后代却重新成为文盲,不知道我们在院子里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烂屋子么”,老宅子的继续人护着恶吼着的狗,它把链子挣得咔咔响,赶紧退出来。
小路靠墙到处堆着修老屋子换下来的旧花砖,和成要了一块,人家大方得很,拿嘛拿嘛,砖面上有花纹和凤凰,非常俊秀,如今的砖瓦厂可不会生产这种奢侈的东西了。村落庄后面靠山的地方是铁路,铁路是通往石屏方向去的,米轨,当年法国人修了联接云南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中国人修了联系滇南的个碧石铁路。铁路已经被植物界绿化得差不多了,隐没在荒草和树林之间,一伙人顺着铁路走,穿过鸟语花香。
建水米轨小火车带你感想熏染慢光阴
米轨带你感想熏染慢光阴
云南大地便是有这种本事,再怎么反自然的东西,都无法把这个地方变成沙漠,几场雨水一阵风,花园就重新一个一个长出来了。末了走到一个黄色的小车站,法度模范方盒子构造的建筑安着中国的曲线飞檐,被改造成中西合璧,这么改造没有什么实用处,要说实用法国人设计的车站已经够实用的了,本来便是他们发明的么,加些中国风格进去,完备是为了顺眼。车站阁下,一树洁白的杏花正靠墙亮着,花瓣落了一地。
建水临安站
这是一个铁路储备站,一直客车,有两小我员守着,他们在车站后面种了蔬菜瓜果,整顿得像是个田舍大院,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很多东西,大多与中国传统生活履历抵牾,但铁路可以接管,比汽车更可以接管,污染小、有亲和力,满车厢的人总是可以造出集体主义的气氛。不像汽车那么孤独,那么个人主义。
火车只是速率慢点,这个时期就嫌弃了,哎,都忙着奔个什么。车站的师傅留我们吃午饭,看着地上堆着一堆刚刚从地里面刨出来的土豆,黄生生,泥漉漉的样子,都想留下了,但已经说好去黄龙寺吃烧豆腐和凉米线,只好割爱。离开车站,到得黄龙寺前,一排屋子前面都是烧烤摊子,人家早已吃的杯盘散乱,是什么味道,看看那景象就知道了。
白天看博物馆,晚上回来享受李家的家宴,大多数韶光坐在院子里闲侃,看着照壁亮起来,残酷如雪,又一点点暗下去,变成黑猫。忽一日,问起是几号了,居然已经由了六天。越日回昆明,老李送到车站,客气话讲了一起,现在很少讲了,以不客气为当代。老李其人,身材细长,玉树临风,说话总是垂着眼睛,很含羞的样子,满口的临安方言,听起来像江南古戏中的韵白。(马映竹 金贤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