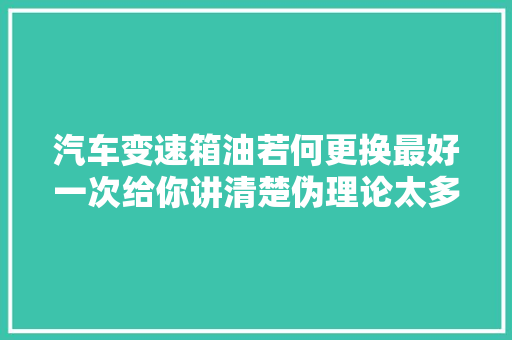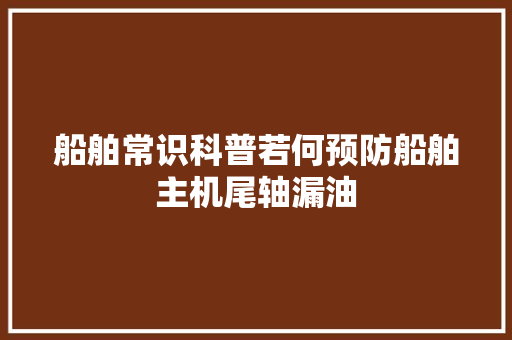【知识·军旅·人生】
三代四型、有方有圆、大小不一、轻重互异……在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藏着这样一批神秘的“铝匣子”。在外人看来,这些带着蓝色屏幕的“铝匣子”长相古怪,不知做何用场。懂行的人知道,它补充了中国国产重力仪研发的空缺,使我国成为继俄、美、德之后第四个研制出捷联式航空重力仪的国家。

这些被称为“地球CT仪”的重力丈量“神器”,由一支成立时均匀年事不到31岁的年轻科研团队,耗费17年韶光自主研发而成。它的出身,为中国核心重力测绘装备的国产化开辟了崭新天地。
冲破垄断:“五年内攻陷这个山头”
9.8N/Kg,这是人们对重力系数的常规认知。但实际上,由于地表布局繁芜,不同地区的重力系数相差甚大。在该团队卖力人吴美平教授看来,“精确的重力信息分布图已成为国家主要计策资源,没有自己的重力信息分布图,远程精准打击就无从谈起。”
绘制精确的重力信息分布图,就像给地球拍“CT”,眇小的重力偏差极可能引起“误诊”,从而导致导弹偏离预定落点几百米乃至上千米,或者影响潜艇的导航性能与计策暗藏能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精确的重力信息分布图对国家安全的主要性进步神速。而环绕军用重力丈量领域的技能博弈与封锁也频频上演。2003年以前,我国对海内地形繁芜的区域进行重力丈量,只能依赖入口的高精度重力仪。而一台重力仪,每每要花费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由于重力信息敏感,一旦仪器涌现小故障,无法返修,只能直接报废。与造成巨额的经济丢失相比拟,更让人无奈的是“有钱都买不到”。于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航空重力仪的需求呼之欲出。2005年,国家863操持将此目标列入项目名单,并在全国范围内探求研发机构。
“五年内攻陷这个山头!
”时任自动掌握系副主任的吴美平教授,带着一支年轻的6人军队,接下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项目申请成功后,大伙儿马一直蹄,投入到紧张的研发之中。一间不敷20平米的屋子,成为了他们简陋的实验室。夏天光着膀子调试设备,冬天裹着被子推导公式,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从早上亮到早上,焊接仪器烧坏的电路板也在角落里堆了一摞。第一年,吴美平教授就瘦了20斤,妻子抱怨:“虽然家就在学校门口,却像是两地分居。”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后,第一代捷联式航空重力仪试验样机终于出身了!
在距东海海平面400米高的飞机上,当航空重力仪的显示屏上涌现了一条条变动的函数曲线时,大家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可以松一松了。这台试验样机,成功测出了我国自主研发重力仪的第一批重力数据,内符合精度达到5mGal/10km。
困境赶超:“在颠簸中测出头发丝1/100的位移”
数据测出来了,可吴美平团队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的“山峰”——提高丈量精度和空间分辨率。
于是,第二道坎又摆在了面前。离样机中期验收的韶光仅有1个月了,可样机测算数据距预想指标还遥遥无期,每个人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基于国产器件不可能研制出高精度重力仪。”吴美平团队决心向一些专家的论断发起寻衅。吴美平教授给大家讲钱学森带领老一辈专家在各部件加工精度有限的情形下,成功研制出导弹的故事。他们瞄准研制“中国芯”的新方向——优化系统设计与算法。一行行实验数据、一条条测试曲线、一份份实验测试方案……项目组成员聚在实验室里研究、剖析、谈论,险些没有周末。近半米高的笔墨资料和实验数据摆满案头,他们逐字逐句比拟每一份资料,反反复复剖析每一个测试数据。这个从0到1的过程,也把团队成员逼成了“多面手”,“搞电气的得懂机器设计和软件流程,做机器的得明白电气走线和滤波算法。”
用国产传感器在飞机翱翔中测出10-6g量级的微弱重力非常,其难度相称于在颠簸的车辆中去测车内设备一根头发丝1/100的位移,这可能吗?完备可能!
当他们将国产加速度计安装到优化设计了的仪器中,测出了比传感器出厂精度指标还要高的精度时,连生产厂家都无法置信,“这相称于用卷尺测出了游标卡尺的精度。”
千淘万漉虽辛劳,吹尽狂沙始到金。2009年,团队终于研制出第一代具有完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捷联式航空重力仪工程样机——SGA-WZ01,精度达到了1.5mGal/5km,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美、德之后第四个研制出捷联式航空重力仪的国家。
2012年8月,应丹麦技能大学的约请,吴美平教授带领3名团队骨干,携带SGA-WZ01飞赴丹麦,参加北极格陵兰岛航空重力联合科学实验,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力仪在国际舞台上的“首秀”。令人骄傲的是,这台“独苗”不负众望,完美完成8个架次7500km的翱翔试验。
当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翱翔试验重力数据初步处理结果的一瞬间,欢呼声沸腾起来,国际测地协会副主席Rene Forsberg教授也微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航空重力丈量仪器。”
寻衅极限:向南极与珠峰进军
2019年11月17日,两套新型捷联式重力仪被封装进“雪龙号”科考船的大舱。它们将与吴美平团队的曹聚亮研究员一起,横跨半个地球,直抵南极中山站,加入我国第36次南极科学稽核队固定翼飞机队。
这次携带自主研制的重力仪挺进南极,不只是全校科研团队首次南极科考,更是在全国此领域开了先河。
“在南极高纬度和极低温的环境条件下,惯导系统初始对准精度低落,自研的捷联式重力仪精度和可靠性如何,能否顺利完成丈量任务?”纵然对自家的设备信心满满,但一想到即将面对的是南极分外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景象环境,曹聚亮心里难免捏了把汗。
试验伊始,就遇上了电源不敷的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重力仪在翱翔过程中不接入飞机机载供电系统,只能用自带电源。可“一旦开启实验,设备不能断电,而携带的UPS不间断电源在低温下仅能够续航5个小时,飞机一架次8个小时,剩下的3个小时去哪里找电源呢?”
思来想去,曹聚亮找到办理之道——改装UPS。在队友的帮忙下,他将UPS充放电回路分开,提高供电效率,现场制作了一个24V/100AH的超级“充电宝”,充满电后可担保重力仪事情10h以上,办理了实验电源不敷的问题。
可翱翔试验期间,机载的测冰雷达又出了故障,功放报警,旗子暗记无法发射出去。翱翔高度不断攀升,高原反应也愈加剧烈,精通电气系统的曹聚亮只能一边吸着氧气,一边定位故障缘故原由并进行临时性修复,担保了科考任务的顺利完成。
就这样,在长达3个月的南极科考期间,曹聚亮逾额完成捷联式重力仪的各项丈量任务,首次成功获取了南极伊丽莎白公主地、埃默里冰架区域的第一手重力场数据。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载荷首次实现在南极的运用示范,对拓展自主载荷运用和提升我国南极稽核监测能力有主要的意义。
2020年初,在海上流落了43天,曹聚亮终于回到了上海,正遇上海内疫情肆虐,他被滞留在了上海隔离。隔离期满的前一天,5个月未归家的他,又接到保障捷联式航空重力仪珠峰丈量任务的命令——15年后我国重启珠峰“身高”丈量,全球瞩目。
深知任务的主要性,第二天,本该飞回长沙的曹聚亮,二话没说坐上了前往拉萨的班机。
5月的珠峰北坡,白雪皑皑。2020珠峰高程丈量登山队队员携带雪深雷达、地面重力仪等仪器设备向最高点攻顶。
搭载吴美平团队自主研制的捷联式航空重力仪的“航空地质一号”飞机,在珠穆朗玛地区1万米高空像犁地一样沿着事先设计好的线路翱翔并获取空间重力数据时,日喀则机场的停机坪上,现场事情职员也在耐心等待着飞机的降落。每飞完一个架次,趁着飞机落地休整空隙,大家赶紧从重力设备中导出测得的数据。
“对取回的丈量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剖析后,我们得出了两张珠峰重力模型图。”指着电脑上两张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区域重力场分布图,曹聚亮说:“这两张图的数据一张由我们的航空重力仪测出,另一张由国外最前辈的同类装备测出。你看,丈量结果基本同等。”这意味着,在极限环境中,吴美平团队所研发的捷联式重力仪性能与国际最前辈的同类装备已不相上下。(本报 刘小兵 本报通讯员 龚仪 焦西凯)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