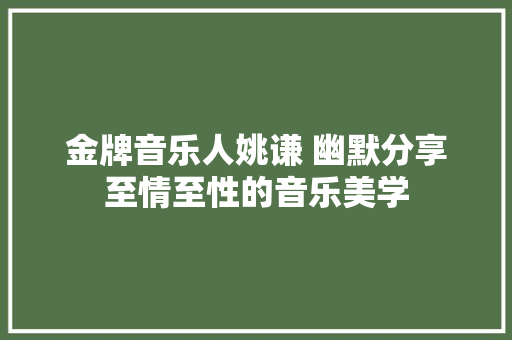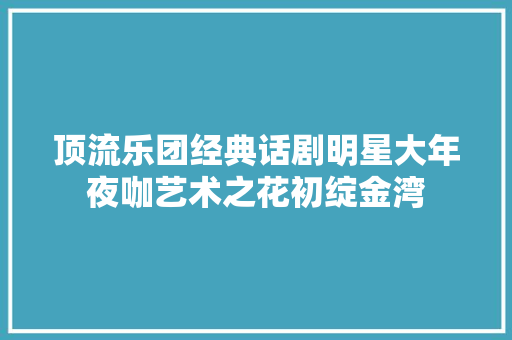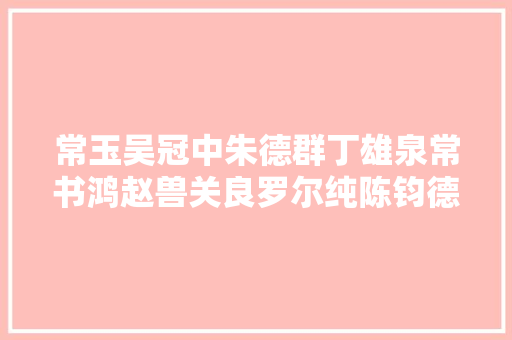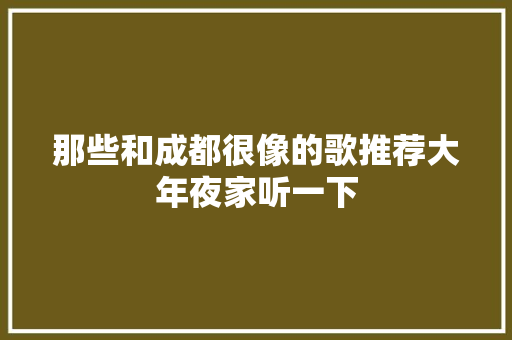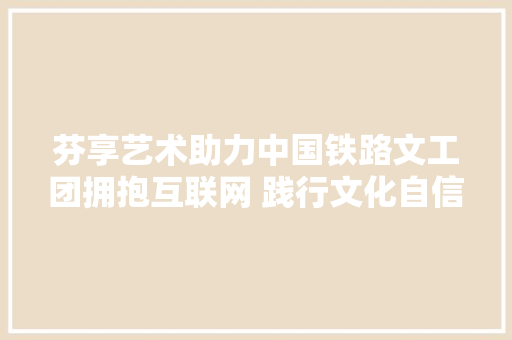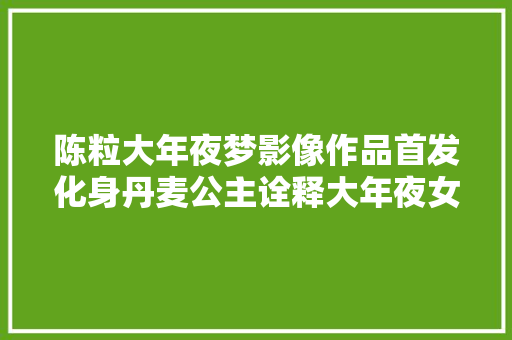歌唱家李光羲谈歌曲《松花江上》
——“心声岂止三千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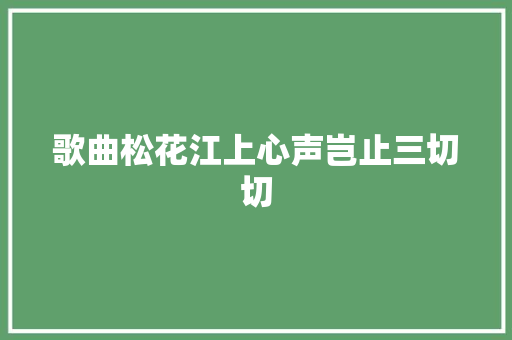
大家常问我是如何演绎《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我回答:“没有演绎,《松花江上》唱的便是我自己,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常听闻亲戚朋友家十几岁的孩子,溘然间就不见了,被日寇抓去做苦工,再没回来。每天胆战心惊,常年受饿受冻,唱歌成了我儿时唯一快乐的事。我从小便会唱《松花江上》,一开始并不懂它的深意。熟年冬天,我在上学路上看到几辆简陋的木板车,拉着冻去世的同胞,那残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1945年,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父亲带着我上街,我指着地摊问他:“那些白珠子是什么呀?”父亲见告我,那便是大米。当年已经16岁的我,才第一次知道大米为何物。统统所见所闻,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歌声。
每当我唱起《松花江上》,昔日山河破碎的场景与悲愤便会涌上心头,演唱时泪水常模糊了双眼。
1936年,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宣扬事情的张寒晖,目睹西安街头东北军民无家可归的流浪与彷徨,谱写出了《松花江上》。“西安事变”前夕,这首歌从西安一所中学唱响,其后迅速传遍全国。
我最难忘的是1964年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过程。我在第四章《抗日烽火》中演绎这首歌。周恩来同道亲自提出歌词的修正见地。对我而言,那次演出是艺术熏陶,也是思想教诲。
“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一曲《松花江上》,唱出的何止是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声?它是亿万中华儿女悲愤交加、哀求还我山河的呼声!
它使人泪下,又催人奋起。我不应把它仅仅理解为是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它已经成为亿万人高唱的战歌。无数人闻曲悲叹,燃起革命激情亲切!
无数青年高歌提高,奔赴抗日沙场!
一同参演《东方红》、曾在西北战地做事团的歌唱家王昆见告我,她与抗日前哨的战士合唱过《松花江上》,边唱边堕泪,越唱越冲动大方。她说:“是革命给了歌曲百倍的豪情和万千的气候。歌唱是艺术,更是革命的号角、尖兵和鼓点。”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此让我对这首歌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歌者用声音塑造形象、通报情绪,该当努力让听众体会歌曲的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松花江上》的动人,在于丰富的层次和意蕴。旋律上,这首歌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办法展开,倾诉性的腔调贯穿全曲。歌词上,它以“怀故、流落、呼唤”的感情脉络递进式地深入民气。以“森林煤矿”“大豆高粱”“同胞”“朽迈的爹娘”开篇,诉说家乡的俏丽富饶。之后,诉说丧家的哀痛、亡命的惨境,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公民带来的深重灾害。歌曲末了,用饱含感慨的发问,唱出声声呼唤。“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将全曲推向高潮,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张寒晖当年噙着眼泪写出的歌,一次次流进我心,我又将这种深切的感想熏染通报给不雅观众。由于《松花江上》,我被不少不雅观众评价为“听他唱歌让人直掉泪的演员”。我想,只有这样深耕时期、心系公民的音乐作品,才能迸发出如此强烈的艺术传染力。
我今年92岁了,很少再登台演出。但我坚信,歌唱本身,也是一种任务、一方教室。我有责任将这样的歌曲和歌曲中的历史传承给本日的年轻人。
几年前,我曾受邀给中心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们传授教化《松花江上》。我见告这些“90后”年轻人,声音即是零。由于如果只追求吐字发音,过度侧重技法,忽略情绪表达、生活体验,将“声乐艺术”变成了“声音艺术”,艺术效果便即是零。鉴古知今,才是歌者的真正“底气”。我希望年轻人提升对历史的理解力,在歌曲中感悟人间正道与生活真谛,创造有生命力与传染力的音响。艺术在传染他人的同时,也在实现歌者自身的生命代价。
我还见告这些年轻人,当年奔赴抗日一线的战士们,那时的他们也正青春。那些斗志昂扬的中国少年,甘将热血沃中华,用无数生命之光点亮了一个民族的光明,让子孙后代享受着他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青年偶像!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声。品味《松花江上》,它悲怆的旋律,激荡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上,成为那段血与火岁月的印记,使我们激愤,使我们复苏,更勉励我们武断信心、接续奋斗。
(本报王瑨采访整理)
(来源:公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