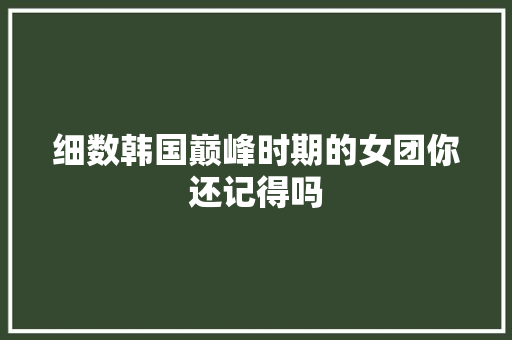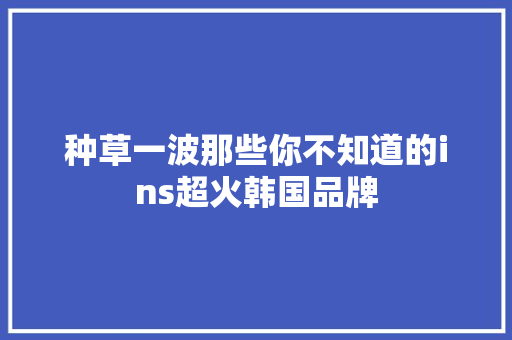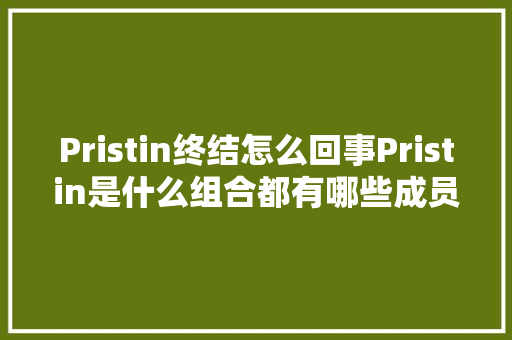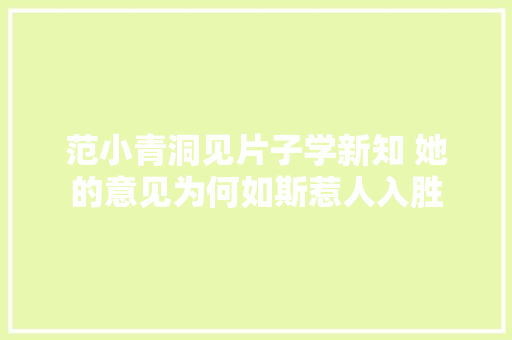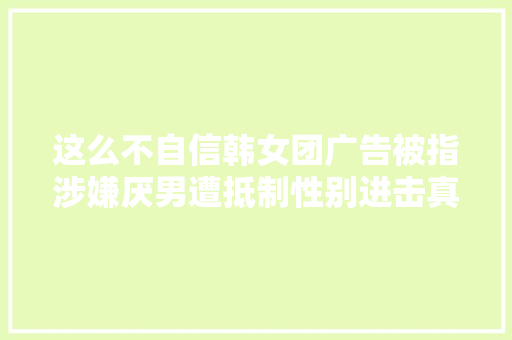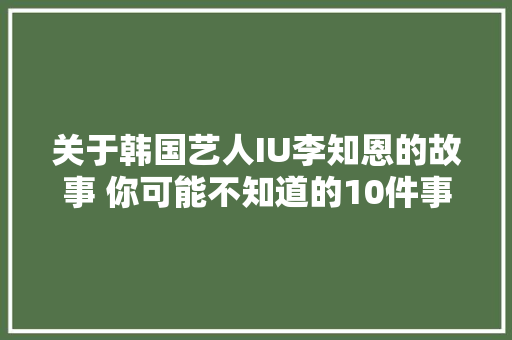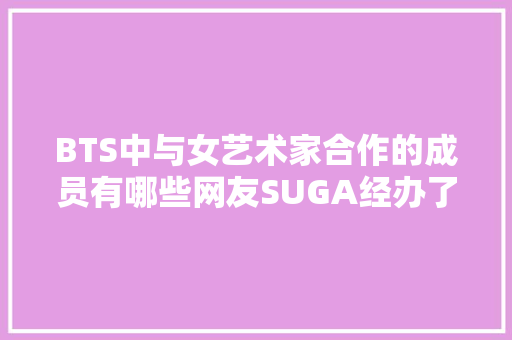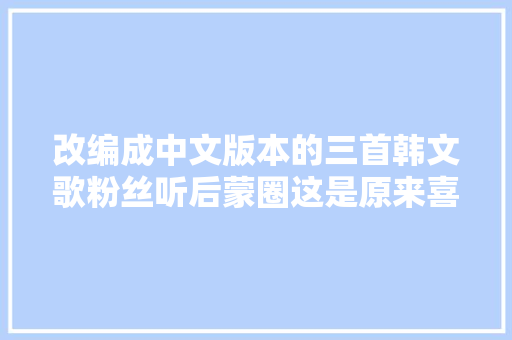这本关于K-pop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迟到的书。这里“迟到”是两个意义上。首先,这本书原版出版于2015年,按照作者迈克尔·富尔(Michael Fuhr) 在书里写的,为这本书做的野外事情是在2008年到2012年。从K-pop更新换代的角度而言(今年年初的歌无疑现在已经是老歌),一本基于10多年前的K-pop状况写的书,是否里面的知识已经迂腐?其次,更主要的是,中国作为K-pop最早的外洋吸收国,特殊是贡献了指称韩国盛行文化的“韩流”(Hallyu)一词,却20多年来没有涌现以中文写就的关于K-pop的系统性深入学术磋商(只有单篇论文和韩语专业的先容性教材)。相反,如果以鸟叔的“江南STYLE”作为K-pop走向西方的标志性事宜,其盛行在西方不过10年,但在英语学术界,从社会学家John Lie 2014年的著作《韩流:韩国的盛行音乐、文化遗忘与经济创新》(K-Pop: Popular Music, Cultural Amnesia,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in South Korea)开始,以英语写就的关于K-pop的学术专著,不完备统计至少有6部(这还不包括关于韩国嘻哈的研究以及更多的论文集),作者遍布美国、加拿大与欧洲。也便是说,K-pop在中国20多年来的盛行并没有转化为足够有代表性的理论话语。
巴黎政治学院媒体学者金润荷(Youna Kim,音译)主编的出版于2023年中的《韩国盛行文化导论》(Introducing Korean Popular Culture)是我目前见到的西方学界与K-pop有关最新学术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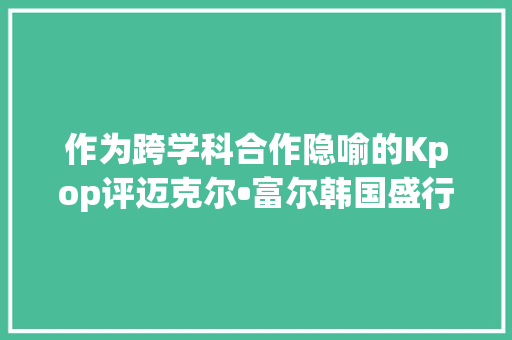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笔者开始为澎湃新闻贡献与K-pop有关的采访,目前统共四篇:2021年10月对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金暻铉的采访、12月对耶鲁大学高玉蘋的采访、2022年7月对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吴周妍的采访、2023年7月对伦敦VA博物馆策展人罗萨莉·金的采访。前三篇都已经翻译成韩文,在《韩国盛行音乐杂志》(韩文杂志名대중음악,英文The Korean Journal of Popular Music)杂志上揭橥。而回过分来看,除了被翻译成韩文外,前三篇采访都有很强的环球性与即时性,在对金暻铉采访时,由于《鱿鱼游戏》的爆火,金暻铉频繁做客于西方各个媒体与电台。对高玉蘋采访后,韩国、西方各大媒体接连对高玉蘋进行采访和宣布,目前已经有24篇。在对吴周妍采访后,韩国、西方各媒体接连对她的新书进行大量宣布。但中国的其它媒体,除了喷鼻香港地区的《中国南方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对高玉蘋做了干系宣布,都没有对她们进行专访。
高玉蘋耶鲁主页上展现的自澎湃采访以来对她的大量与K-pop有关的采访与宣布
如果,我们纯挚说这是由于K-pop只是韩国、西方征象,而不是中国征象,无疑不符合事实。从2021年开始,与韩舞翻跳有关的活动在中国各大城市空间兴起,听说上海现在各个阛阓都有韩舞活动,而在海内各个高校,也有越来越多学校官方参与主理的韩舞活动。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中国粉丝对K-pop专辑的购买,仍旧是K-pop家当紧张收入大来源之一。如果站在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将K-pop的环球盛行看作目前韩国以输出盛行文化为主的成本扩展与积累,中国无疑是K-pop进行原始积累的产地。从环球成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欧洲如果没有从16世纪在美洲、非洲进行的300年原始积累,无疑没有能力在19世纪去寻衅从奥斯曼到中国的欧亚大陆传统帝国势力。同样,如果没有K-pop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16年将近20年在中国的成本原始积累,K-pop家当恐怕也没有之后去进军西方的成本与能力。
海内韩舞翻跳活动
只管K-pop粉丝大概会以为天下粉丝是一家,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粉丝间无疑有国别的等级差异。从同时不雅观看过一个三代团在日本与中国演唱会的中国粉丝那里,我理解到该团在日本演出时唱跳无比卖力,但在中国的演出就非常随意。如果我们把天下K-pop粉丝看作一种“环球情绪劳动家当链”,比较西方、日韩,中国无疑处于家当链中下端,而这背后又有环球经济分工与种族构造等更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界无法像西方一样不断提出关于K-pop的理论化阐明,去勾引环球关于K-pop的舆论话语走向,则是这一家当构造在思想文化上的反响。对付K-pop环球家当链,中国彷佛只有贡献专辑销量的地位,而没有能力去进行理论阐明、去建立对这一当下环球最火的盛行文化征象的话语权。
因此,当我得知江苏公民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个中包含这本富尔2015年的著作《韩国盛行音乐》(Globalization and Popular Music in South Korea: Sounding Out K-pop,我更乐意翻译成《环球韩国盛行音乐》)时,我无疑认为这是汉语学界对K-pop环球盛行的一种迟到的反应。当然,正如一开始所说,这本书在目前西方K-pop研究里,无疑不是最新的书。如果有出版社找我推举翻译西方K-pop研究著作,我可能会首先推举金久用2018年的《从工厂女孩到韩流女星: 发展主义的文化政治、父权制与韩国盛行音乐家当的新自由成本主义》(From Factory Girls to K-Pop Idol Girls: Cultur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alism, Patriarchy, and Neoliberalism in South Korea’s Popular Music Industry)。只管这本书关注的以二代团为主,却对K-pop进行了具有历史和理论深度的阐明,将K-pop的兴起放在1960年代以来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脉络里,建立了对K-pop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框架(当然, 作者由于对K-pop短缺内部者同情视野,也导致这本书在英语学界主流接管度不高)。其次是笔者做过采访的金暻铉的《霸权模范:21世纪的韩国盛行文化》(Hegemonic Mimicry: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这本书对K-pop在内的韩国盛行文化建立了后殖民理论框架,将韩国盛行文化看作是美国盛行文化的东亚变种。
比较之下,笔者在2021年初第一次读富尔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时,感想熏染不深,更以为这本书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像金久用、金暻铉那样非常有力地把K-pop放到一个理论框架内。然而三年之后,笔者通过中文版再次读这本书时,感想熏染却非常不一样。只管,我仍旧认为这本书中央论点没有像以上两本书那样明确,但这正好构成了这本书一大优点,即没有只依赖一种理论和历史框架对K-pop进行彻底定型式谈论,而是包含着很多更奇妙的繁芜思考。这种阅读感想熏染的变革与我对K-pop的理解不断深入有关,更主要的是,与我一开始把稳到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以为这本书是不是有点“过期”不同,我非常惊异创造作者基于K-pop二代团时期的一些思考,在本日K-pop环球大火的四、五代团时期才彻底展现出来。
在第一章,作者以三个花絮(韩国文化广播公司举办的周六打歌舞台、遍布韩国公共空间的K-pop视频、德国西部一个中型城市里广场上四名白人少女对K-pop舞蹈的翻跳)引入关于K-pop的谈论,提问是什么导致K-pop成为一种环球征象,并提出只管音乐不完备是K-pop的核心,但在个中不可或缺,进而暗示,K-pop并非所谓的“韩国盛行音乐”的简称。作者非常锐利地将K-pop概括为韩国在千禧年后的环球化进程中由偶像来充当门面的配乐。同时,作者反对将K-pop大略化为对欧美盛行文化的模拟,或欧美文化帝国主义在韩国的产物。并强调,K-pop的环球盛行,颠倒了当代以来边缘-中央、东方-西方秩序。在不将K-pop与传统民族、族群意义上的“韩国”建立实质性联系的情形下,作者强调K-pop的殽杂性,特殊强调其是“拼贴和戏仿的后当代作品”。在此根本上,作者从学术方法论的角度反思了研究K-pop在学理上的寻衅。作为音乐学家,作者特殊强调包括K-pop在内的盛行音乐是音乐学的“他者”:不是古典音乐,经不住音乐学家的艺术鉴赏;不是传统民俗音乐,无法知足民族音乐学家还有人类学家的猎奇生理。进而,作者提出了“关系音乐学”的观点,强调从多学科角度来处理K-pop的必要性,并先容了从“环球想象”、“民族认同”、“跨国流动”来理解K-pop的三个维度,以及结合野外调查与文本分析的研究策略。
在第一章的根本上,作者将这本书的紧张谈论分为两部分,上部是对K-pop从历史与生产的角度进行基本先容,而下部则是基于作者提出的三个维度,对K-pop进行专题性磋商。在第二章历史部分,作为音乐学家,作者采取永劫段视角,从19世纪末西方音乐进入韩国开始,对韩国盛行音乐版图进行基本先容,强调当代意义上的韩国盛行音乐是从日本殖民期间开始的,既有在日本enka影响下的trot乐,又有通过日本传入的西方爵士乐。他指出在战后韩国独立后去日本化的情形下,殖民期间日本主导下发展起来的盛行音乐家当下的艺人转而为驻韩美军演出,并先容了驻韩美军在将美国盛行文化引入韩国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浸染,进而提出通过美国传入韩国的舞曲与说唱在1980年代朴南正和赵容弼等歌手的奠基以及在1990年代“徐太志与孩子们”的推动下,将舞曲与说唱推向主流,成为未来K-pop的根本。
韩国国民歌手赵容弼
在先容历史的根本上,作者在第三章里对K-pop进行理解剖式的先容。一开始,作者特殊先容了音乐学家亚当·克里姆斯(Adam Krims)在研究说唱音乐时,将音乐内部的构造与社会功能联系起来的不雅观点,即在音乐内部的构造体系里隐蔽着晚期成本主义经济构造。作者进而提出,就稠浊型极强的K-pop而言,其制作模式比音乐风格更加主要,并提出K-pop是一种“多文本征象”,是一种话语、视觉和声音构成的“符号制度”。在这一理论视野下,作者进而从术语(怎么称呼K-pop)、艺名(更加西方还是更加东方)、歌词中的英语(展现K-pop当代性、环球性的手段)、后援字幕(粉丝为翻译做出的大量无偿情绪劳动)、经纪公司定义的体系、偶像明星体系、粉丝对公司的认同、偶像(以H.O.T为例)、练习生制度(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培训与管理模式)、歌曲(以演出为中央的创作、欧美作曲人的大量参与)、形式与曲式、洗脑歌曲式(K-pop歌曲里易于影象的Hook、歌曲戏剧性)、声音(舞蹈节拍、影象点、说唱、Trot里的嘣成分)、视觉性(舞蹈翻跳、招牌舞蹈动作、MV美学)等方面展开了论述。特殊值得强调的是,在先容作曲与声音方面,作者发挥其音乐学家的专长,对一些有代表性的K-pop歌曲进行乐理剖析,但不得不说的是,作为音乐学家,作者对舞蹈、视觉等方面的敏锐把握同样让人惊异(详见后文)。
而不才部的第四到六章,则以“环球想象”、“民族认同”、“跨国流动”为经、以野外调查和文本分析为纬,对K-pop进行个案剖析。在第四章里,作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谈论了韩国盛行文化里呈现出的韶光不对称性。从1990年代末以来,在韩国媒体与国家结合的文化家当发展计策下,韩国如何把韩国盛行文化置于亚洲的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磋商既包含丰富的数据,也包含大量的野外调查和采访先容。在此根本上,作者以日本对韩国盛行文化的接管为例,先容了日本人对韩国盛行文化的态度的转变,即怎么从韩国文化产品找到过去日本的影子(怀旧)转向将韩国盛行文化作为一种潮流文化(共时)。
如果说在这一章里,作者以韶光为维度,先容了日本与韩国之间通过盛行文化的后殖民纠缠,在第五章里,作者则以K-pop闯美为例,先容了K-pop环球化过程中的空间不对称。作者以BoA在2009年发布的《吃定你》(Eat You Up)闯美失落败、Wonder Girls通过《Nobody》一歌闯美成功、摇滚乐队YB进军美国市场的东方化计策以及韩国雷鬼歌手Skull去族群化的策略,来剖析韩国盛行音乐走向环球过程中呈现的不同面貌。在此过程中, 作者结合网上评论(作为一种网络民族志野外调查)、对SM与JYP公司事情职员的采访、对YB成员尹度玹与金镇元的采访为根本进行剖析,展示了韩国盛行音乐在以闯美为中央的计策里,在环球与地方、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徘徊。作者在剖析BoA的《吃定你》MV与歌曲制作都有美国业内人士大量参与但还是失落败的情形时非常锐利地指出,这是美国想象亚洲与亚洲想象美国的双重失落败(即SM公司希望美国音乐人将BoA歌曲的MV按照美国对亚洲人的想象打造,而在此过程中,SM公司又是基于韩国对美国的想象进行生产)。而在剖析《Nobody》的成功时,作者强调了其如何成功售卖了美国人对1980年代的怀旧;在剖析YB与SKULL两个非K-pop案例时,作者强调YB对韩国传统国乐(kugak)的利用及Skull将自己塑造成纯粹牙买加艺人的两种对立策略,进而总结了在东方主义与天下主义之间的韩国盛行音乐家当。
《Nobody》里的复古怀旧情调
如果说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以民族国家为单元进行先容的话(韩国与日本、或韩国与美国),第六章则以自下而上的视野,关注了以韩裔美国人为代表的外国群体在K-pop家当里的浸染,强调了流动的不对称。通过先容1990年代韩裔美国人嘻哈乐队Solid在美国的活动、K-pop家当里的外国偶像(大略提了韩庚与宋茜,而重点谈论了2PM里的中泰混血亚裔美国人成员尼坤)、有黑人血统的韩语说唱歌手(金仁顺与尹美莱),来展示当K-pop代表作为民族国家的韩国走向天下、迎合天下不同地区的不雅观众的过程中,韩国盛行音乐自身的多元性与繁芜性。接下来,作者以2009年终于朴宰范的争端为例,来剖析作为韩裔美国人的他如何成为韩国网民宣泄爱国主义与反美感情的符号;另一方面,作者又以SM早期团体RB里的韩裔美国人朱珉奎为例(基于对他的深度采访),先容K-pop练习生体系如何将一个在美国出生终年夜的韩裔美国人规训为“韩国人”,在此过程中作者也先容了K-pop文化里的新儒家身分,进而谈论了K-pop所折射出的在环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韩国的种族想象。
在读完中译本(并借此机会又重读了英文原版)后,我改变了三年前初读时的想法。我现在认为比较其它既有的K-pop著作(乃至2023年的《剑桥K-pop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pop]),这本书是建立汉语学界与中文读者对K-pop学理上总体性认知的绝佳读本。我一开始担心,这本基于一代团与二代团的研究著作是否在现在已经有所过期。再次读完之后,我认为,正好相反,这本书基于一二代团总结出来的理论思考,在现在社交媒体时期的四、五代团才充分展现出来。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在作者写作的前社交媒体时期,视频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没有像现在随着智好手机盛行变得无孔不入,对付作者将K-pop定位为跨媒介的独特领悟与拼贴、戏仿的后当代作品,还无法很好地理解(特殊是仍旧把K-pop大略化为一种作为盛行音乐的听觉文化),在四、五代团所代表的K-pop的社交媒体时期,我们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作者写作的时期,视频文化还没有本日发达,K-pop视频制作还没有本日那么博识,K-pop视频没有能力像本日那样能通过抖音、B站等多种办法进入天下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作者就跳出了一样平常音乐学家的视野局限,强调了K-pop的视觉性。与此同时, 作者强调K-pop舞蹈招牌动作,认为这是K-pop音乐视频的先决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吴周妍将K-pop舞蹈定义为“手势亮点编舞”(gestural point choreography)的不雅观点。作为舞蹈学者和专业舞者的吴周妍是站在K-pop三到五代团的高度,在K-pop舞蹈已经成熟到充分吸纳嘻哈、爵士的编舞时,提出了这一不雅观点,而富尔在K-pop一二代团还相对大略的编舞里把K-pop作为视频舞蹈(吴周妍将其总结为社交媒体舞蹈)的特点总结了出来。(我查阅了吴周妍的《韩舞:在社交媒体上粉自己》(K-pop Dance: Fandoming Yourself on Social Media)一书,富尔的书没有在该书的参考书目里)。
在这个意义上说,学者能干过后诸葛亮,当K-pop在社交媒体时期达到充分成熟程度(我认为NewJeans音乐视频里对社交媒体的大量元媒体呈现与指涉,是K-pop作为一种视听综合文化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将K-pop的特点理论化,是学者自身的能力的表示。而富尔能在K-pop诸多特点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时,就将其总结出来,无疑是一种更高明的洞见。特殊是,作者的一些洞见都被K-pop此后的发展所证明。比如,在基于二代团期间K-pop闯美还相对有限,更多是亚洲征象之时,作者就从《Nobody》的走红,强调K-pop触发美国人对1980年代的怀旧是其成功的主要缘故原由。而这正好是2020年让防弹少年团在美国登顶的《Dynamite》中利用的策略,这首歌里大量的冷战期间美国盛行文化里复古符号,特殊是对迈克·杰克逊的致敬。对此,电影学者米歇尔·赵(Michelle Cho)在《洛杉矶书评》(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揭橥的“为怀旧的怀旧:美国电视上的防弹少年团”(Nostalgia for Nostalgia: BTS on American TV)一文有充分剖析。
NewJeans的2023歌曲《Super Shy》一开始表现在西方一个城市公园里,一群白人女性在翻跳NewJeans的出道曲《Attention》,这已经是用K-pop表现K-pop
此外,作者在全书开头的第二个花絮里,先容《少女时期》的2009年音乐视频《GEE》将9位成员作为人体模特展示在一时装店的橱窗里时,非常有洞见地总结到:“这个故事是对古老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主题的盛行音乐演绎,将其移植到了晚期消费成本主义的城市和后当代背景里。”(第6页)。皮格马利翁故事记载在罗马帝国早期墨客奥维德的《变形记》里,讲述了传说中塞浦路斯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将自己空想中的女性刻画成雕像供自己欣赏的故事。现任教于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意大利古典学家马尔克·佛尔米萨诺(Marco Formisano)在媒体研究的视野下,指出奥维德皮格马利翁故事是当代媒介文化的一个隐喻。从这个角度来看,皮格马里翁故事更是作为高度发达的媒体文化K-pop的隐喻:K-pop偶像是粉丝心目中理性男性和女性的动态雕塑。不仅如此,2023年男团ONEUS发布的专辑就叫《皮格马利翁》。类似的征象还有很多(比如作者对K-pop家当里种族想象的谈论、K-pop与韩裔美国人关系),这里不一一先容。
ONEUS《皮格马利翁》专辑
这充分解释富尔对K-pop征象把握的独特深度。这本书不但没有过期,相反,这本书谈论的诸多征象到了三代团往后,才更加明显地展现出来。这本书有历史概括、家当剖析、K-pop闯日、闯美先容以及K-pop里的外国偶像,并把K-pop放到韩国盛行文化与其它音乐文体的视野下谈论。无论是对付想要入门K-pop的普通读者还是希望建立对K-pop学理性认识的K-pop粉丝而言,都是一本极佳读物。当然,该书仍旧存在对很多问题没有深入谈论的问题,但这种在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缺失落或许也会成为获取更广阔读者群的一个主要条件。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的译笔也十分出色,比如第4章里的第二个小标题“globalizing Korea, promoting culture”,译者将其译为“韩国环球化、文化宣天下”,十分精当真切,整体阅读体验比英文版更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图书馆里收藏的五本K-pop著作,个中包括富尔的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图书馆里收藏的五本K-pop著作封面
因此,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这是一本迟到的书(第一个意义上)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展现的方法论多元性(野外调查、音乐风格剖析、媒体话语剖析、图像解读)也可以看作是K-pop本身的稠浊型(不同音乐风格、不同舞蹈风格、音乐舞蹈时装等融为一体)在学术上表现的一种“元K-pop”式的反响。因此,我更乐意将这本书定义为在K-pop驱动下展示的一种跨学科可能。目前,在西方学界,K-pop研究早已超越了东亚研究,而成为音乐学、舞蹈学、电影学、媒体研究、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史、人文地理学、宗传授教化等等学科都会参与谈论的一个话题。只管“跨学科”作为一种空想一贯为学界以各种办法探索,以什么样的办法能实现不同学科间学者的有机对话、避免鸡同鸭讲,一贯是一个寻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西方学术界(尤其在美国),环绕K-pop的议题,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跨学科对话办法,大家用自己的学科来诚挚磋商K-pop方方面面,而不是像传统区域研究会议(比如东亚研究)下不同小组里自说自话。传统的跨学科考试测验每每是把摇滚歌手、嘻哈歌手、蓝调歌手、民谣歌手聚拢起来,让大家机器地互换不同音乐风格;或者把作曲人、编舞师、时装设计师聚拢起来,不太舒畅地谈论不同潮流艺术领域的创作,而不同学科的学者环绕K-pop议题的谈论,则更像K-pop把不同音乐风格稠浊起来、不同艺术领域聚拢起来,创造出一种有自己风格的演出形式。而这一特点在富尔这本书的跨学科性中已经有所表示。
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在去年11月份,我线上为肯塔基大学研究东亚演出文化的罗靓老师的东亚盛行文化研讨课做了客座演讲,先容对K-pop里的古典接管的研究。这本来只是针对该校本科生的一门讲座,但由于东亚研究在肯塔基大学从属于“当代与古典措辞、文学与文化系”,该系除了东亚研究,还有古典研究、德语文学、意大利文学等专业,结果竟然有两位日本研究和两位古典学的学者前来,还有一位德国文学的老师由于韶光冲突无法参加但希望能看之后录屏。大家对与K-pop干系话题的兴趣(尤其是通过K-pop里的古典接管来和古典学结合)让我十分惊异,之后私下听罗老师说来听的老师们对我的报告给出了同等好评,也给了我连续从事干系研究的动力。
2024年1月,女团G(I)-DLE《Super Lady》里的古典接管
当然,我在说K-pop作为一种跨学科互助隐喻时,并不是说只有靠K-pop才能实现真正跨学科互助。更主要的是,K-pop作为一种文化综合体,怎么给当代人文社科学者以启迪,去重新思考19世纪工业革命下建立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组织形式是不是已经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社交媒体时期充分显示出了问题(用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话语,现在的生产关系已经掉队于生产力的哀求)?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卢西安(又译琉善)就充分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写《论舞蹈》(De Saltatione)便是反思当罗马剧院里的哑剧盛行舞者成为公众年夜众关注的焦点时学者作甚。而根据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家、古典学家莎拉·莫罗森(Sara Monoson)在《柏拉图的民主纠缠:雅典政治与哲学实践》(Plato's Democratic Entanglements: Athenian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一书里的研究,柏拉图也思考过类似问题。通过对《空想国》(Politeia)的细读,莫罗森展示柏拉图在思考哲学家怎么通过接管剧院里的演出文化特点,让从事哲学谈论与民众剧院不雅观看盛行演出一样有趣(类似本日的父母会思考为什么小孩不能用追星的激情亲切去学习书本知识)。这种知识分子与盛行文化交融的古代模式也不断会成为当代古典学家反思当代教诲问题的一个视角,比如法国已经去世的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 1922-2010)则很早就指出古代哲学和中世纪以来的哲学是两回事,古代哲学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做,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学院里(阿多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也有法国高档教诲体系的独特性,特殊是阿多长期任教于面向"大众年夜众开坛讲道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而最近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关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智术师的研讨会,将他们定义为“公共哲学家”,想必也有这样的反思。古代模式给当今学者的一个潜在启迪是,不同文化形式之间是可以互动、互鉴的。
在2021年5月份,带着上述思考,我有幸通过ZOOM视频与哈佛大学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学家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就上述问题进行请教, 由于她是古典学演习出身。她对我的思考表示附和,并且在结束时说:“我们要向盛行文化学习的地方有很多。”(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pop culture)在之后的2023年初,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比较文学学者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出版了《文化,我们的故事:从岩画到K-pop》(Culture: the Story of Us, from Cave Art to K-pop)一书。在书末端,普克纳就像卢西安思考罗马帝国期间知识分子能从哑剧舞者的成功那里学到什么一样,认为当代人文学者能从K-pop的文化稠浊性那得到启示,并强调如果人文学要生存,学者要借鉴各种手段。也便是说,普克纳认为,人文学日渐衰落的缘故原由的任务不在"大众沉迷盛行文化,而在人文学者没有像盛行文化(比如K-pop)那样与时俱进、不断吸纳新的元素和技能、不断改造表达形式,而在自恋的抱残守缺。而在2023年4月尾,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古典学会议上,报告了与罗马哑剧干系的题目。我在报告末了讲述了公元3世纪希腊作家菲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在《智者传》(Vita Sophistarum)里提到的一个趣闻:公元2世纪演说家哈德良(113-193,并非罗马天子哈德良)来到罗马,当这一传到罗马剧院时,正在看哑剧的民众与政治家抛弃了他们的哑剧明星,跑到一公里以外去听哈德良演讲。我在哈佛大学开会时,适逢英国著名网红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芝加哥大学做公共演讲,磋商古典学还有没有未来。在报告结束时,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比尔德演讲的时候有一个K-pop演唱会在芝加哥举行,比尔德是否有能力让大家放弃他们的爱豆,跑到芝大去听她的演讲?这个提问引发了大家的沉思,或容许能解释这个问题引起了人文学者们在社交媒体时期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与忧虑。
比尔德2019年1月在圣地亚哥美国古典学年会上的特殊演讲,盛况空前,大量粉丝上去要署名与合影
比尔德2019年1月在圣地亚哥美国古典学年会上的特殊演讲,盛况空前。
因此,我更乐意将富尔这本书呈现的高度跨学科性与多方法性看作K-pop在学术领域展示一种跨学科方法的一种隐喻。此外,富尔也在书一开始先容了自己的德韩双重背景,自己的母亲是朴正熙期间被派送到德国打工的护士,作为为韩国赚取外汇操持的一部分。按照一开始提到的金久用的《从工厂女工到韩流女星》的政治经济学阐明,朴正熙向外输出的韩国劳工在经济意义上是K-pop爱豆的“原型”。富尔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韩国通过对外输出劳工(从输出经济劳工到输出文化劳工)的一种跨媒介(trans-media)呈现,如果我们将学术写作揭橥看作一种媒介形式的话。也便是说,写这本书是作者德韩跨文化、族群背景的一种自我反思。这又涉及到西方K-pop研究的其余一个维度,即种族和族群维度,由亚裔(特殊韩裔)学者推动。在我在2021年做高玉蘋的采访时,作为著名种族社会学家与亚裔美国研究专家,她特殊强调了亚裔在美国的长期边缘地位是如何让她认为K-pop是一个主要征象。2022年5月,斯坦福大学韩国中央举办了一个关于K-pop的会议。在会上,斯坦福大学艺术史学者马西·权(Marci Kwon)略带夸年夜地说,她所认识的所有亚裔女教授都在疫情期间入坑K-pop,并结合亚裔在美国的边缘地位,强调当K-pop作为一种来自亚洲的文化,是如何通过击败诸多主流美国歌手让亚裔找到自傲。更早的时候,最早将K-pop征象先容给美国古典学界的韩国古典学生蔡瑛仁(Yung In Chae,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剑桥大学硕士)则在先容防弹少年团《狄奥尼索斯》(Dionysus)里的古典接管一文中,指出K-pop闯美的努力不禁让她遐想到自己作为一名亚洲学生,在白人主导的英美古典学领域里努力让亚洲人赢得认可的经历。就我个人而言,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韩国盛行文化的影响(大概正是青少年没有受过任何K-pop影响,从一开始就可以以学术的办法面对K-pop,而没有粉丝思维包袱),当2021年初第一次读富尔的书时,看到他谈论K-pop寻衅了传统东方-西方文化等级秩序和流动时,也不禁像蔡瑛仁一样去思考自己在西方学界的经历。
斯坦福大学2022年终于K-pop的线下会议,参会者包括李秀满与EXO成员金俊勉(Suho)
就海内而言,从K-pop研究的角度,这本书的引进的确是迟到了,只管书本身没有过期。但从更大的角度,即将这本书看作K-pop影响下的一种跨学科范式,大概正当实在。在该书的序言解释里,海内著名学者刘东提出了他对当代韩国感兴趣的23个问题(个中一个问题和韩流有关),并引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祸与内政之关系”的谈论,暗示韩国履历给当代中国的潜在启示。这一视野无疑与普克纳站在世界文化史的高度看K-pop非常相似,如果说普克纳的《文化》一书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层面及时将K-pop纳入美国的知识体系下,刘东的这一论断则暗示了将K-pop纳入中国正在发展的区域研究视野的一部分的可能。当海内提出建立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理念之时,韩国如何通过重新整合欧美既有的不同音乐流派和各自独立的艺术领域,发展出一种基于欧美盛行文化但又独树一帜进而“文化宣天下”的盛行文化体系,这无疑值得处于社交媒体时期、面对深受K-pop影响的00后学生的中国学者们去思考和反思。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丁晨楠老师对本文写作供应了主要帮助,在此特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