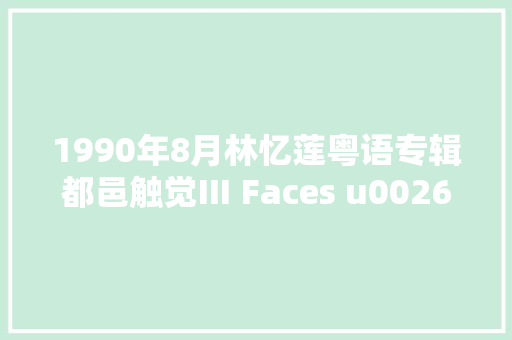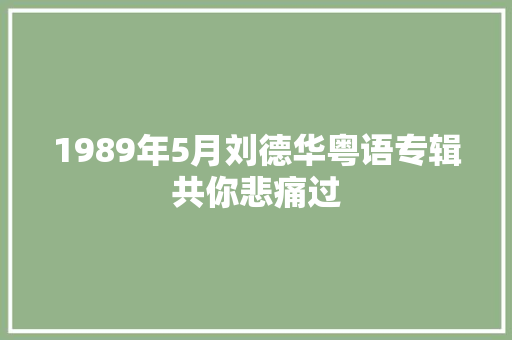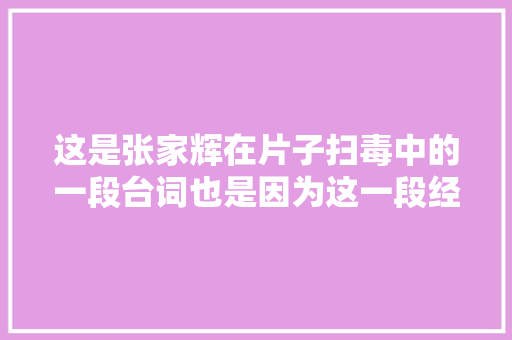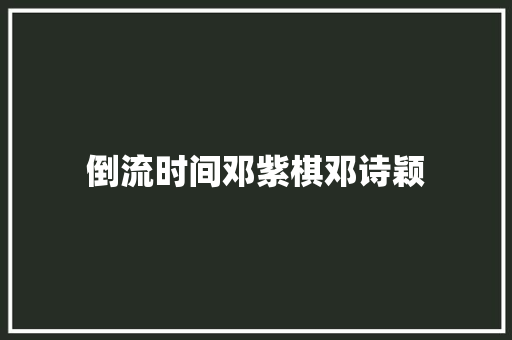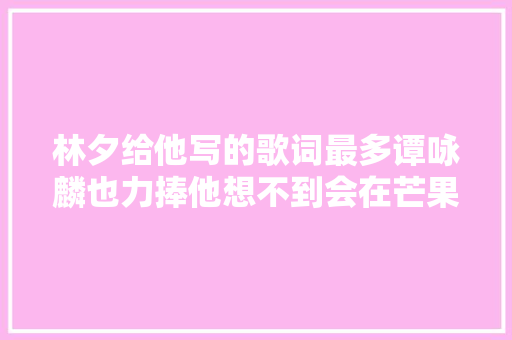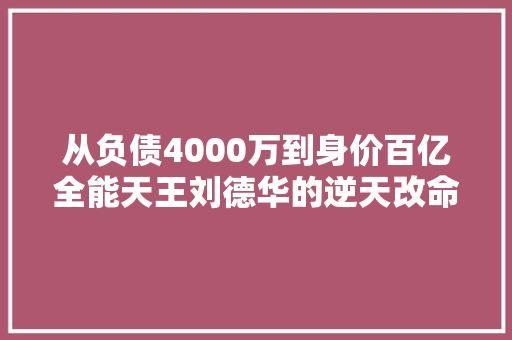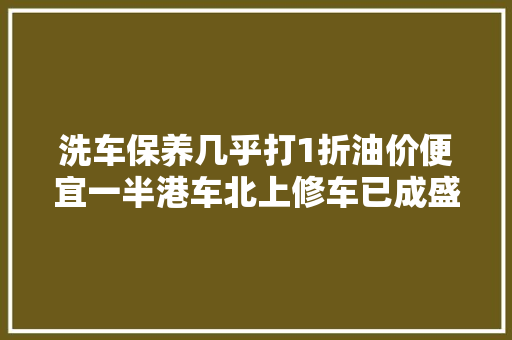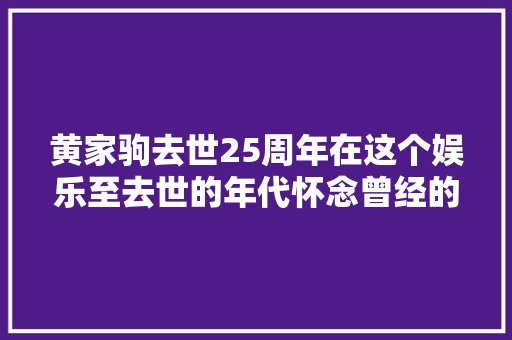说到喷鼻香港,许多人会想到狮子山。1973年,讲述喷鼻香港经济腾飞时草根阶层拼搏不息的电视剧《狮子山下》开播,而黄霑作词、罗文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广为传唱,“狮子山精神”成为港人奋斗精神的象征。
说到详细的狮子山,则端坐于喷鼻香港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大围之间,“狮子”头面向九龙西边,狮身连尾巴完全地伏在山上。

狮子山见证了喷鼻香港由一个小渔村落到国际化大都邑的艰辛进程,而以此山命名的“狮子山精神”也刻印在许多喷鼻香港人的心里,表示在万万千万的喷鼻香港人身上。
15年前的2002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在喷鼻香港特区政府的欢迎晚宴上,还特殊念了一遍《狮子山下》的歌词,并表示,“我看了这个歌词往后,很受冲动。我相信在座的参加创业的这些老前辈,更有这种感想熏染。由于歌词的每句话,都充满着真实的感情,而这种真实的感情,会永久发光。”
当年站在狮子山顶可以看到喷鼻香港的两面
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南天海角,狮子山前,我校耸立辉煌”,坐在办公室的喷鼻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只要抬开始,便能透过窗户看见远处的狮子山。
周伟立在喷鼻香港浸会大学
很多个周六,他都会去爬狮子山。而他与这座山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1960年代。彼时,他恰好住在狮子山下。“那时候家里没有钱买玩具,就跑到山上去玩,山上有条小溪,我们从里面捞出蝌蚪带回家,看它逐步终年夜变成田鸡。”
年幼的周伟立喜好站在狮子山顶俯瞰着他出生和发展的喷鼻香港,“往南边看是喷鼻香港岛和九龙,往北便是沙田、大埔、粉岭,那时新界沙田不是本日高楼林立的样子,没有屋子,都是农田,其余一边便是市区有很多屋子。”在他看来,狮子山是市区和郊区的分边界,站在狮子山顶的自己可以同时看到喷鼻香港的两面。
同那个时期许许多多住在狮子山下的喷鼻香港人一样,周伟立一家住在徙置区,这是喷鼻香港政府从前所建的公屋。10平米旁边的房间容纳着这一家8口人的生活起居,卫生间则为多户人家共用。“60年代的喷鼻香港还是比较穷的,那个年代基本都是这样的”。周伟立的爸爸当时在工厂事情,妈妈把一些叫做“家庭工业”的活儿接回家做。“比如有人做塑胶花,很多人说李嘉诚由于这个发财。我们做的比这个更须要技能一些,我家有两台缝纫机,我妈接单在家里做牛仔裤。”
周伟立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帮忙赢利,“我做作业比较快,然后就帮妈妈做,她教我一些大略的,比如把口袋缝起来,在裤边走一行直的线,现在给我一台缝纫机我都会用”。正由于这样的发展经历,周伟立认为《狮子山下》这部电视剧非常随意马虎引起喷鼻香港人的共鸣,他见告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爸妈常常说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做投契取巧和损人利己的事情。我认为‘狮子山精神’便是在不利的环境下,不是躺在那里说我没有办法,而是咬紧牙关,找办法开一片新天地。”
1980年,周伟立考入喷鼻香港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1992年回喷鼻香港大学任教,如今担当喷鼻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在从事教诲的25年里,面对自己的学生,他认为不须要刻意贯注灌注“狮子山精神”:“把自己做好,存心干事,学生会看得见”。
去年,在一次以歌曲为主题的讲座现场,周伟立唱起了年轻时学会的《我的祖国》,视频一度广为传播。谈及此,周伟立表示,当年“喷鼻香港很多学校都有人在唱,我们对内地理解比较少,希望知道多一点。大学生都在问自己,内地很多地方比较掉队,自己有什么可以做的。和内地亲戚的亲情也一贯坚持着。”这也道出了当时喷鼻香港的大学生态。
“父母总教诲我们肯干才能有饭吃”
今年70岁的何伯是一名喷鼻香港小巴司机,和妻子住在新界葵青区大窝口的一间公租屋里。这是范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屋子,铁窗铁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伯夫妇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能够拥有这座寓所,何伯感慨“好似中了六合彩”。
之以是这么说,是由于何伯夫妇也住过徙置区。“长长的条廊被分隔成一个个小房子,全部没有窗户,厨房和公厕在屋子前,常常两三天才来一次水,我爸爸先沐浴,洗过的水我再洗”,何伯说。如今,每月只需向政府支付1000多港币,何伯夫妇便能安居在这间公租屋里。而附近相同面积的私屋(商品房),租金将近8000港币。
何伯何太
为了谋生,何伯从前做过很多事情,如工厂的机器维修工、坚持社会治安的辅警、医院的后勤职员等等。2008年从地政总署寮屋牵制组退休后,他应聘成为一名小巴司机。每天中午12点在家吃完午饭,何伯开工,直到凌晨12点放工回家。“每月根本人为很低,人为按照每天开的班次打算,为了多开几班,他常常搪塞着吃顿下午饭”,何太见告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
但是何伯对事情的喜好,令何太哭笑不得。“我生了孩子后身体不好,再没有出去事情了,有时候想去看看他,一上车他就把我赶下来,说不要打扰他事情,不要占我搭客的座位”。
“年轻时,父母总教诲我们肯干才能有饭吃,我现在安居乐业,以为很幸福”。何伯认为,“狮子山精神”不但像李嘉诚一样的成功人士有,它的主体是喷鼻香港的普通大众。
同何伯的不雅观点一样,居住在大围田心村落的徐太也认为“狮子山精神”表示在所有喷鼻香港市民身上。上个世纪90年代,徐太一度曾动过移民的动机,却终于没有走。“我和丈夫都在喷鼻香港出生终年夜,从小时候一家6口挤在公租屋里,到凭借文凭找到事情,再到成家后和丈夫一起买房,百口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如果移民,那即是放弃这统统重新开始”。更主要的是,徐太看到,回归后的喷鼻香港仍旧是一个推崇努力打拼、每个人靠自己本事用饭的城市,这点和回归前并没有不同。
而今,年近六旬的徐太决定回内地养老。“前几年我在广东番禺买了一套屋子,但那里只是一个落脚点,我想去内地的很多地方旅游,比如四川的九寨沟、杭州的西湖、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安、重庆、厦门等等……可是,唯一的问题便是我普通话还不太好”,说着徐太不好意思地笑了。
年轻的人与不老的“狮子山”
喷鼻香港的年青一代若何理解“狮子山精神”?
“小时候爸妈跟我讲过‘狮子山精神’,当时我很迷惑,我住在港岛,狮子山在九龙和新界,跟我没有关系。然后爸妈就特地带我去那边看,跟我讲,以前狮子山住的是喷鼻香港基层的人们,各方面环境都不好,但是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生于80年代末的喷鼻香港青年黄芷渊记得,中学历史课上,老师在讲到喷鼻香港历史时,教大家唱《狮子山下》,“老师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上一辈、上上一辈是怎么打拼的,喷鼻香港本日的造诣是怎么来的。”
狮子山
黄芷渊还记得2003年,也便是“非典”传播的年份。那段韶光,喷鼻香港的电视台里常常会放《狮子山下》这首歌。“在现实中看到全体社会面对着同一个困难,全体社会还是很联络的,那个时候才真正理解了歌词的内涵,创造歌词特殊好,特殊励志。”
黄芷渊之前一贯认为,他们这一代喷鼻香港年轻人生于物质富余的年代,可能无法体会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但在一场SARS中,黄芷渊看到了喷鼻香港人守望相助的代价,看到了这个文明社会的精良质素。“狮子山下的喷鼻香港精神仍常挂在我们嘴边。而我所说的挂在嘴边,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喷鼻香港人,还包括在喷鼻香港生活的少数族裔新一代,乃至在喷鼻香港发展的内地新移民。”黄芷渊对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说道。
“90后”喷鼻香港学生黄凯怡从喷鼻香港高校毕业后,选择来到北京大学攻读中文专业的硕士。一个女孩,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读书,刚开始家人不放心,反对她的决定。但她还是屈服了自己的决定,由于专业与大学所读并不相同,她刚开始的时候跟不上学业进度。但她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将这段求学生涯变成了自己最宝贵的经历。下一步,他会到爱丁堡大学连续攻读,在文学领域的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
在黄凯怡看来,“狮子山精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是大家共知的一个事情,不用特地去强调,它是喷鼻香港人的一种特质和处世办法。”
校正 |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