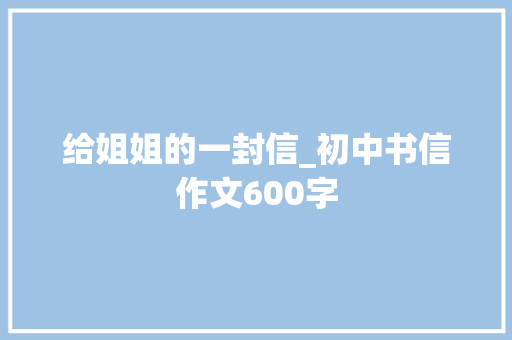妈妈正在沐浴,只听门外大叫“妈妈!
妈妈!
” 还没等回应,浴室门“嘭”地一声撞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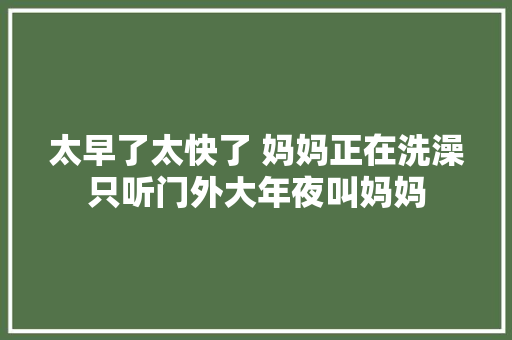
还能怎么办,妈妈整顿好自己,匆忙前去查看。只见桌面上缭乱地散落着大大小小十余根羽毛。
妈妈捡起最大最蓝的那根,看形状该当是根俊秀的尾羽。仔细端详下,羽毛根部还有血迹。
可怜的凤尾!
妈妈大怒:徐笑吟!
你为什么拔凤尾的羽毛?!
我扯你头发你痛不痛?!
暖暖被怒火震慑,愣住,眼眶泛红。越来越红。嘴唇向下一撇一撇。
半晌,小声蠕嗫道:妈妈,我欠妥心的……
妈妈处在暴怒中,为凤尾的疼痛,也为暖暖的残酷:欠妥心?如果是一两根小小的羽毛那叫欠妥心!
这么多羽毛!
不用力能拔下来吗?你得使了多大的劲才扯下来这么多? 下次你再拔凤尾的毛,拔几根我就拔你几根头发!
你这叫虐待!
凤尾会讨厌你的!
暖暖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但她没有回嘴,也没有哇哇大哭,像一座悄悄的喷泉。
两三秒后,暖暖溘然穿上拖鞋,踏踏踏地向房间走去。中途还用袖子揩了一把脸。
门“嘭”的一声关上。紧接着“咔咔”两声,门被反锁了。
妈妈不解气,赶到房门外:徐笑吟你又锁门!
你给我出来,跟我讲清楚!
没有声音。
妈妈深吸一口气,默念:
温顺而武断。
温顺而武断。
温顺而武断。
“暖暖,对不起。妈妈刚才冲你嚷,是不对的。我跟你道歉。你什么时候想出来了,我们再谈。”
没有声音。
过了好半天,该沐浴了。
妈妈:暖暖开门,要沐浴了。
过了几秒钟,妈妈听见窸窸窣窣下床的声音。咔。咔。门开了。暖暖没有看妈妈,径直转身爬到了床上。
床上像小山一样,七扭八歪地堆了一摞书。暖暖一摩挲脸,把散落的头发撩到耳边,拾起正在看的书读了起来。
仿佛没我这个人。
妈妈讪讪地搭讪:看书呢?
没有回答。
妈妈:嗯……我知道,我的暖暖是最善良的,暖暖最爱凤尾。暖暖绝对不会无缘无端地拔凤尾的羽毛。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状况,是不是?你能跟我讲讲发生了什么吗?
暖暖盯着书,眼眶又泛红了。小嘴撅了起来,十二万分委曲。
妈妈蹭过去几分,摸摸暖暖的头,顺势微微用力把书抽走。见暖暖没有抵抗,一把把暖暖揽到怀里:“哎呀呀,我的心肝宝受委曲了。妈妈坏对不对?妈妈吼我们,也不问前因后果。暖暖拔了凤尾的羽毛已经很腼腆了,妈妈还吼我们,暖暖太伤心了。”
暖暖再次化身成一座委曲的喷泉。
六月飞雪,梨花带雨。如泣如诉,可怜可叹。
哭了好一下子才平复下来,讲述了故事的原委:
暖暖放凤尾到客厅透气。等她想把凤尾放回笼子时,凤尾不愿意,噗噗噗飞到地板上。阳台门敞着,暖暖担心凤尾飞走,就狠命逮她,把羽毛拽下来好多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暖暖学会了悄悄地哭泣。她更幼小的时候,可是只会嚎啕大哭的啊!
人幼小的时候,哭起来都是唯恐不足大声,唯恐没人把稳;终年夜了恰好相反,怕人讯问,咽泪装欢。 暖暖终年夜了,终年夜得有点太快了,也太早了。是什么让你终年夜得这么快的呢?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哦,还有那“咔咔”的反锁声。妈妈原以为啊,还得等个五六年才会响起。没想到,暖暖才四五岁光景,就把妈妈反锁在门外了。
好早啊!
好快啊!
太早了。太快了。
我们家书架上,有一本龙应台的《目送》。里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逐步地、逐步地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便是今生现代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逝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见告你:不必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