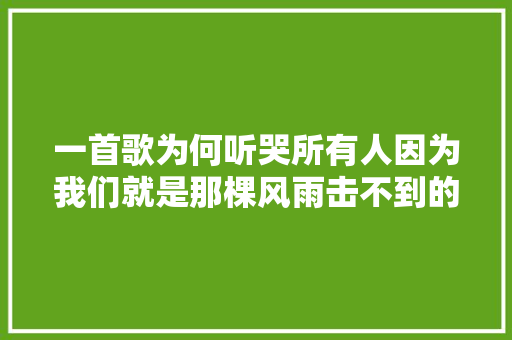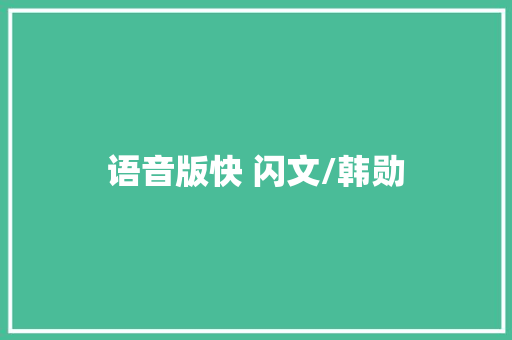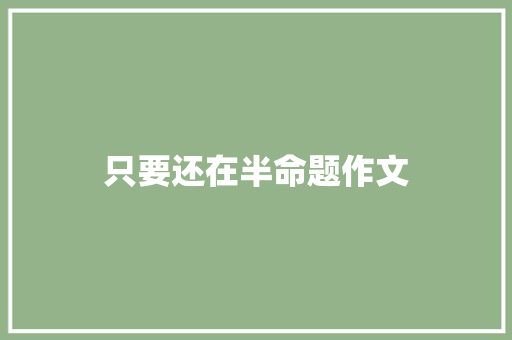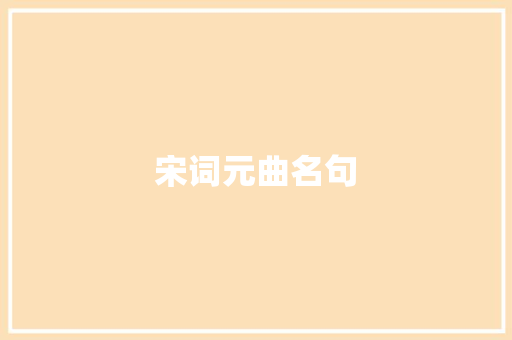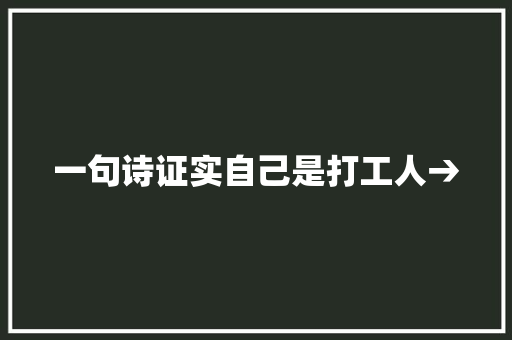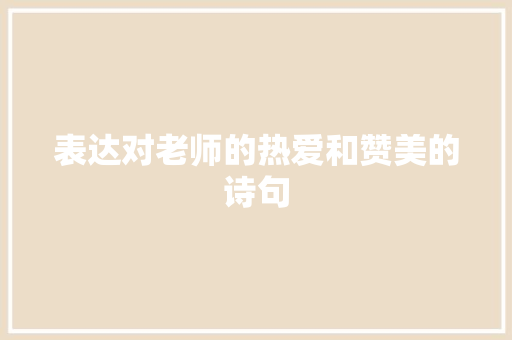隋唐洛阳城遗址平面实测图。资料图片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内景。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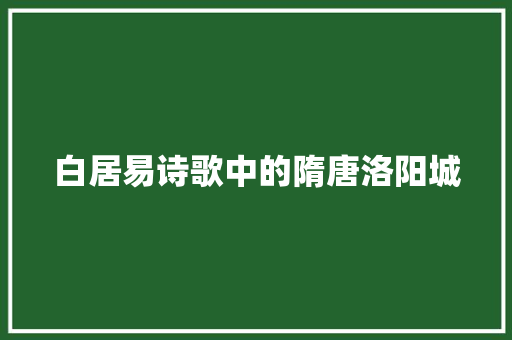
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唐代瓷器与石器。资料图片
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唐代瓷器与石器。资料图片
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唐代瓷器与石器。资料图片
演讲人:霍宏伟 演讲地点:河南洛阳博物馆 演讲韶光:2019年4月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是唐代墨客白居易年少时写的一首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相传此诗与一段逸闻有关。白居易年轻时进京赶考,带着自己的诗歌来拜会墨客顾况。顾况看着白居易的大名,对白公说:“米价方贵,在长安城住着不随意马虎啊。”等到读完第一篇中的“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不禁惊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幽闲鼓吹》)白氏由此声名大振,留下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典故。据学者考证,这只是一个关于少年白居易的美好传说。不过,老年白居易的确曾经在一座环境宜人的城市里定居长达18年之久,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
这座城市的诸多美景化为绝妙的诗行,积淀于白氏的卷帙之中。“唯此鄙人叟,顽慵恋洛阳。”(《餍饫闲坐》)白公闲适恬淡,终老生平,末了长眠于名都南郊,这座城便是隋唐洛阳城。
此城虽然现在或为广袤的野外所覆盖,或被当代城市的高楼大厦所叠压,却依然如故,以顽强的生命力,与岁月的磨蚀与人为的毁坏相反抗,在沉寂千年之后,经由考古勘查与发掘,逐渐显露出隋唐韵致,与白居易的诗行交相照映,熠熠生辉。
白居易诗歌中的洛阳城
隋唐洛阳城肇端于隋代东京城。隋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炀帝下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十个月后东京城落成。大业五年改名东都。东都城,一座平地起建的都城,仿佛一张空缺宣纸可以描述出最俏丽的国画那样,历经隋、唐两代的苦心经营,构筑了一个弘大、繁芜的城市空间体系,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即城、苑、窟、墓四个组成部分。隋唐东都的前三个部分城、苑、窟均属于阳世,末了一部分墓为阴间。阳世与阴间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东都城完全的城市空间体系。
其一为城,包括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及外郭城等由城垣环绕的城市范围。白居易在洛阳城中生活,紧张活动范围是属于外郭城的洛南里坊区,并写下了不少与洛阳城有关的佳句:
闲绕洛阳城,无人知姓名。(《城东闲行因题尉迟司业水阁》)
丰年寒食节,美景洛阳城。(《六年寒食洛下宴游》)
三年遇寒食,尽在洛阳城。(《洛桥寒食日作十韵》)
今年共君听,同在洛阳城。(《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
老除吴郡守,春别洛阳城。(《除苏州刺史别洛城东花》)
黄绮更归何处去,洛阳城内有商山。(《题岐王旧山池石壁》)
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闲吟》)
其二为苑,紧张指隋唐两代的离宫别苑。离宫分为苑内型、城郊型及县区型等三种类型,别苑即东都城西面的西苑,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唐代有所改建。白居易长期在洛水以南的里坊区生活,与西苑隔河相望,时常眺望苑中美景,也会有诗兴大发之时:
上苑风烟好,中桥道路平。(《洛桥寒食日作十韵》)
笙歌辞洛苑,风雪蔽梁园。(《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
东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东风》)
西来为看秦山雪,东去缘寻洛苑春。(《京路》)
三为窟,是指以龙门石窟为中央的龙门地区。龙门石窟位于隋唐洛阳城以南约十公里的伊水两岸山崖上,是东都城主要的佛教文化区。这一地区面积广大,各种文化遗存丰富,根据其性子的不同,分为石窟区、寺院区等。白居易晚年喜好佛学,龙门一带的石窟及寺院也是他常常拜会之地。卒后葬于龙门东山,今人在其墓地建有白园。白公在龙门留下了诸多诗作,记录下他的行踪:
水碧玉磷磷,龙门秋胜春。(《同崔十八宿龙门》)
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喷鼻香山下卜居》)
老住喷鼻香山初到夜,秋逢白月正圆时。(《初入喷鼻香山院对月》)
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
经年不到龙门寺,今夜何人知我情。(《五年秋病后独宿喷鼻香山寺三绝句》)
四为墓,是指隋唐洛阳城垣之外隋唐期间的大量墓地,多位于城郊及县区。现已发掘上千座隋唐墓葬,以唐墓居多。洛阳城外的墓区,以城外北面的邙山最为著名,因历代坟茔数量浩瀚,以至于“无卧牛之地”。白居易写有多首与北邙山有关的诗歌,反响出生离去世别之情,以及对付世间名利的淡然心态:
形骸随众人,敛葬北邙山。(《哭孔戡》)
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浩歌行》)
东风草绿北邙山,此地年年死活别。(《挽歌词》)
北邙未省留闲地,东海何曾有定波。(《放言五首并序》)
羲和趁日沉西海,鬼伯驱人葬北邙。(《仲春五日花下作》)
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清嫡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羽士》)
诗作中的洛阳城密码
在由一道道黄土夯筑、外加青砖包砌的城墙分割包围下,面积约为47平方公里的城垣以内的隋唐洛阳城市空间划分出不同区域。东都城仍旧沿袭了北魏洛阳城、隋大兴城以来的“三城制”:宫城、皇城、外郭城,只不过宫城、皇城不是位于全城中心,而是偏居西北。有人说是因“下京城一等”,另有人说是西北方向代表乾卦,贵为乾位,或称乾冈。
宫城不仅是隋唐帝国某些期间的政治中枢,而且是东都城内的核心空间。由于是天子办公、起居之所,故防守严密,周围有一些小城拱卫。其南临皇城,北倚玄武、曜仪、圆璧三城,东接含嘉仓城与东城,西连禁苑。宫城内的建筑布局,遵照中国古代传统,前朝后寝,主体建筑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分布。考古发掘出的主要遗址有宫城正南门应天门、宫城主体建筑明堂与天国等遗址。白居易《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赐教兼呈梦得》中的“月牙上宫城”一句,颇具画面感:
七月中气后,金与火交争。一闻白雪唱,暑退清风生。碧树未摇落,寒蝉始悲鸣。夜凉枕簟滑,秋燥衣巾轻。疏受老慵出,刘桢疾未平。何人伴公醉,月牙上宫城。
唐太和六年(832年)八月旬日,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亲临俗称“五凤楼”的应天门城楼,即兴创作了一首《五凤楼晚望》。作者登高望远,见景生情,抒发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想熏染:
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目前。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隋唐期间中心衙署及附属机构的办公重地。隋代洛阳皇城与东城设置有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官署,唐代则改为六省、九寺、十四卫府及十率府等,武周期间增置“左祖右社”等礼制建筑。已发掘出皇城南面右掖门遗址、唐右威卫府门址、泻口碾坊故址等。白居易有一首以洛阳皇城为题的诗作《早入皇城赠王留守仆射》,彷佛流露出一丝凄苦与伤感:“津桥残月晓沈沈,风露凄清禁署深。城柳宫槐谩摇落,悲愁不到朱紫心。”
在皇城西南,还有一处主要的宫殿区上阳宫,武则天就病逝于上阳宫内的仙居殿。作为盛唐前期权力中央的上阳宫,在盛唐后期及中唐却成为流放嫔妃佳丽的宫怨之所。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政治讽喻诗《上阳白发人》,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一位终生禁锢于上阳宫的宫女的悲惨命运。自注云:“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首诗的第一部分记述了老宫女的出生来历及上阳宫的环境: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第二部分描写了老宫女对往事的回顾及幽居深宫的煎熬之苦: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生平遂向空房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第三部分描述这位年迈的老宫女的生活现状: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苗条。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当年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隋唐两代,东都郭城城门数量相同,皆为八座,惟城门名称略有改动。唐代城门,南面有定鼎、长夏、厚载三门,东面有建春、永通、上东三门,北面有安喜、徽安两门,经由考古发掘的有定鼎、长夏、建春、永通等门址。郭城正门定鼎门,隋代称建国门,门址由三门道、长方形墩台、两道隔墙、东西飞廊、东西两阙及马道等组成,分为四期。以盛唐前期门址为例,每个门道东西宽5.8米、南北进深21.04米。现已在该门址上建立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因该城门为外郭城南面正门,成为唐代主要的地标性建筑,而在白居易《秋日与张来宾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中,描写了墨客以定鼎门为洛阳城的坐标点,向南秋游十八里的一段轶事:
秋日高高秋光清,秋风袅袅秋虫鸣。嵩峰余霞锦绮卷,伊水细浪鳞甲生。洛阳闲客知无数,少出游山多在城。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门十八里,庄店逦迤桥道平。不寒不热好时节,鞍马稳快衣衫轻。
由于白居易的宅第位于全城的东南隅,地近外郭城东面两门永通门与建春门,属于墨客的活动范围,以是这两座城门自然被墨客引入诗中:
水南冠盖地,城东桃李园。雪消洛阳堰,春入永通门。(《洛阳春赠刘李二来宾》)
闲游何必多徒侣,相劝时时举一杯。博望苑中无职役,建春门外足池台。(《与皇甫庶子同游城东》)
隋唐洛阳城的外郭城里坊区,建筑性子互异,大致包括衙署、寺不雅观祠庙、市廛作坊、住宅、园池、馆驿、渠堰堤桥等七种类型。衙署分为中心与地方两级,隋代数量极少,大多为唐代所置,分布于洛南里坊区的衙署数量大于洛北区,而在洛南,以定鼎门大街两侧里坊内分布的衙署数量最多。河南府衙门位于洛南的宣范坊,白居易在此当过一段韶光的河南府尹。归隐田园之后,他也曾多次故地重游,写有关于河南府衙的诗歌,如“每入河南府,依然似到家。杯尝七尹酒,树看十年花”(《自罢河南已换七尹》)。
寺不雅观祠庙包括佛寺、道不雅观、胡寺祆祠、寺院等,里坊区内约有唐代佛寺二十座,道不雅观十二座,波斯胡寺一座,祆祠三座,寺院四座。从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在洛阳城内寺院中,他登临次数最多的是天宫寺中的楼阁,并谈到了自己上阁的缘故原由,“天宫高阁上何频,每上令人线人新”:
洛城秋霁后,梵阁暮立地。(《天宫阁秋晴晚望》)
高上烟中阁,平看雪后山。(《登天宫阁》)
前日晚登缘看雪,目前晴望为迎春。(《天宫阁早春》)
天宫阁上醉萧辰,丝管闲听酒慢巡。(《早秋登天宫寺阁赠诸客》)
东都里坊区内的住宅数量最多,霸占了里坊的绝大部分空间。依其主人地位、身份的不同,又分为王侯将相府第、仕宦宅第及普通民居等。王侯将相府第占地面积较大,建筑奢华,如武则天宠臣张易之与宗楚客的府第豪华至极,两处宅第分别位于修行坊、宣风坊内。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为壮丽,计用钱数百万。“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为梁,沉喷鼻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喷鼻香气发达,磨文石为阶砌及地。”(《朝野佥载》)这些达官显贵们在洛阳里坊区内营建的豪宅,也自然进入了白居易不雅观察的视野范围之内:
水木谁家宅,门高占地宽。悬鱼挂青甃,行马护朱栏。春榭笼烟暖,秋庭锁月寒。松胶黏琥珀,筠粉扑琅玕。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生未曾到,唯展宅图看。(《题洛中第宅》)
最具代表性的仕宦宅第,当属白居易晚年居洛的履道坊第宅,其基本特点是住宅与园林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住宅的基本布局在其《池上篇并序》中有详细描述:
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1992—1993年,在洛阳市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落发掘出白居易故居遗址。履道坊西门即今狮子桥村落东出口处,发掘地点在该坊西北隅,紧张有住宅、园林、水渠及道路等遗迹,出土建筑构件、陶瓷器、铜器、铁器、骨器等遗物。白氏住宅在履道坊内西北角,是一处坐北朝南、有前后两进院落的宅院。宅院内有一平面大致呈方形的中庭,东西5.5米、南北5.8米。东、西两端由回廊与东、西厢房相连。自中庭向南约12.6米处,残余一段踏步和散水,平面大致呈凸字形,为宅院的门庭基址。由此向南,为园林区,称为“南园”。当年,白居易对此小园环境十分满意,有诗为证: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豪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自题小园》)
南园经钻探与局部发掘,证明有大片淤土,面积达3300平方米,深1.9~3.2米,应是南园中的湖面,西侧有一条小水道与唐代伊水渠相通。在白诗中,这一片湖水被称为“池”,白公以此为题材,也创作过不少诗作:
水积春塘晚,阴交夏木繁。(《池上早夏》)
薰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首夏南池独酌》)
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池上》)
檐前微雨歇,池上凉风起。(《雨歇池上》)
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闲题家池寄王屋张羽士》)
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池上竹下作》)
唐代伊水渠在宅院的西侧与东侧,呈曲尺形,宽约9.2~11米,淤土中包含有丰富的唐代遗物。渠西有一条南北向大道,宽约8.2~8.5米,发掘长度10米,路面及路土中散见一些砖块、瓦片、陶瓷片及鹅卵石等。此路土当为履道坊与集贤坊之间的坊间大道,出土唐代遗物较多,有建筑材料、陶瓷器及铜钱等。当年白居易最为欣赏的便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安卧于室内,仍能听到伊水渠中潺潺的流水声,他写道:
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是时群动息,风静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满耳秋泠泠。终日临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惬,亦不要人听。(《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
在该遗址发掘过程中,最为主要的创造是清理出数件残石经幢,个中一件刻有“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等内容,另一残块仅存两面,有“唐大和九年”等铭文,从而证明此地确为白居易故居遗址。
洛阳水系发达,洛水横贯全城,分为洛南、洛北两大区域,而联系两者最主要的桥梁便是天津桥,石砌桥墩于2000年创造,并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天津桥位于要冲,白居易时常由此经由,此桥也成为白公吟咏的工具:
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天津桥》)
晚归骑马过天津,沙白桥红返照新。(《早春晚归》)
上阳宫里晓钟后,天津桥头残月前。(《晓上天津桥闲望偶逢卢郎中张员外携酒同倾》)
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和朋侪洛中春感》)
斯人已去,诗作长存
唐太和七年(833年),由于白居易的文坛老友相继离世,让墨客深感寂寞,扪心《自问》:
依仁台废悲风晚,履信池荒宿草春。(自注云:“晦叔亭台在依仁,微之池馆在履信。”)自问老身骑马出,洛阳城里觅何人。
并失落鹓鸾侣,空留麋鹿身。只应嵩洛下,长作独游人。永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
这里的“晦叔”即崔玄亮,其宅位于洛南依仁坊,西邻白居易住的履道坊;“微之”即元稹,宅第在履信坊,南邻履道坊。两位绅士均为白居易的好友,两处宅院因主人的逝去而逐渐衰落,令白公极为伤感,以至于发出“洛阳城里觅何人”的感叹。
白居易在洛阳期间,创作诗歌达到800首以上。唐开成三年(838年),67岁的白乐天自撰《醉吟师长西席传》:“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不雅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不雅观。……每每乘兴,屦及邻,杖于乡,骑游都会,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旁边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岁酿酒约数百斛。”唐开成五年(840年),白乐天将自己在洛所写诗歌合集入藏龙门喷鼻香山寺,并在《喷鼻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中说:“《白氏洛中集》者,乐天在洛所著书也。大和三年春,乐天始以太子来宾分司东都,及兹十有二年矣。其间,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合为十卷,今纳于龙门喷鼻香山寺经藏堂。”
唐会昌六年(846年),白居易卒于履道坊家中,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后来,白氏宅第变成了佛寺,东都、江州父老还为其立祠。
李唐以降,五代期间的梁、唐、晋三朝皆以洛阳为都。期间战事不断,对城市造成较大毁坏。北宋期间,洛阳作为太祖赵匡胤的老家,他屡次欲迁都于洛,但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后将洛阳定为西京,相沿隋唐旧城,城市情貌有所改不雅观。后在金与南宋的战役中,洛阳城在经历了长达五百年的发展之后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急剧低落,金代为了有利于军事防守,将洛阳城垣范围大大紧缩,修建中京城,紧张包括隋唐东都的东城和洛北里坊区的一小部分。元、明、清三代亦用该城,这便是本日我们常说的洛阳老城。老城平面形制大致呈方形,面积2.25平方公里,约占隋唐东都城面积的1/21。
本日身居闹市的老城十字街,沿袭着深埋于地下的隋唐街道遗痕。在老城区的考古工地,还能发掘出隋唐期间的建筑基址、夯土城墙、灰坑、烧窑;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偶尔还能拾到残断的唐砖宋瓦、粗陶细瓷。
而洛阳城中的白居易宅第,在白公逝去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坎坷之路。五代、北宋时的白居易履道坊故居尚存,后唐时为普明禅院,有后唐明宗次子秦王李从荣所施大字经藏及写白公诗集置藏中,故该寺俗称“大字寺”。在宋代墨客李清照父亲李格非所撰《洛阳名园记》一书中,这样写道:“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甲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犹存,而曰堂曰亭者,无复仿佛矣。岂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可恃邪。寺中乐天石刻,存者尚多。”《邵氏闻见录》还有其余一种说法:“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池台故基犹在。”北宋墨客宋庠写有3首以普明禅院为题的诗作,个中谈到了寺院与白居易的密切关系。《过普明禅院二首》第一首云:“自昔仁为里,于今福作田。清风残竹地,宝色故池天。绘象成真侣,家声入梵缘。一披龙藏集,无复叹亡篇。”作者自注云:此寺为唐太子少傅白公旧宅,寺内有乐天旧影与蒲禅师偶立。后唐明宗次子秦王特写白公函集一本,置经中,至今集本最善(《元宪集》卷五)。元代初年,蒙元军将塔里赤奉旨南征至洛阳,得白乐天故址,曾经在此居住。
元末明初,履道坊一带成为耕种庄稼的农田,白氏故居的许多主要遗迹遭到严重损毁。在白居易宅院遗址西南隅,发掘出两座元末明初的石灰窑,在两窑的底部及窑门处,出土许多残碎的青石块,个中一些经由加工的柱石及碑刻残块,上面刻有笔墨。由此推断,元末明初之际,宋人所说寺中存者尚多的乐天石刻,可能被作为烧石灰的质料,遭到了彻底毁坏。
白居易在隋唐洛阳城留下的踪迹也随着隋唐洛阳城的起起伏伏而经历波折。然而,现实中的那座隋唐洛阳城虽然损毁,白居易诗作中的这座隋唐洛阳城,依旧保留着千年前的气候。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8BKG03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