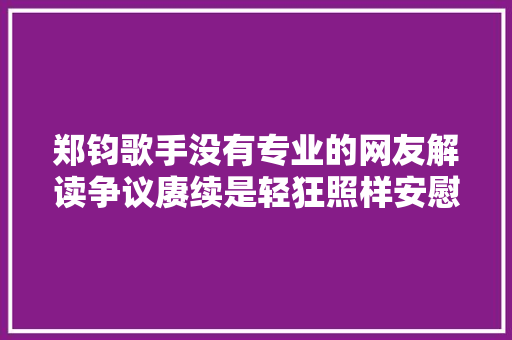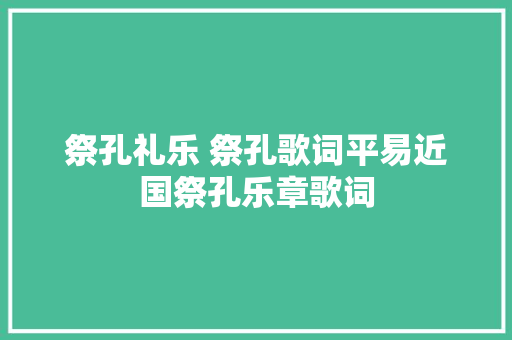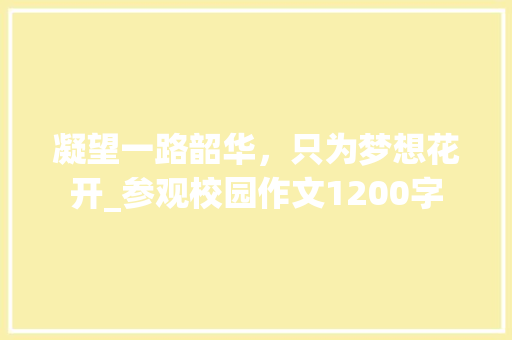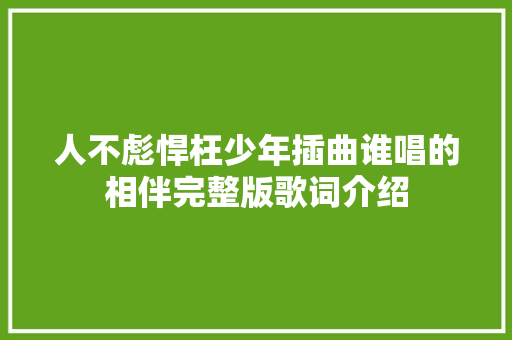这一幕,让多少不雅观众落泪。
前阵子恰好有粉丝问我:“咱们的赤色特工,真的不能把身份见告妻儿吗?”答案在多数情形下,都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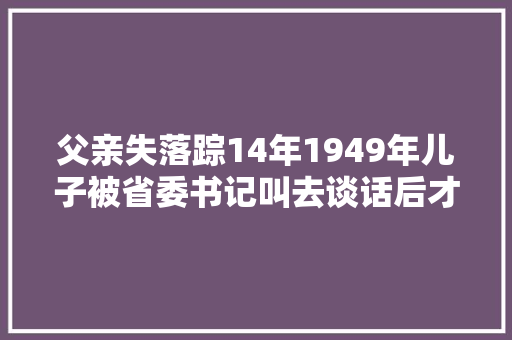
对付这些暗藏战线上的英雄来说,不但须要长年忍受着仇敌的猜疑,而且每每承受着被家人误会的无奈。但这是他们的选择,从接管潜伏任务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们将承受这统统。他们无怨无悔。
而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本期笔者就跟大家说一段建国后发生的往事。
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时任安徽省团委布告的青年干部项南接到了一个主要任务。任务是省委布告曾希圣亲自支配给他的,内容为:寻人。
之以是会有这样一个任务,是由于前几天,在东北公民政府事情的梁明德,溘然联系到曾希圣,希望他能帮自己探求一下失落散多年的儿子。梁明德是曾希圣的老战友,两人曾并肩作战多年,以是对付他的重托,曾希圣十分上心。
梁明德见告曾希圣,他听人说自己的儿子现在就在安徽省青年集团系事情。于是这个“寻人”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团委布告项南头上。曾希圣叮嘱项南,老战友的儿子已经失落联10多年了,一定要尽快找到,让革命元勋一家团圆。
项南对这件事很重视,回到团委后就动手开始了查找。只是曾希圣给出的条件太过宽泛,而且缺少细节,这也让项南的探求事情始终难以找到打破口。
一段韶光后,曾希圣等得有点心急,便找到项南来讯问探求情形。项南只能据实申报请示:“能不能再供应一些干系的详细情形?”
听项南这么一说,曾希圣也意识到自己之前有点操之过急,下任务的时候太过草率了。于是在一次事情会议结束后,单独把项南留了下来,准备供应一些进一步的细节。
曾希圣见告项南两个新信息:第一个信息,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第二个信息,梁明德是个地下党,30年代时他们一家住在上海八仙桥一带。
这番话让项南一韶光有点错愕,由于曾希圣说的这些东西他太熟习了。他随口说道:“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住过……”
曾希圣听完项南的回答,也以为很凑巧,于是便急忙问道:“你们家住八仙桥哪里?你父亲做什么事情的?”
项南接下来的回答,让曾希圣很欣喜。项南说:“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做生意的。”
项南口中提到的这个地点,是30年代我党地下组织在上海的一个联结点,曾希圣当年就常常到此地通报情报。于是曾希圣赶忙追问项南,问他们家为何当时会住在那儿,他还见告项南这个地址是我党的联结点。
这下轮到项南懵了,他纳闷地问领导:“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地下党呢?”
随着两人之间聊得越来越深入,曾希圣越来越以为面前的项南和自己要找的人很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只是过去了那么多年,他对付这种预测也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他溘然想起自己当年常常到梁明德家去,还常常和他要找的儿子一起玩。
于是曾希圣试探性地问项南:“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南点了点头。父亲是个买卖人,平时结交的人当然很多。
听到这个回答,曾希圣便“意有所指”地问项南:“他的朋友中,是否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
这一问,项南也意识到了什么,当即回答道:“有,有,有一个大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
事情发展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这个项南便是曾希圣下任务要找的人,这可正是应了那句老话“远在天边,近在面前”。
一韶光曾希圣也是感慨良多,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贯在找的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细细看着面前的项南,越来越以为他的眉眼间和老战友梁明德是那么像。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曾希圣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
项南望着面前的曾希圣,忍不住大声喊道:“胡子叔叔!
”
至此,项南的身份算是彻底确认了,他便是梁明德要找的儿子。曾希圣也跟项南详细说了他父亲的真实身份、经历,以及为什么会改名换姓叫梁明德。而这些细节,也让项南终于确定了一件事:“失落踪”14年之久的父亲,真的是我党的赤色特工。
一下子,项南内心释然了。原来,父亲的身份真的不大略。实在早在6年前,他对付父亲的身份就以为很迷惑。
1943年,也便是父亲离家8年后,项南跟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在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当时组织要审查他的家庭出身,当同道们问到项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时,他一韶光犯起了难。
由于对付父亲的职业,项南真的说不清楚。父亲说他是买卖人,但在项南的印象里,另日常平常便是常常跑码头。他不开店,不知道详细卖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做生意彷佛从来赚不到什么钱。
以是当时面对组织的问询,项南的回答含暗昧糊,都是“可能”、“大概”这种不愿定性的字眼。卖力审查的同道们很聪明,他们根据项南关于父亲的描述,创造这个人很神秘,各类行为和我党地下事情职员很像,于是不少同道就问项南:“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
这是项南第一听说父亲可能是地下党。对付项南来说,如果父亲真的是一个赤色特工,那该有多好?作为儿子,他当然希望父亲和自己是一个战线上的同道。
只是,那时项南并没有确切证据,而且当时他已经跟父亲失落去联系多年,连对方是生是去世都不知道。以是对付同道们的预测,他只能无奈地表示:“可能吧。”
那么梁明德和项南这对父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当年他们一家住在上海时,父亲梁明德到底在实行什么绝密任务呢?梁明德“失落踪”的这14年,都去了哪里?
多年后的本日,梁明德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众人所熟知,他便是:项与年。这3个字,代表着一段传奇。本期请随着笔者一起,理解我党赤色特工项与年的传奇,这是一段关于国与家的尘封往事。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的一户田舍。在发展过程中,项与年目睹了军阀混战和老百姓的水深火热,于是便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并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很多福建人都到南洋去做生意,项与年身边有些朋友都过去了。恰好我党要在南洋等地发展建立组织,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项与年头上。毕竟他头脑灵巧,又能说福建话,他去是最得当的。
就这样,1926年初,项与年踏上了前往南洋的旅程。当时项与年已经结婚多年,儿子项南(原名项德崇)也已经8岁了。这是项与年第一次离开儿子,当时他对儿子说自己是去南洋做生意。项南从小就跟父亲的感情很好,对父亲的话他笃信不疑。
项与年去的地方是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那里是荷兰的殖民地。他到当地后积极奔忙在华人中间,积极宣扬革命思想,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还在当地建立了党支部。并以此为根本,在当地组织掀起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成为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只是在那样的漩涡中,项与年屡屡身处斗争一线,成为了殖民当局的眼中钉,终极被当局逮捕。好在在当地华侨各界的努力下,当局开释了他,但同时他也被驱逐出境。
无奈之下,项与年只能回到老家。去南洋做生意的同村落人多少都能赚到点钱,唯有项与年回来时是身无分文的,这是亲朋好友们都无法理解的。毕竟,不管是论头脑还是论肯吃苦,项与年都不比同村落的年轻人差。
对此,项与年倒也没有太多阐明,总是说:做生意嘛,本来便是有赚有赔的。那时,项南只有9岁,这些事他还不懂,能再见到父亲,他已经很愉快了。
一家人团圆后不久,组织上给了项与年一项新任务:前往上海从事地下事情。当时的上海,是仇敌防控最严密的城市之一。那里表面上歌舞升平,一派繁华,实则敌我斗争十分激烈。
为了便于掩护,这一次项与年没有选择独身只身前往,而是举家迁居到了上海,他们就住在八仙桥附近,这便是前文项南提到自己在上海八仙桥居住的经历。
当时,周恩来亲清闲上海组建了中心特科,项与年是个中“行动科”的主要成员。行动科的任务便是惩办叛徒和敌特,以是他们有个称号叫“红队”。
这段韶光,项与年景了一个“双面人”。
在表面,项与年和战友们是出生入去世、在枪林弹雨中实行任务。1929年,为了除掉出卖澎湃等同道的叛徒白鑫,项与年和战友们精心策划并实行了锄奸行动。在仇敌的层层防控下,了却了叛徒。
在家里,项与年是一个“市侩”的买卖人。他每天早出晚归,彷佛永久有做不完的买卖,忙不完的应酬。家里的大小事,都是由妻子作主。也便是在这段韶光,“胡子叔叔”等人也常常来家里。小小年纪的项南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商量着什么,只知道他们每天都行色匆匆。
1933年10月,此时项南已经15岁。项与年又一次接到组织任务:前往江西德安,在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的军队里开展情报事情。
莫雄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却有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和我党职员也素有往来,在上海时曾提出加入我党。不过考虑到莫雄的分外身份,连续留在国民党内无疑更利于开展事情,以是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让他加入我党,而是让他以国民党将领的身份为我党供应力所能及的帮助。
恰好在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让他自己组建班子。这也就给了莫雄和我党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趁机派自己人到个中任职,帮忙莫雄从事地下秘密事情。项与年作为中心特科的骨干,这个任务自然少不了他。
就这样,项与年又一次离开了妻儿,踏上了革命征程。不过对付家里人,他只说自己是去九江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这是他和儿子的第二次离去。
项与年的这次潜伏是非常成功的。
当时蒋介石任命莫雄为保安司令,实在紧张任务便是“剿共”。为了合营莫雄的事情,项与年等地下党员一边派人和当地红军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游击活动,另一边还让莫雄主动出兵,和当地红军打了几场仗,每次红军都是佯装败退。
这实在便是双方在唱“双簧”,在这些“剿共”的战斗中,项与年等地下党员费尽心机为当地红军供应了大量物资补给。蒋介石不知个中的黑幕,还以为是莫雄有能力,又尽职尽责,于是还专门通报表扬了莫雄“剿共得力,全省第一”。
以是在接下来的牯岭高等军事会议中,蒋介石专门点名特邀莫雄前往芦山参加。这是一次,级别很高的主要会议。
会议全程都极为保密,经由一周的切磋研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终极制订了一个名为“铁桶围剿”的操持。
理解历史的朋友,该当会很清楚这个操持。内容概括起来便是纠集150万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央、半径达300华里的包围圈。为了担保这一操持的顺利,会议谈论出了很多细节,比如如何吸引我军的把稳力,如何支配堡垒线。
莫雄听完这个操持后,直接吓得捏了把汗。如果这一操持真的成功,对我军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情形十分遑急,必须把这些细节全部传送出去。
这一关乎死活的任务交给谁,成了莫雄须要思考的问题。他自己出面,目标太大,肯定是弗成的。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项与年。
项与年当然知道这一情报意味着什么,这不但是莫雄和他自己的性命问题。他当即和同道们一起做出了两个明智的安排:首先,他们把操持的大致内容用电台申报请示给了中心苏区;其次,他们又弄来了4本学生字典,用特制的药水把情报的细节写在个中,由项与年送往中心苏区瑞金。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由8个县市,通过几十个关卡,难度可想而知。好在,项与年本身长得就文质彬彬,以是他一开始扮装成了一名教书师长西席。
当他到达南昌附近的一个关卡时,碰着了查抄的仇敌。仇敌见他背着一个袋子,伸手就要检讨。
虽然字典里的情报是用分外药水处理过的,但如果他们详细翻看,难保不会被创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项与年急中生智,当即捂着嘴对检讨的仇敌说:“老总,我的牙痛又产生发火了,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
同时他就在袋子里开始翻找牙痛水,一边翻一边随手拿出那几本字典在检讨的仇敌面前晃了晃,说:“袋里几本字典,本人教书用的。”
检讨的仇敌看项与年的袋子里除了字典也没啥东西了,而且看他文质彬彬,也就没有过多纠缠,便放行了。可以说这一次能够“逃出生天”,项与年完备便是靠自己的机警。
到了南昌我党的地下办事处往后,项与年考虑到这几本字典实在是有点显眼。于是他赶忙找到几位地下党员帮忙,将字典上的机密情报全部缩写誊抄到了一张薄纱纸上,然后将它们藏进了布鞋垫层里,穿着连续赶路。
只是随着项与年逐渐靠近瑞金,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如果连续以教书师长西席的身份提高,很有可能会引起仇敌的疑惑。项与年思考再三,决定扮成一个托钵人连续前行,毕竟当时正值浊世,很多老百姓颠沛流离沦为托钵人,这样的身份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不过项与年本身一幅文质彬彬的样子,即便蓬葆垢面伪装成托钵人,和这个身份也有点扞格难入。于是他钻进路旁的僻静处,找了块石头,用力往自己嘴上呼唤,一下子就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虽然项与年强忍着,但突如其来的巨大疼痛还是让他昏倒在了路旁。
等他醒来,便强忍着疼痛连续前行。此后的一段韶光,他每天昼伏夜出,饿了就随便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河水,困了就在树底下短暂休息一下子。此时的他早已是蓬葆垢面,身上的衣服和鞋子也是破褴褛烂,和真的托钵人已无两样。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碰着了仇敌的盘查,在经由一个关卡的时候,仇敌凶恶地盯着他问:“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项与年心里早就打好了腹稿,他假装怯懦地说:“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我奔跑中跌倒时摔的。”仇敌见他衣衫褴褛、全身血污的样子,嫌弃地赶他快走。
就这样,一起奔波一起被人嫌弃,项与年终于困难地抵达了中心苏区。当他把鞋子垫层中的情报取出来,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在场的众人看到他全身血污的样子,无不冲动。
而他送来的绝密情报,也武断了我军进行计策大转移的决心。可以说,这份情报对我党是极为主要的。3天后,红军开始了长征,这间隔国民党庐山牯岭会议制订“铁桶围剿操持”还不到一个星期。
此后项与年就随着党组织开始了长征之路,不过在途中,为了反击仇敌的围追堵截,项与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带领爆破职员到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机场及油库,毁坏他们的补给线。
不过这次任务并不顺利,他们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虽然项与年终极凭借过人的聪慧逃了出来,但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了项与年的安全,也为了我党地下组织的安全,党组织暂时让项与年回到上海的家中,不要有任何行动。
当时项与年在上海家中待了一个多月,这是项南影象里父亲在家里待得最久的一次,那也是他影象中最幸福的一段光阴。只是这幸福过得太快,一个多月之后,1935年春节刚过,项与年接到组织任务,又匆匆离开了家人。这是项南和父亲的第三次离去,此时的他已经17岁。
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为了暗藏身份,项与年改名成了梁明德。而原名项德崇的项南也参加了革命,把名字改成了项南。他跟父亲一样,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我党的精良青年干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此时,这对父亲已经失落联14年了。
解放后,项与年开始探求儿子。但父子皆已改名,以是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项南找项南”的奇事。
好在,他们终极找到了彼此。得知父亲的真实身份后,项南激动得一夜无眠。他没想到,父亲是这么伟大的一名赤色特工。原来当年他多次匆匆离家,不是去做生意 ,而是实行主要的革命任务。他为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骄傲。
当晚,睡不着的项南拿起笔,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全部见告了父亲,他想让父亲知道,这些年他没给父亲丢脸。
不过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初期,他们各自的事情都很繁忙。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参加会议,这对阔别18年的父子,才终于得以重聚。
那一天,看着终年夜成人,还这么有出息的儿子,项与年硬是不敢认。他们面对面地站着,都没有说话。许久后,项南主动走过去,叫了一声:“爸爸”。两人都哭了。
此后为了新中国的培植,父子两始终聚少离多,再加上他们都很低调,以是他们的关系知道的人也不多。
1978年10月2日,84岁的项与年因病去世。他的伤悼会上,来了很多领导,项南作为家属站在前排。伤悼会用的是梁明德这个名字,当时有同道还把项南拉到一旁,问他:“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项南这才见告大家,梁总是他的父亲。众人听完,无不感佩。
项南是幸运的,由于他在父亲还健在时,就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他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满。但还有一些赤色特工,他们身份至去世都没有为妻儿所知。比如我党传奇特工阎又文,他至去世都没有机会大公至正见告儿女:你们的父亲是一位精良的共产党人。直到他去世29年后,儿女们才意外得知。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有一种伟大,深埋于心。仇敌不知道,战友不知道,妻儿也不知道,但山知道,江河知道,祖国不会忘却。谨以此文,纪念暗藏战线上的所有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