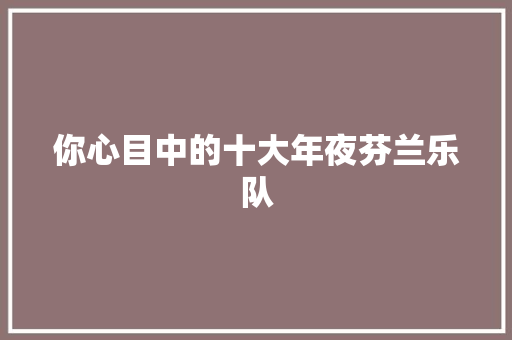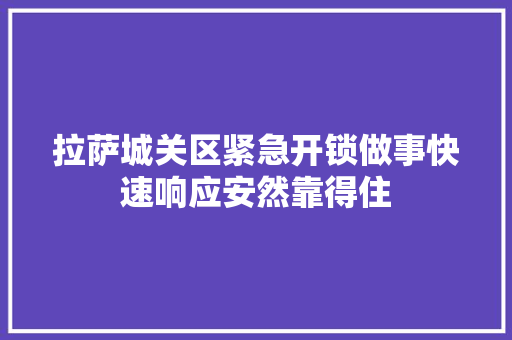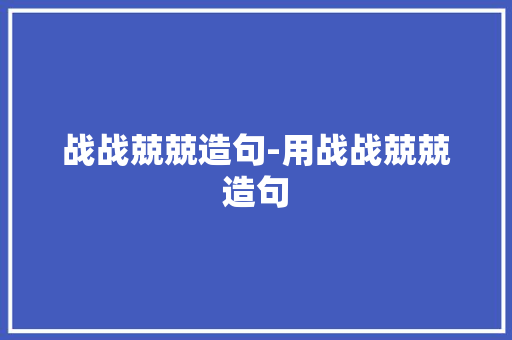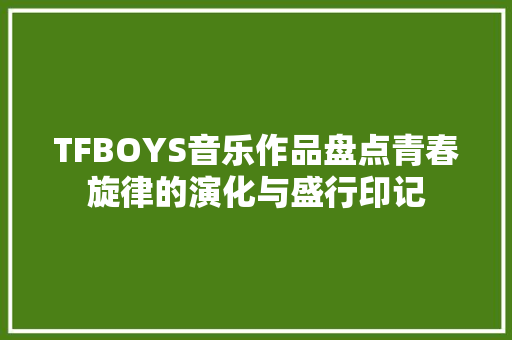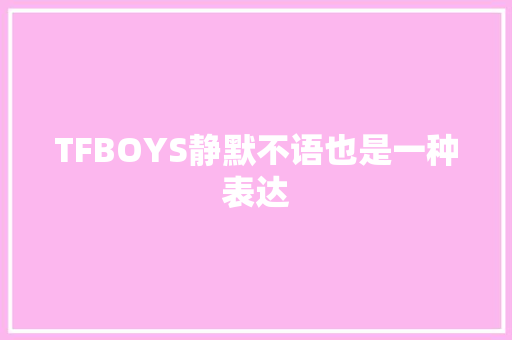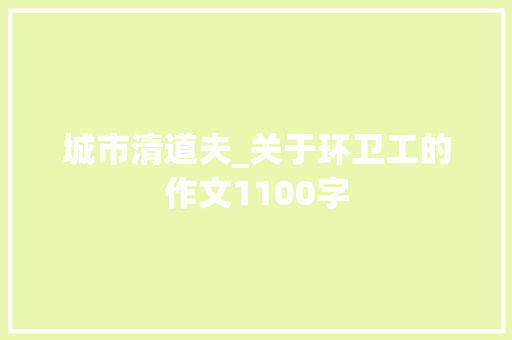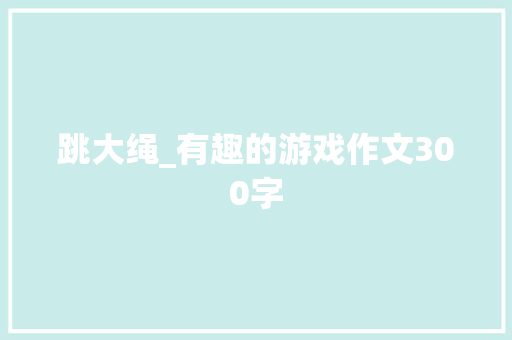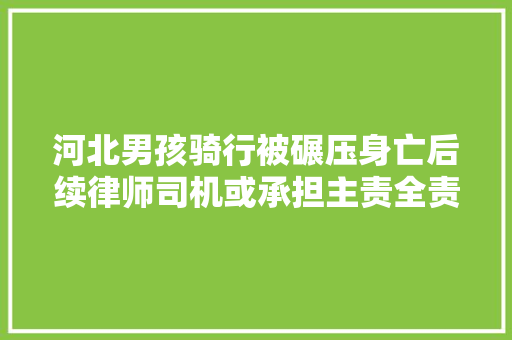大略地说:好妹妹的这一次翻唱,到底有何清丽脱俗之处?
随着和齐豫一同演绎的《船歌》的释出,我的疑问被解开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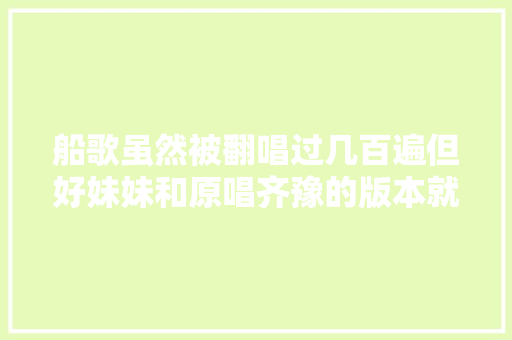
在好妹妹一次的访谈中,他们提到了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十多年前,以“发热唱片”的名义,小娟把《梦田》、《花祭》、《爱的箴言》等歌曲通过她空想化的办法进行演绎,实现了这些经典之作的暗度陈仓,也影响了像好妹妹这样的年轻世代。
乃至在好妹妹后来的创作中,“再唱一段思想起”成为写入他们身体里的DNA,台湾盛行音乐黄金时期对他们的影响,大概比他们自己想的还要深。本着一向的臭美,好妹妹用一张专辑的长度,去阐明他们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并试图把这些决定他们日后的音乐光谱再一次分享出去,也是蛮奢侈和任性的行为。
至于为什么会把《船歌》作为第一主打,我以为有以下三点考量。
一,表示尊重。
无论后面的9位女歌手是谁,齐豫的地位都无可撼动。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作为女神级歌手,齐豫本身便是一个盛行音乐的Icon,她和李泰祥、三毛等所树立的盛行文化与典雅艺术相互领悟的标准,迄今后人依然难望其项背(乃至写下这段话时,我也不禁换了一种肃然起敬的腔调)。好妹妹以齐豫作为致敬和传承的出发点,是得当的。
且改编的《船歌》,其原曲中男声的部分就占了相称的比重,好妹妹在其根本上进行发展,你初听好妹妹的版本时,前面的部分实在和齐豫自己的“老歌新唱”并没有太大差异。由齐豫的独唱引领,再到男声仿照舟子号子的“Boom Boom Boom”,在第二段主歌时,好妹妹的声音才作为主音涌现。这样的处理,对付老听众来说显得充满诚意且有礼貌,会更随意马虎接管后面的改编。这表示的,首先是对前辈的尊重。
二,重塑中国风。
《船歌》作者为罗大佑,是他少有的、现在被称作“中国风”的作品。罗大佑参考了江南水乡的男女应答式船歌号子的写法,去展现游子的流落感,并利用了良久影象点的民乐打击乐,乃至我后来一贯认为,“船歌”便是像《船歌》里唱的那样。虽然歌曲里也有利用木吉他这样的泰西乐器,但这首歌的东方小调色彩是绝对隧道的,这便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国风”。
在好妹妹过往的作品里,尤其是首张专辑《春生》里的《相思授予谁》、《冬》,包括后来他们在《说时依旧》里重唱的《往事只能回味》,都带有这种“中国风”的意味,虽然他们并没有用明显的民乐作为表达,但字里行间、尤其是旋律里的低回,是这个味儿。
这次重唱《船歌》,我能觉得到好妹妹对“中国风”情意结的坚持,歌曲前奏里的笛子一出来,清幽的感情就被渲染开来了,然后是迪吉里杜管——提及来,最开始听时我并没有把它识别出来,后来看制作名单时,才知道原来那个类似口弦拨动的音色,也是迪吉里杜管发出来的。
来自澳洲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它虽然不能机动地吹出音阶,但它的低鸣和气声非常适宜铺排感情,且用在《船歌》里,其他乡色彩可陪衬游子思乡之情,乃至它的视觉效果(以长达一米或以上的树枝制成)也和船篙很相似,对歌曲意境塑造很到位。以及在沿用了原曲的民乐打击乐的同时,用更具有感情化的弦乐给予歌曲能量,加上原来就很经典的东方调式旋律,这样的体例也可视作中国风的典范。
三、“在路上”的传承。
《船歌》对付我来说,并不是纯挚的一首“老年人脱销金曲”。作为罗大佑为电影《衣锦回籍》所打造的配乐,歌曲第一次涌现,是黎明时分,张艾嘉在船头洗衣,洪金宝整理衣衫,船即将靠岸,分别十数年的嫡亲终于见面,表中国人范例的近乡情怯之感。歌曲再一次涌现,则是在末端,张艾嘉出嫁的时候,流落感成为了宿命的循环,“水乡温顺,何处是我家”,成为了一个百感交集的命题。
我所理解的singer-songwriter,它总要有一种“在路上”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是身体上的,同样也是生理上的。安于一隅,这不是吾手写吾口的唱作人。不论前方是阳关大道还是丛林荒野,他们都会去选择冒险,通过音乐抵达未曾到过的地方。
对付好妹妹的来说,这种“在路上”的流落感,实在是他们主要的情绪标签之一。从那时专辑《南北》用火车票的拼贴作封面,到他们的巡演“清闲如风”,好妹妹作品中所调动的当代年轻人的共鸣,有很大程度来源于好妹妹供应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选项。虽然你看他们彷佛总是上综艺或干别的,但骨子里他们还是到处为家的铃鼓师长西席。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有这种觉察,但他们和齐豫唱这首歌,真的很搭。
以上三点,让我以为单就《船歌》这首看来,也打消请到了原唱助力的成分,我以为他们现在做到的比十年前小娟那稍显糖不甩的要强(没有捧一踩一的意思,小娟本便是传承者之一)。当然,完全的评价最好是等到全张专辑都底细毕露了再来下判断。以是潘越云、郑怡、娃娃、小玲姐、蔡琴是不是已经都安排上了?
音乐自媒体“乱弹山”
万马齐喑的浊世里,
透过音乐,
我们记录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