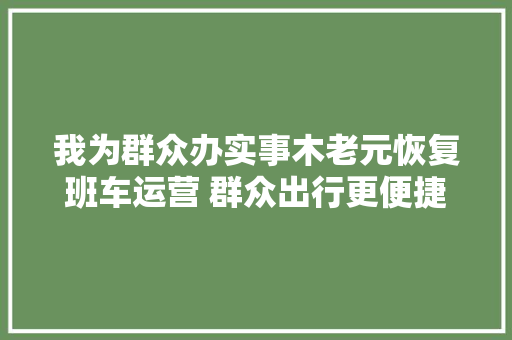走着走着,人声少了,林子深了。松树落影间,涌现了一块由云南省公民政府于2015年8月15日立的碑,上书“中国远征军第261团义冢”。再往上爬,才知道这儿是合葬义冢,所有的将士是一个集体——“261团”。这里说是墓,实在便是一方方土,杂草间隆起的一堆堆便是墓。忽的,鼻头一酸,眼泪竟从心头直涌出来。
战役年代统统从简,261团的将士们被拉回这里相依安葬,有的也只是带回了衣冠。诚如复修碑上所述“就太平街旁修成义冢 合葬我江防殉职者之劲骨 慰我宁为玉碎者之英灵”,1944年6月10日滇西抗战大反攻前夕,远征军在太平建筑了合葬义冢,这是对逝者的礼遇,更是对那群即将再次奔赴前哨的生者的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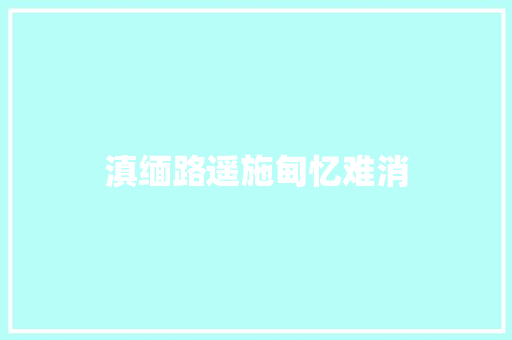
本日,我们脱帽,鞠躬,鞠躬,再鞠躬,排列整洁地向这英雄群体表达内心的哀思与崇敬。
在温暖的光阴里,重走浴血的路,是一种思想与现实的碰撞,我们在沿江的惠通桥、堡垒间游走,思绪在面前的尘土飞扬与历史的战火硝烟中跳跃穿梭。从由旺子孙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旧址)出来,坐在图书馆的蒲团上,手里捧着《横戈怒江》《血肉滇缅路》两本书,里面阐述了滇西抗战历史中的许许多多施甸人、施甸事。
恍惚间,面前尽是战火硝烟,受伤捐躯的将士、光脚拷(砸)石头的修路小孩、牵马运粮的民夫、战火渡江的竹筏历历在目。
若说,滇西抗战与你我无关,那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若说,滇西抗战与你我有关,那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仅限于中学的历史教材,这又太牵强。人总是这样,对付和自己无关的影象总是消散得快些。我们没有经历战火硝烟、没有亲手砸石铺路、没有瞬间嫡亲相离,我们多是在缓缓的日子里过着,挨着来自外界亦或自己内心的压力,努力生活。岂不知,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属痛快酣畅。岂不知,离家不远处埋葬着那么多为了祖国捐躯的将士。岂不知,那日惠通桥炸毁后并没有阻断所有的日军。岂不知,今日弯弯绕绕到太平的路,那颠簸的弹石路面上,纵然只是小小一块石头也是饱含血泪的。
来,一起翻开书,随着修建滇缅路民工们的影象,一起走进那段历史。
> 1930年6月出生的杨如美去修滇缅路年仅12岁,她说修路去了几天后,一日有人在江对面喊,渡过去的人回来说日本人来了,让快跑。
来到桥头,人挤人,人挤车,桥两边分别捆着一包炸药,导火线“嗞嗞”冒着火烟,一边还立着一把半尺来宽的大刀。老倌儿喊:“别瞧,快走!
”过了桥,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轰”的一声响,转头,江西的桥面已经不见了,只见江里的水花掀起数丈高。枪声大作,松山那边的大炮一直地向这边的公路轰。路边有一片平地,几堆人顶着毯子呜呜地哭。——摘自《血肉滇缅路》
> 1930年2月出生的杨如国有去修滇缅路时年仅8岁,和裹小脚的大姑妈去修滇缅路。
那年我8岁,出工只是刮刮土,端端小碎石。
我大姑妈裹小脚,常常是挑重担子,裹着的脚磨出了大水泡,后又变成血泡,血水和裹带粘连在一起,每天睡觉前她都烧一锅温水逐步浸泡,那时,正是寒冬,我们民工的棚子里都烧一个小火塘,睡觉时,大姑妈就把脚露在被子外晾着,第二天出工前又把脚裹了起来。——摘自《血肉滇缅路》
> 1923年2月出生的徐有娣,当时背着不满两岁的儿子日日出工去修滇缅路。
要打大松山的时候,我的男人和村落中的青壮男人都被派去当民夫去了,村落中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
拷石头时,石末像面粉一样飞,到晚上收工,脸就像一个拉磨人,眼睛和鼻子都分不开。有时,小娃哭,就喂一口奶。晚上收工了还摸黑煮饭,吃过饭还舂一臼喷鼻香叶。远方枪一直地响,想想离家不知去世活的男人,眼泪就一直地掉。——摘自《血肉滇缅路》
>1925年出生的杨绍义是家中宗子,老父亲是个石匠,修路时随着家里的老叔去。
毛路修通往后,我们接着铺沙垫石的时候,铺一道就用石碾子压一道。石碾子有一米多高,三四吨重,两头有轴子,那轴子像我们拉磨的磨管心,轴子外又斗着一个木架架,木架上拴上杯口粗的4根绳子,拉的时候,一根绳子站六七个人,压路时,石碾后有4个撬手。
洋邑坪有一段转弯上坡路面,一天,太阳火辣辣的,我们拉着石碾正上坡,拉绳子的一个民工忽然晕倒了,人一阵慌乱,石碾就今后滚,在后撬石碾的4个人,居中的两人当场压成了肉饼,分不清哪是肉,哪是骨,居边的一人一只大腿被压碎了……
老人阐述着忽然从心底长长哼了一声,声音中断了,昏花的眼中,豆大的泪珠滚落在地上,胯前的地面也打湿了……—— 摘自《血肉滇缅路》
当时施甸总人口9.4万人,驻扎在施甸的中国远征军10万人,派出民夫150万人次,出动畜力53万匹头次,修通江防便道160公里,修复滇缅公路65公里,征集粮食1400万斤,征集肉食14万斤,扩修毛路130公里,帮忙修建战壕12公里。目前,施甸境内滇西沙场遗迹包括:1942年5月初至1945年1月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在与日军隔江对峙两年零八个月期间,在怒江防线上建筑的堡垒、阵地、战壕义冢及沙场遗迹17处;沿江渡口、远征军旧址13处。
读完这些,再重走一次滇缅路吧!
带着描写滇西抗战、描写滇缅路的书,边走边读。
此时,你会创造,滇西抗战施甸数字碑上的那一串数字逐渐丰满。在太平镇跑马山,埋葬着中国远征军第261团的将士们,他们相依埋葬、无分你我,他们为国捐躯,不畏归家无路。在滇缅公路沿线,有着老少民工的血汗,有着颠簸的弹石路面,有着散落的石碾子。当你远足深山,瞧见突出的一方方土,请错开走。或许,那一方土堆下长眠英雄骨。
滇缅路遥,施甸忆难消。光阴走得太快,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忘怀那段战火硝烟的旧光阴,走过了它才有了我们本日的安然。
后记:
9月28日至29日,由县文广旅游局主理,县图书馆、新华书店承办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滇西抗战江防遗迹实践式阅读活动在施甸县境内怒江沿线开展。各州里文化骨干、阅读爱好者、专业学者40余人,一同重走施甸抗战遗迹。分享会上,众人感伤之余更觉重任在肩,滇西抗战属于施甸的那一块影象连施甸人都要忘怀了,这弗成。我们要做的是发动可以发动的所有力量,挖掘整理这段历史。同时,利用诗歌、纪实文学等各种手段去弘扬施甸本土文化,让更多的施甸人精确认识历史,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