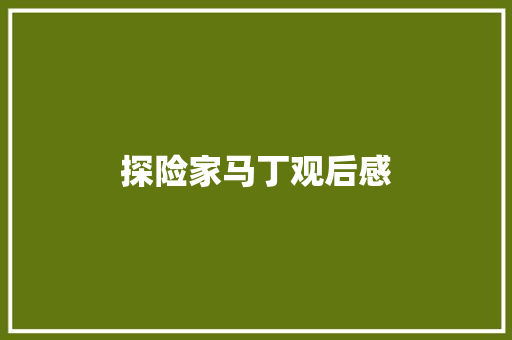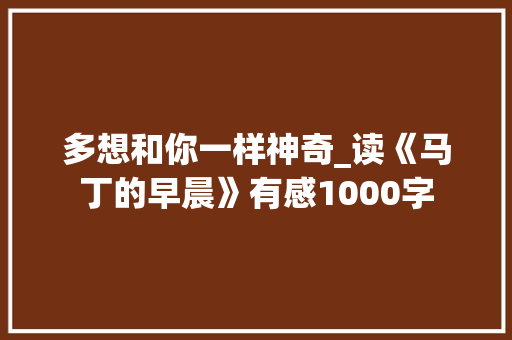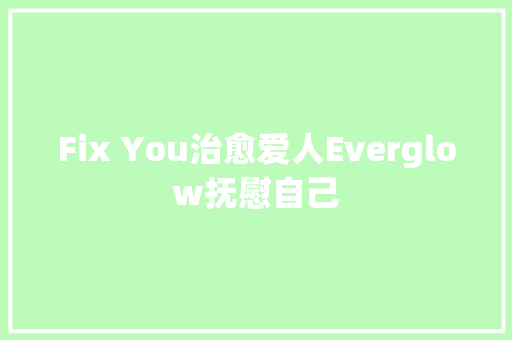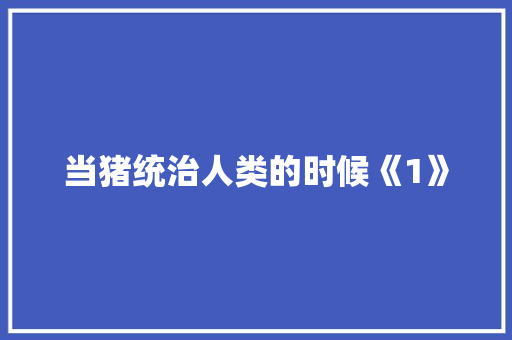在马丁遭熊袭生还后埃文人就对她说,“要体谅熊”、“不要恨它”,也有人关怀地问,“你体谅熊了吗?”
本书也是马丁寻求创伤背后意义的内在旅途。她也在终点展现了接管创伤、埃文人、熊、自己,以及创伤没有任何阐明的可能。也正是因此,读罢全书,释然之感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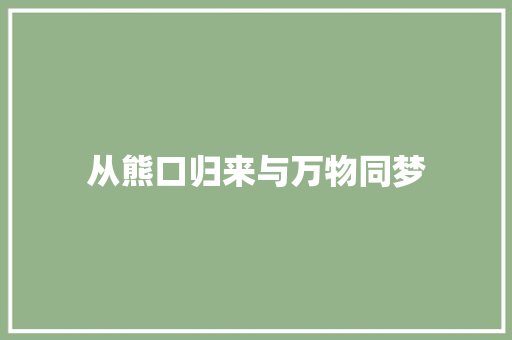
娜斯塔西娅·马丁著《从熊口归来》,袁筱一译,上海公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年5月
缘起
马丁选择去勘察加埃文人那儿做人类学野外调查始于有时。去那儿以前,她的野外埠是和勘察加隔着白令海的阿拉斯加育空堡,和那里的哥威迅人(Gwich’in)一起生活。一次有时的机会,她的哥威迅朋友神秘兮兮地说要带她深入荒原看看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们带她看的是朝向白令海对岸的卫星锅盖——时时刻刻,在这个凡人不会涉足之地,美国仍旧密切关注着对岸的情形。猛然间,马丁尤其想知道,所谓的“对岸”生活着若何的原住民部族,他们也有这样的秘密地吗?她深切地感想熏染到如果不理解他们,她的研究便是不完全的。
从很多角度来说,哥威迅人和埃文人有截然不同的命运。马丁刚开始涉足哥威迅人生活之地时,以为他们的文化险些不再存在了,生活境遇可悲可怜,曾经和大自然共存共生的聪慧,他们的仪式和歌谣,对宇宙和梦境的理解无处可循,直到她花了几年韶光深入当地才逐步看到自己梦寐以求想要找到的原生聪慧。埃文人就不一样了,马丁首次探访勘察加时就创造他们的文化存在感极强,还有政府举办的文化节日。哥威迅人的文化是被压抑的,埃文人的则是被刻意强调的。
达利亚的苦难和沉着
马丁想找的是那些真正重返自然的埃文人,他们是渔人、猎人,生活在森林深处。但这并不随意马虎。经由不懈努力,她才找到这样一家人并让他们接管了自己。女主人达利亚成了马丁紧张的信息宣布人,也是个充满母性的角色,而且她“能瞥见不同天下的东西”。达利亚逐渐向马丁透露了自己的命运,她的讲述是“循回往来来往的,时而重复,时而戛然而止”,马丁在法国文化节La Manufacture d'idées的一次分享会中说到。在《从熊口归来》里,达利亚的话散落在作者的意识流里,每一句都带着冲击。她向作者回顾苏联解体时说:“有一天,灯光熄灭了,精灵回来了。然后我们出发去了森林。”这触动了马丁,她想到的是:“在我的家乡,灯光从未熄灭过,精灵都逃走了。”要知道,马丁认识的巴黎被誉为光之城。
达利亚给予马丁启迪、守护和爱,更主要的是,向她展现了超越创伤、收成沉着的可能。马丁遭到熊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经由漫长、孤零零地在荒凉医院里的挣扎后,获准出院回法国连续治疗。分别时,达利亚、她的儿子伊万和马丁抱在一起哭了,“接着,达利亚首先规复了沉着,”马丁写道,“每一次都是如此,由于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生活的苦难。”
达利亚曾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在蒙古包内的火堆旁向马丁吐露了自己“五个孩子的两个爸爸离世”。
“第一个去世于集体农庄的劳作,第二个在后苏联时期去世于争斗和抢劫。”达利亚对熊也有不同的意见,她见告马丁自己每次看到熊,就想这或许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和她打呼唤,“大海把他送了回来”。这当然会触动年幼丧父的马丁“想起了自己身边消逝的亲人,想他们现在是在哪里,是不是也能够见到我。”
告别那天就和蒙古包里的那个夜晚一样,达利亚不断地见告马丁:“Ni nado plakat Nastia——不要哭,娜斯佳(马丁的小名),Ysio boudet khorocho,统统都会好起来的。 还有:想要连续活下去,就不能想不好的事情。该当不断回忆的,只有爱。”
半人半熊
多年以来,马丁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都在网络“多重存在可能居于同一具身体里的故事”,为的是颠覆“一元的、统一的和单维度的身份不雅观念”。她知道在埃文语中有专门的词,miedka(米耶德卡),指“被打上熊的烙印的人”,即遭遇了熊还活下来的人。她也知道“得到这个称呼的人从此便是半人半熊”。
马丁始终在探寻的是人和动物、自然、其他性灵的身份边界交融的可能,半人半熊看似和她的设想相合。遭熊袭后她更想冲破自己和熊的界线,至少把我和熊变成“我们”,她始终在想的问题之一还包括:“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彼此?”
她也试图通过熊吻事宜来探索内心深处的各种伤痕。在法国治疗时就思考着各种抽象问题,创造自己“从来未曾想过要让自己的生活沉着无波,尤其是和他者的相遇。……很永劫光以来我都在北极事情,这便是一个处在动荡之中的地方。我知道如何在变革、爆炸之中事情……在我看来,危急状况是思考的好机会,由于危急状况总是隐蔽着另一种生活,另一个天下的可能。相反,安宁并不是我善于的。我虽然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我的确在暗示自己,要到高处的平原去探求内心深处战斗性的一壁……像一个悍妇一样平常投入战斗,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了对方的符号。我很难阐明这统统,但是我知道在这场相遇之前,统统都是有准备的。”
在法国,人们粗暴地把她的经历解读为一场悲剧。她无法接管即便是接管灵魂天下这个观点的西方人也把其他存在投射为自己的灵魂状态。“对付它们自己的生活,对付它们在这个天下的足迹,它们的选择,我们究竟是怎么对待的?”她险些是质问道。每个试图理清她遭熊袭缘故原由的人则都把统统归于马丁,从各种童年创伤和内心阴影来解读她的行为、希望和去世亡冲动。
治疗基本完成后,马丁第一韶光回到了埃文人那里,去探求创伤背后的意义——她的创伤也是熊的创伤。她以为,埃文人有半人半熊这个观点,能理解她,也能见告她和熊相遇背后的深刻缘故原由。马丁还想要知道、理解熊到底经历了什么,感想熏染到了什么,“谁又能说清楚,除了那种根本的功能主义的阐明,推动它行动的究竟是什么?显然,有些东西我永久都不会知道的,但这并不虞味着该当放弃,放弃更深层的理解。”
等她回到那里之后,创造的却是自己被贴上了“半人半熊”这个标签,埃文人有和西方人不同的天下不雅观、意见,但做法仍旧是贴标签、分类,而不是相领悟一。
有埃文人和马丁阐明了熊为什么要咬她的脸——那是由于熊和她对视了,“熊不能忍受与人类直视,由于它们从中看到的是自己的灵魂。”而且“一头熊,倘若遭遇了人类的目光,它会一贯试图抹去它所瞥见的。”这也是熊和人之间的差别,前者无法与他人直视。
马丁试图解读埃文人的意见:“见到一个看到熊的人或是一头瞥见人类的熊,便是可逆转性的象征;在这种面对面中,一定发生的激烈转变事实上只是一种尽可能的靠近;在这一空间中,熊只是人在另一个天下的影子而已。”
埃文人还认为“半人半熊”只能带来不好的东西,必须避开他们,乃至连他们的东西也不能碰。“他们害怕,由于像你这样身上留有熊的印记的人,是唯一直接打仗过熊的人。……一种来自久远之前的亲近,才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才能够让这样的事成为可能。”达利亚没有回避马丁,接着向她阐明埃文人认为“半人半熊”意为着人不完备是人,身上有一部分是熊。而且对某些人影响更大,终生都会被熊追逐,在现实中和在梦里都是如此。自己没有避开马丁的缘故原由则是不相信这些所谓的传说,“我们和所有的灵魂一起生活,那些流浪的灵魂,那些在旅途上的灵魂,活的和去世去的灵魂,‘米耶德卡’和其他。大家一起生活。”达利亚也认为马丁能活着回来意味着她是“熊给我们的礼物”。
埃文人对“半人半熊”的解读同样刺痛了马丁,让她既冲动,又感到愤怒。冲动的是埃文人和西方所信的不同,“他们都很明白,森林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生命,也在这里生活、感想熏染、思考和谛听,在他们周围,其他力量也在起浸染。在这里,有一种人类之外的意愿,不受人掌握的意愿。” 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克拉规复了“万物有灵”这个词,他也是马丁的老师,他们用万物有灵“来定义和描述这样一种类型的天下:在这条道路上,我和其他生灵,我们的身心彼此追随。”
马丁认为“在‘熊给我们的礼物’这句话中,暗含着这样一种想法,便是和动物的互换是可能的,只管这种互换只有在罕见的情形下才会以可控的办法发生;这句话还见告我们,很明显,我们生活在一个统统都可以被不雅观察到、被听到、被回顾起、被给予和重新拥有的天下里;这句话里还有对除我们自己之外的生命的关注;末了,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
让马丁愤怒的是,这句话意味着埃文人解读她和熊的相遇仍旧不是她所期望的合一状态,“熊和我,我们又一次成为异于我们自身的其他东西;我们相遇的结果是说给不在场的人听的,说的是不在场的人。”
她在书中也提到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和写作偏好一贯关于“边界、边缘、极限性、边界地带、两个天下的中间地带,等等”,她认为“在这个地方,有可能碰着另一种力量,我们有可能改变,而且很难再回去。”猎人的天下便是如此,“猎者会抹上猎物的味道,穿上猎物的外衣,调度自己的声音,采取猎物的声音,这样就可以走入猎物的天下,这时猎者戴上了面具,不过在面具之下,他还是他自己。这是他的诡计,也是他的危险所在。于是所有的问题就变成了,杀去世对方,这样才能回去——回到自身,回到他的亲人身边。否则便是失落败,被他者吞噬,不再在人类的天下存活。”
人类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边界之地事情,在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交合之所,这对马丁有致命吸引,“不再回到自己的天下,被另一个天下彻底擒住的风险,是巨大的。”她在Jan Michalski基金会的演讲上说。她说的是原住民和西方人的天下,也是生与去世的天下。
勘察加使得马丁在阿拉斯加的研究更完全的缘故原由比她曾设想的更深刻也更切肤——“在阿拉斯加我写下了这些事情;我在堪察加半岛经历”,她在书中写道。
梦与醒的边界
达利亚见告过马丁,对一些“半人半熊”来说,终其生平都会被熊追逐,在现实里也在梦境里。梦是另一个马丁热衷的地带,与万物同梦也是《从熊口归来》的另一条线索。
遭熊袭后,马丁在法国的生理年夜夫用西方视角解读她的梦,这令她抵触不已。事实上,早在熊袭之前、乃至是在去勘察加之前,她就对原住民对梦的意见略知一二了。
阿拉斯加育空堡的一位哥威迅族智者是马丁的朋友,他说的许多话也深受马丁重视。比方说,他见告马丁“树、动物、河流,天下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记住我们所做的、所说的统统,乃至有时候,还会记住我们的所梦所想。”在哥威迅族智者看来,梦和现实是并行的。
隔着白令海的埃文人对梦也有类似的意见和履历,并不认为梦是假的,他们相信梦是指引,决定了第二天该如何行事,像是到哪里去捕猎等非常实际的决定都可能是由前一晚的梦决定的。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围着篝火分享自己的梦。达利亚和其他埃文人在黎明时分的蒙古包内讲述自己的梦时也总会压低声音,不是恐怕打扰别人,而是不肯望“它们”,即其他生灵、存在听到他们说的话。
马丁在哥威迅人那里得知他们可以和森林一起做梦,自己在那儿也做梦,不过在当时,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或是“人类学家所必须的同理心的大略表现”都说得过去。到了埃文人这儿,她有了深刻的亲自经历,而且认为“这不是一件安逸的事情”。
和埃文人一起后,她做梦的征象变得越来越难阐明。马丁一直地做梦,也加倍厚重。“梦境是我和埃文人共享的东西,我开始梦见他们所梦见的,熊以及其他猎食动物,它们有时是猎物,有时是猎手。埃文人有时可以和它们建立对话,但也不是所有的时候。” 马丁在Jan Michalski基金会的演讲上进一步阐明,“我阔别自己的舒适区,更薄弱,也有更多内在空间,让这些梦境通过我展现。”即便如此,她仍旧认为“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隐蔽其后,便是15年野外事情的总结和意识。我想通过这本书表达的也是人类学家不是超人,我们不可能以彻底客不雅观的视角来记录自己的野外”。
达利亚更不以为这有什么好错愕的,很正常,“你离家那么远……你看到那么多东西,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总结道。她见告马丁,“与某种事物一起做梦,便是得到讯息。”埃文人还认为“我们梦见一些事物,一些事物也会梦见我们”。
马丁成为半人半熊后,达利亚见告她 “你的梦既是它(熊)的梦,也是你的梦”。在遭熊袭前,这些梦就让马丁想要逃离了,她认为正是这些梦终极把她送进熊嘴里。现在,与熊同梦“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而且达利亚还说,这更意味着她该留下。
离开与归来
马丁终归还是要走的,她细细描述又一次别离,说在森林里“从来不是逐渐准备好要走,从来都不准备,大家仍旧是没有任何变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变革一下子来临”,她写到埃文人也从来不评论辩论分离的时候,“那个统统都不复从前的时候”。在明知要离开却仍在一同度日的一每天里,她就和所有人一起“复苏地生活在永恒的幻觉之中”。
马丁走时达利亚说自己并不难过,“由于在这里生活便是等待回归。等待花开,等待迁徙的鸟儿,等待主要的生命。你也是这些主要的生命中的一个。我会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