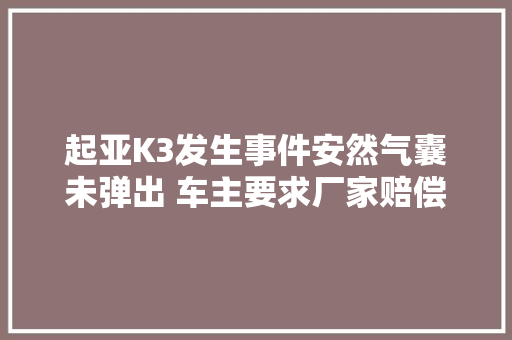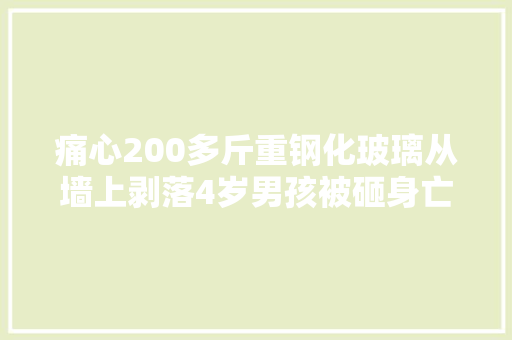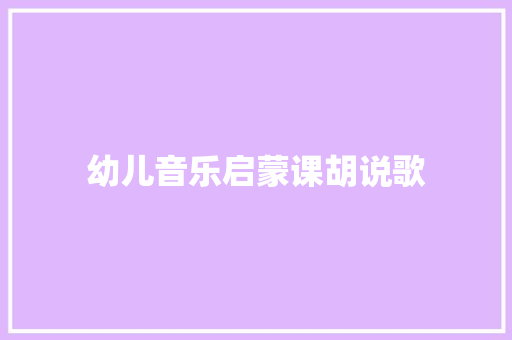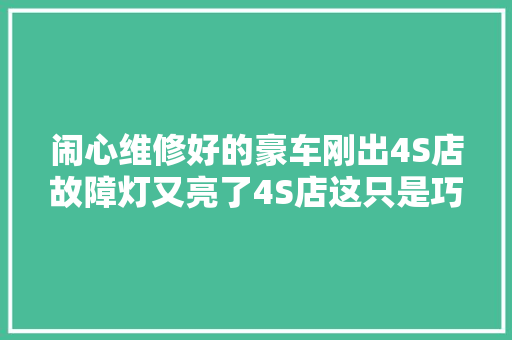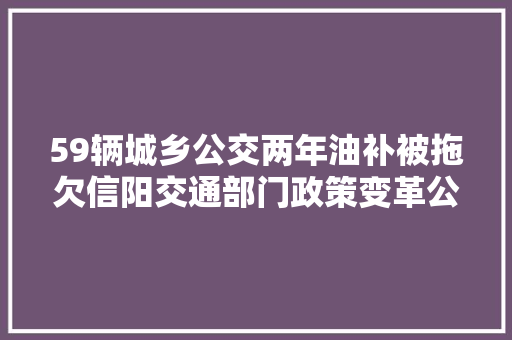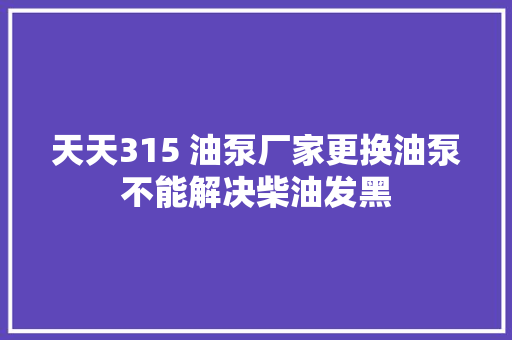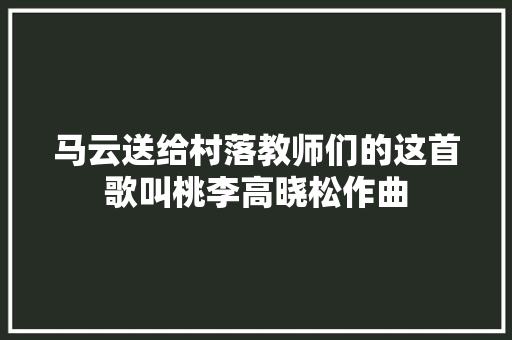在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这样的情景: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一位七十多岁、视力衰退的老者,前倾着身子坐在电脑前,用大号字困难地为我解答学术问题;夏日里,他顶着太阳,去邮局给我这个并不认识的远方学子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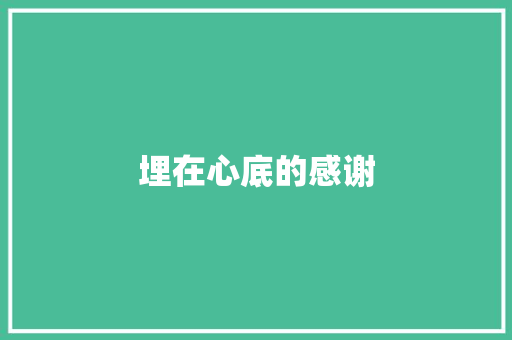
十几年前,我还在青岛大学中文牵挂捆扎书,在帮助冯光廉师长西席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王得后师长西席致冯师长西席的一封羊毫信札,上面写着王师长西席的电子邮箱。王师长西席是研究当代文学的老一辈学者,1934年生人,这一代学者会上网的很少,王师长西席却能够自若地收发电子邮件,可见他乐意接管新事物,乐于寻衅自己。
我喜好读师长西席的文章,此前已经读过他的学术著作《两地书研究》《鲁迅心解》和随笔集《垂死挣扎集》。经查阅得知,他还出版过《人海语丝》《世纪末杂言》等杂文集。然而当时青岛像样的文史类书店不多,许多学术著作难觅。于是想给师长西席写封邮件,问问他是否还有存书。邮件发出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师长西席的复书,他说他会到鲁迅博物馆的书屋找一找。后来,师长西席专门去了一趟,却没找到书。为了对我的阅读激情亲切表示鼓励,他寄来了他的夫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老师签赠的一本著作。
王师长西席以研究鲁迅名世,于是我在阅读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碰着什么问题,就会给师长西席发邮件请教。有一次,我问起师长西席某个题目值不值得做,从何处下手,须要哪些准备事情。师长西席回答说:“学术研究是对研究工具的一种创造,恰如天文学家不雅观察星空一样,根柢在非常熟习工具,发人之所未发。不读原著,不熟习原著,仅凭一点不雅观感,是难成大的造诣的。”师长西席的话,让我逐渐镇静下来,知道了自己的盲目,知道了学术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要负责阅读原著,有了知识的积累和真切的人生体验后才有发言权。师长西席的话,我一贯服膺。
2012年春天,我的硕士论文《论鲁迅书信的当代意义》开题在即,我想听听王得后师长西席的见地,于是给他发去邮件。同样是在第二天便收到了师长西席的复书:“我双目黄斑变性,视力大减,已经不能读书读报,只能在电脑上把字放大,阅读与写作。但我乐意拜读您的大作。……‘书信’‘日记’,初衷本是不揭橥,不给"大众看的,彷佛不说‘著作’更准确,换一个名词如何。虽然如此,已经公开拓表,它的意义自然起了变革,不妨碍人们研究。只是正如您开题报告后面也提到的,不能不看到它的‘私密性’。由于收信人不同,写法、内容也不同,有些是‘应酬’,不可不把稳。”
师长西席在信中还提到一件事,说鲁迅博物馆有一个“鲁迅全集检索系统”,如果我没有可以发给我一个,在电脑上自动安装就能利用了。“自然,这只是工具,功底还在自己熟读《鲁迅全集》。比如书信,鲁迅对收信人的称呼不止一个,必须分别输入每一个称呼,才能检索完好。”这对付研究鲁迅的人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检索系统可以让研究者节省大量韶光。师长西席跑了一趟邮局,给我寄来一个光盘,检索系统顺利安装。
2013年我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就没敢再叨扰师长西席。然而在我的书架上总是放着师长西席的两摞著作,有师长西席多年前出版的书——是我从旧书网站上购来的,也有近年出版的新作。师长西席既搞学术研究,也坚持写杂文随笔,两条腿走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结合得很好。师长西席认为,研究鲁迅而不写杂文,是说不过去的,那样就不能深层次地理解鲁迅。
去年秋日,我和朋侪去北京的一处养老社区看望北大教授钱理群师长西席。我知道王得后师长西席和赵园师长西席也住在这里,于是想去看望。然而钱师长西席见告我,他们夫妇眼疾较重,得后师长西席的眼睛险些看不见了,很难接待访客,于是作罢。我为二位师长西席的身体状况担忧,也为无缘相见而深感遗憾。
记得师长西席在一篇散文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妻子赵园问他,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怎么生活?师长西席说,如果真有来生,我还是要研究鲁迅。这让我心头一热,充满冲动。师长西席何幸,与鲁迅精神相遇;青年学子何幸,有这样内心羞辱的师长西席答疑解惑。在与师长西席交往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深远的教益,也感想熏染到了浓浓的温情。在此,我想向未曾谋面的师长西席道一声“感激”,同时祝福师长西席90岁生日快乐,学术生命长青!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3日 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