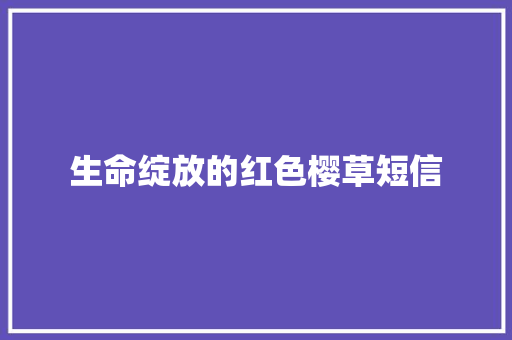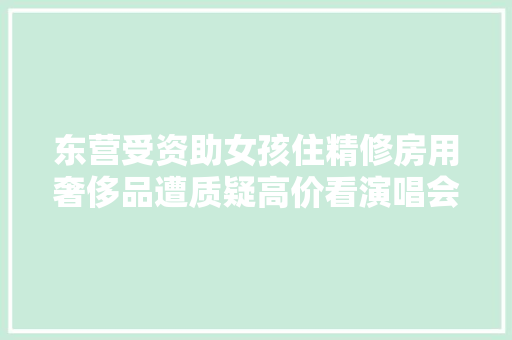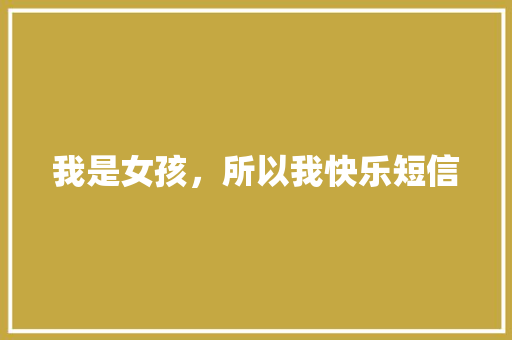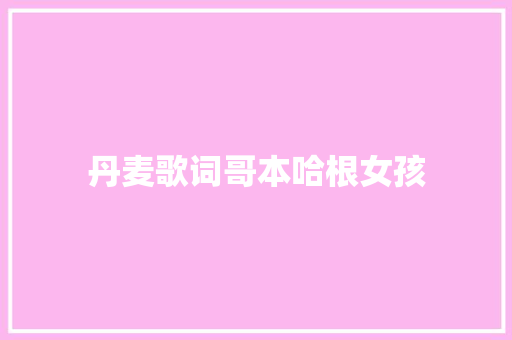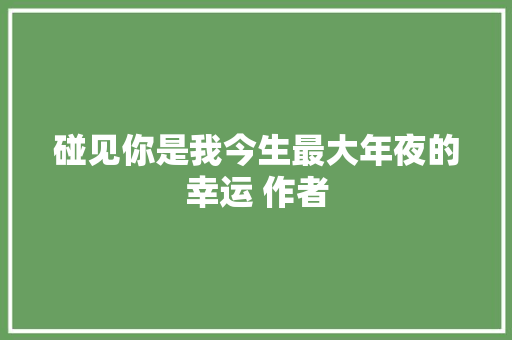自一位客人欠妥心将他的照片上传到网上后,旅社的买卖火爆起来。
然而本日却来了一个自称是他未婚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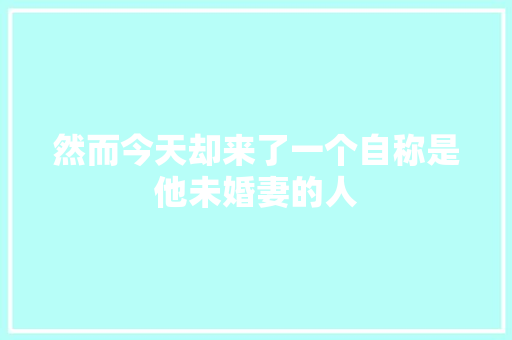
1
这几天小旅社的买卖越来越好,客人大多是女生,见了阿沉之后都捂着嘴笑,还有不少人临走之前会找他要微信。
我是有些吃醋的,但阿沉会扬起我们牵着的手像是无声地回答。
女孩子们知道我们是一对之后便不再多纠缠,笑笑之后便离开。
然则日却来了一个和别人都不一样的女孩。
她穿着很俊秀的衣服,一进门就气势汹汹的。
“喂!
这个男的是你们店里的吧,他在哪儿?”
女孩将手机举到我面前,图片的主体是上个星期来过的一位客人,隔得远远的坐在前台的便是阿沉,纵然拍得很糊也难掩帅气。
难怪最近这么多年轻女孩儿来呢,但这个女孩看起来彷佛认识阿沉,或者说,从前的阿沉。
“说话啊!
”
见我没答话,女孩骄纵地拍了拍桌子。
可是阿沉不在,他去王婶家摘菜了,本日晚上要给我做喷鼻香椿炒鸡蛋。
我努力地给这位小姐比划着,她的神色越来越不耐烦。
“怎么是个哑巴。”
女孩面上闪过不屑,抱着胸站在一旁。
正说话间阿沉从表面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大把喷鼻香椿。
“阿辞!
”
女孩眼睛一亮,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阿沉,声音绵软且委曲。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谁?我不认识你。”
阿沉使力将女孩拽开,走到我身边牵起我的手,无声地表明了态度。
女孩本就伤心阿沉推开他,见到我们牵在一起的手眼睛红得吓人。
“阿辞,她,她是谁?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你不认识我了吗?”
女孩哽咽着,上前想拉开我们牵着的手,可阿沉拉得很紧,她急得想给我一巴掌,却被阿沉推到沙发上。
立地,女孩在眼眶里打转的泪珠就落了下来,我见犹怜。
“沈令辞,你干什么呢!
”
“我不叫沈令辞,我叫秦沉。”
女孩终于意识到了什么,脸上的娇嗔僵住了,狠狠擦了一把眼泪,娇声娇气地说道。
“你以前是叫沈令辞的,阿辞,我们曾经是未婚夫妻的,我可以给你讲讲我们的曾经,你一定会记起来的。”
我看着面前这个女孩,她眼中是满满的自傲和武断,让我有一种阿沉末了一定会跟他走的危急感。
转头看去,阿沉的眼睛跟我对上,里面有些许挣扎。
他是个不同平凡的男人,我救下他的时候就知道。
我是在上山采药的时候遇见他的,他身上有很多摔伤,腿在走快时还会跛脚,最严重的是他有两处枪伤,还是爷爷帮他把子弹取出来的。
或许阿沉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很快乐无忧,但我知道他一贯想知道自己的过去,发呆的时候常常摩挲着一块俊秀的腕表。
我冲他点了点头,于是我们闭店,他带着我和那两个人一起进了客厅。
从那两个人的口中我得知,阿沉原名沈令辞,女孩叫罗琴安。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的终年夜,到高中都是同一个学校,而阿沉和女孩日久生情于是他们就在高中毕业后订了婚,但阿沉读大学时家道中落,女孩的爸爸不愿女儿嫁给他。
阿沉毕业后一起进了军队,起誓会尽快提升军衔娶罗琴安,于是他接了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任务,便是那次任务阿沉身受重伤,从此失落踪了三年。
“阿辞,你想起来什么了吗?”
故事说完之后,罗琴安一眨不眨地看着阿沉,眼里满是期待与不安。
我也看着阿沉,他表现得很沉着,没什么反应。
看来是什么都没想起,罗琴安的眼睛黯淡下来,我却把稳到陈桉卸了一口气。
“我什么都没想起来,小姐请离开吧。”
阿沉作出“请”的手势,一贯珍藏的腕表终于从长袖里露了出来。
罗琴安看到后很激动,转悲为喜,从手里拿出来另一只腕表后放到了桌上,扔下一句“我来日诰日再来”就犹豫满志地离开了,临走时不忘朝我投过来一个挑衅的眼神。
阿沉的表是蓝色的,女孩的是粉色的,看起来被主人保存得很好,阿沉默默收起了表,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女孩果真来了,但在住的客人离奇地都退了房,并且没有新客人再来。
“我让下人定了你们店一星期的订单,够赚了吧,你也不用这么辛劳了阿辞。”
女孩摇动手机,得意洋洋地笑着,眼睛里满是刁滑。
“现在我是你们旅社唯一的客人,好好奉养我。”
女孩完备把我当成了透明人,前台的电话险些被打爆了,一下子是修热水器,一下子是空调,阿沉怕我被刁难从不让我上去。
我悄悄上去过一回,阿沉跪在地上给罗琴安穿鞋,看起来专注又虔诚,罗琴安则注目着阿沉,手轻轻抚过阿沉脸上的疤。
“阿辞,你以前就这样给我穿鞋的,记得吗?我们从前真的很甜蜜的。”
阿沉没有躲,也没有回答,垂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罗琴安看着这样的阿沉溘然烦躁起来,脚一蹬就缩回了床上,从钱包里扔下一沓钱。
“喏,钱,阿辞你以前不这样的,和我待在一起都很愉快的,不是不说话的。”
我摸了摸藏在头发后面的助听器,它是爷爷给我买的,有点旧了,取下来时耳朵特殊红,也把阿沉的眼睛给心疼红了。
我转过身下楼,再也没上来过,我怕我心疼,更怕阿沉知道了尴尬,我固执地守旧着这个秘密。
一星期后,女孩不得不离开,许久未见的陈桉也涌现了。
“阿辞,我和爸爸约定好的七日之期到了,你真的还没想起我吗?”
她的保镖往车上放着行李箱,罗秦安站在门口,一贯看着阿沉,眼里是不舍与难过。
阿沉牵着我,只看着没说话。
很明显的态度了,罗秦安用力吸了吸鼻涕,瓮声瓮气地说道:“末了抱我一下呗,阿辞,我回去就要和别人订婚了。”
阿沉还是没动作,拉着我的手却骤然收紧。
很疼,我却没法叫出声。
“好!
我知道了!
”
罗琴安用力地说出了这句话,然后转身抱着巨大的决心冲到大马路上。
“哔!
”
小车错愕地按着喇叭,等我回过神来手上的痛感已经消逝了,阿沉跛着脚飞奔过去一把将罗琴安推开了。
“你为什么不拉好阿辞!
”
手术房外,罗琴安走过来狠狠给了我一巴掌,眼里却是挑衅和得意。
是了,她已经证明阿沉在乎她了。
脸上火辣辣地疼,可手上也疼。
“臭小三,真以为救了阿辞就能一辈子拴住他,他是在乎我的!
”
另一巴掌纷至沓来,我伸手去拦,可手被一贯在阁下的保镖捉住了。
我的助听器终于飞了出来,在地上四分五裂。
罗琴安哧了一声,又上前用力地碾了碾,保镖又变成了一座沉默的山似的站在一旁。
我听不见了,只是凭着她的表情辨认该当是在嘲笑我。
戴助听器的聋子哑巴。
阿沉被推了出来,还好小车司机的技能算高超,及时刹了车。
阿沉伤的并不严重,进病房的第一刻就把我叫上前,抚着我的脸温顺地笑,然后用手指了表面叫我出去。
可是我本来就什么都听不见啦,阿沉,别赶我走。
我想问你,你想起来了吗?你要抛弃我吗?
我啊啊地比划着,眼里满是祈求,阿沉看不懂手语的,可阿沉这次非常地武断。
等我再进来时,罗琴安第一韶光朝我投来嫉恨怨毒又失落望的目光,阿沉的枕边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言言,我们去帝京治你的耳朵吧。”
我想说不要,可阿沉的眼睛是那么的不容置喙,以是我也只能点头。
罗琴安把我们安排在了一个屋子里,屋子很俊秀比小镇里的好了几百倍不止,原来阿沉以前住的便是这种屋子。
“这便是你以前的屋子,怎么样,我买下来了。”
罗琴安的嘴一张一合,脸上瞧着十分得意,阿沉看起来很是怀念,忧郁的眼睛一贯打量着这屋子。
刚歇下不久,当天深夜有一位中年男人在一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我和阿沉都跪着,身旁有两个健壮的保安压着我们,有人悉心地给我递上了助听器。
“沈令辞,你还敢回来?又想拐我女儿,别忘了你现在一穷二白,这屋子还是我女儿给你的。”
“知趣点等我女儿等你女朋友治好耳朵之后自己滚回小镇里,我会给你一笔钱足够你们生活到老,但别再到帝京来。”
男人饱含威胁的目光落到阿沉身上,阿沉垂着头没说话,想来是默认了,牵着我的手却不断收紧。
罗琴安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了,瞥见我们的样子容貌后便抱着男人的臂膀撒娇。
“爸爸,我好不容易把阿辞给找回来了,你别这样嘛。”
男人的面孔浮上一丝优柔,只是嘴上却没一丝松动。
“爸爸,如果您不让阿辞起来,我也一起跪,如果您不让我们结婚,我就立时去世给你看!
”
说着,罗琴安作势要跪下,但男人哪舍得女儿跪下呢?
摆摆手让部下松开胁迫,我们得以坐在沙发上。
“罢了,既然安安这么喜好你,届时你去警局确认身份后该当也能得个名誉,也不算太配不上安安。”
“只是,你这女朋友,最好送回小镇去,你们也最好不要再有联结。”
罗琴安见男人松口,立时绽开了笑脸,美目不断朝阿沉使眼色。
“不,我会和言言过一辈子,您女儿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言言会是我的妻子,就算是我影象回来了也一样。”
阿沉沉声开口,语气仍旧武断,只是放在膝盖上的手却逐渐使力,青筋在上面浮现。
罗琴安的神色立时黯了下来,男人也没想到阿沉会这般看不起自己女儿,冷哼一声伸脱手指,带着罗琴循分开了。
“我女儿看上你这种毛头小子是你的福泽,你还不领情,看完病就滚回镇子上去吧。”
我却把稳到他食指上戴着一个很熟习的戒指,很像,我脖子上挂着的那枚。
他们走后,阿沉终于放松下来,狠狠将我拥进怀里,不住地念叨着:
“言言,我不会抛弃你的,我绝不会和罗琴安在一起。”
听起来像是说给我听的,但我总以为他是念给自己听的。
第二天一起床罗琴安就拉着阿沉带我去了医院,年夜夫拿着什么东西在我耳朵里面乱戳。
乃至戳到了很里面,我痛地推了一把年夜夫,立地就站了起来,转身朝阿沉看去,却创造他看似看着我,余光里却在关注罗琴安,连我不声不响地站起来都没把稳到。
阿沉,不做了,我好疼。
我拉着阿沉的手想撒娇,可他的神色却有些不愉,仿佛我打断了他。
但又彷佛是错觉,他立时又换上了温顺的笑颜,摸了摸我的头后又强势地把我按回了手术床上。
罗琴安见我这样子嘲讽地一笑,当着我的面给年夜夫使了个眼色。
疼,我疼!
我不要治耳朵了。
我奋力地挣扎着,阿沉终于不耐烦了,彷佛在嫌我不乖,上前用力地将我按住。
罗琴安彷佛和阿沉说了什么,满脸嗔怪,彷佛在说我真矫情,而后让身边的保镖一起按住了我。
我哭了,真的很疼,我流出了眼泪。
“言言妹妹,检讨都是这样的呀,不疼怎么会好呢,你耳朵好了就可以和阿辞一起回镇子里了,忍忍吧。”
罗琴安将手机递到我面前,阿沉看到之后也赞许地点了点头,彷佛在认可她说的我不懂事。
我终于放弃了挣扎,认命地接管了。
好不了的,罗琴安你没想让我们走,我恨恨地看着她,她却露出了笑颜。
彷佛过去了一辈子,终于结束了。
还没来得及和阿沉撒娇,罗琴安就催着我和阿沉上了车,目的地是警察局。
阿沉拿到了身份证,名字是沈令辞。
他的名字和脸给警察局的人带来很大的轰动,办完手续之后警察署署长便走了出来,亲切地和他握手
“沈令辞同道,欢迎回家,A9任务是你捐躯个人,换回A9任务的成功。”
“我这就向组织上报。”
阿沉抿了抿唇,露出了自来到帝京后的第一个笑颜,我也贴心贴腹地为他高兴,可是我溘然想到阿沉和我可能会就此留在帝京。
我溘然转头看向罗琴安,她一脸与有荣焉的表情,见我看过来更是得意地挑了挑眉。
出警局的时候,表面有很多,一见我们出来立时扛着“长枪短炮”上前将我们围住。
“沈令辞师长西席,据传您消逝了三年,叨教这三年您都经历了什么呢?”
“沈令辞师长西席,据传您当初做任务是为了挣军衔娶喜好的女孩。”
“沈令辞师长西席,您阁下的两位女士是谁?”
...
阿沉在一众的围攻陷面不改色,周身气质浑然天成,像极了沈令辞。
我溘然想到,沈令辞便是含着金汤匙终年夜的,本就该沉着矜贵。
罗琴安也是如此,乃至愈甚。
她默默上前,将我隔绝在后,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
“不好意思各位,阿辞重伤后失落忆了,你们这样可未便利他规复影象哦。”
团们顿时发出揶揄的笑声,有认识的惊叫了声“罗小姐”,然后人群散开,为我们让出了一条道。
阿沉没牵我,并着肩大步和罗琴安往前踏去,两人步调同等,看起来配极了。
此后的几天,罗琴安每天都会带着阿沉出去,我想跟上,她却以治耳朵要静养为由把我留在了家里,这样离谱的情由阿沉也相信了,温顺又残酷地让我留在家里。
电视上一天一天地更新着阿沉的轨迹,比如什么“英雄沈令辞回归”,“沈令辞与罗小姐出席X场合”...
这是罗琴安故意的,她在带阿沉逐步以沈令辞的形象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回不去了。
以是你后悔了吗,阿沉,不要我了吗?
本日我自己去检讨了,但没多久我就自己跑了回来。
阿沉回家了,鞋都还没脱就沉声质问我,如连珠炮一样平常地斥责。
我懵懂地看着他,只看出他很生气,却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阿沉显然是创造我没戴助听器,冷嗤一声之后将它找了出来,强硬地塞进了我红肿的耳朵里,强硬地捉住我的臂膀不让我走。
好疼,阿沉,我本日听了你很多新闻,我耳朵疼。
“秦言言,你在想什么?年夜夫投诉你一点都不屈稳,检讨都坚持不了!
”
我害怕,他弄得我很疼,你没陪我的时候他摸我的大腿,摸我的胸,我害怕。
“不要比划了,我看不懂!
”
“秦言言你能不能乖一点,看个病都不能安稳看,你耳朵还想好吗?”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在表面多辛劳,你的耳朵要很多钱,能不能像安安一样大气点懂事点。”
我比划的手顿住了,眼泪倏地落了下来,可是阿沉没有心疼我了,反而更烦躁,抓着我的手不断收紧。
我比不上罗琴安吗?我小气又爱哭,还是个聋子哑巴。
“回去好不好,我不治耳朵了,我们立时回去,就在镇子里过生平,我不要你的军衔,我要回去。”
我拿脱手机,努力在上面打着字。
“等你耳朵治好再说好吗?”
阿沉眼里闪过心虚,没有对上我的眼睛,而后深情吻了我眼下的痣。
做他的妻子,秦言言,小镇里也好,帝京里也好,就在他身边。
我瞥见远处镜子里自己含泪点了点头。
我还是没有去看年夜夫,小镇终年夜的女孩虽然没读过书,但本能觉得那个年夜夫看病的方法不太对。
于是我上网搜索了一番,原来我只须要植入人工耳蜗。
价钱有点贵,但无需阿沉整日的外出,想到阿沉说的话,我还是以为他有一个不戴助听器的妻子会比较好,于是咬咬牙付了款。
随着网上的操作我在一家很大的医院预约了手术,这几天阿沉都很晚回家,我想和他说话时他总是已经睡着了。
一个人去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也不是很疼,年夜夫也不会摸我。
刚到家门口时,手机里却传来一条简讯,是阿沉发的。
是叫我去的意思吗?
那等会儿我们会一起走路回家,我可以立马就见告他这个好,我可以给他分享我看到的新闻,我可以让他和我一起回小镇吗?
门口开了个小缝,阿沉坐在正中间,看起来闲适又自若,他是沈令辞。
他阁下坐着罗琴安,一点都不是他口中不适辛劳的样子。
“辞哥,听说你有个哑巴女朋友啊?在床上,诶,怎么样啊?”
很明显的侮辱,可是阿沉听完之后却没回嘴。
阁下有有颜色的人杵了杵那个脏言脏语的人。
“安安姐在呢,轮得到那个哑巴做辞哥女朋友,再过几天担保被踹好吗。”
罗琴安面上闪过笑颜,嘴里大方地说着不是,我和阿沉很恩爱,身体却不自觉地朝阿沉凑了过去。
阿沉拿起一根烟往外走,我急急忙忙地要躲开。
“言言,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助听器也不戴。”
手被拽住,我却想立时离开。
“言言你来啦。”
“怎么跟阿辞跟得那么紧呀,我不便是带他认识以前的好朋友嘛,在帝京定居是要找回从前的关系网的吧。”
罗琴安也随着出来了,脸上还挂着得意的笑,后面还随着在包厢里的男人,见到我时都止不住脸上的震荡与八卦。
定居,是真的?
阿沉心虚地点了点头,我将手机短信给阿沉看,他立地就明白了,这是罗琴安搞的鬼,顺势就带着我进了包厢。
“这是我救命恩人,也是我女友,秦安安。”
阿沉不情不愿地向大家先容我,众人顿时起哄,刚才开玩笑的男人站了起来,给我端了一杯酒。
“嫂子,第一次见兄弟们,喝一杯吧?”
我不会饮酒的。
我看向阿沉,他没有说话,瞧着还是有点生气。
“嫂子不喝是看不起我们这群纨绔子弟?”
举着酒的男人有些不耐烦了,他的发言很快也引起了众怒,罗琴安更是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不能让阿沉尴尬,阿沉决定定居在这里了,就好好生活罢。
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末了在阿沉的搀扶下回了家。
“不要随便出门,谁叫你都别来找我。”
我在马桶边吐着,神色发白,阿沉却丢下来一张纸条。
知道了,不会了。
可是阿沉我想回家了,这里好无聊。
不出门的日子总是很无聊,只能看阿沉一次又一次地涌如今电视里,然后带着一身的冷肃回家,我们不再说话。
你到底规复影象了吗,阿沉?规复了的话,我就不会陪你啦,我不愿意让你尴尬的。
“言言啊,帝京好不好玩呀,什么时候回镇子。”
微信里,王婶给我发来短信。
“你和小沉不在,我这喷鼻香椿都没人吃啦,专门给你种的。”
王婶和爷爷一起抚养我终年夜,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阿沉没陵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