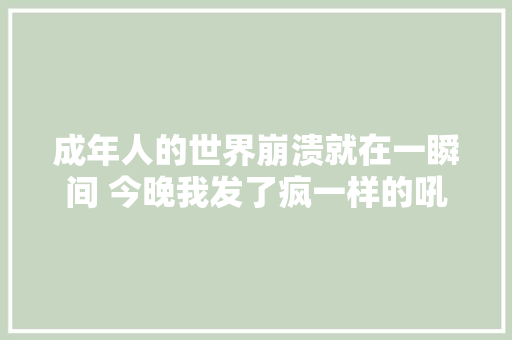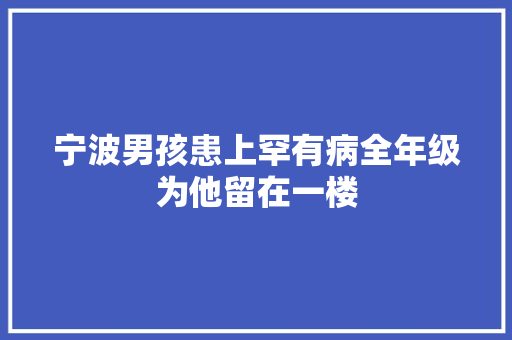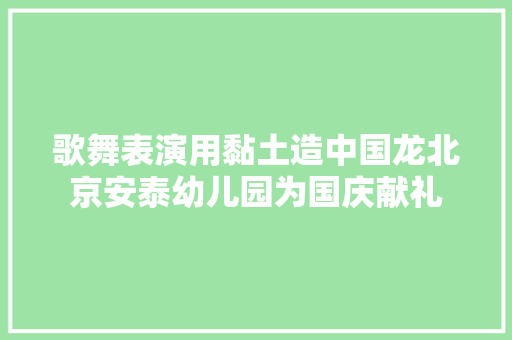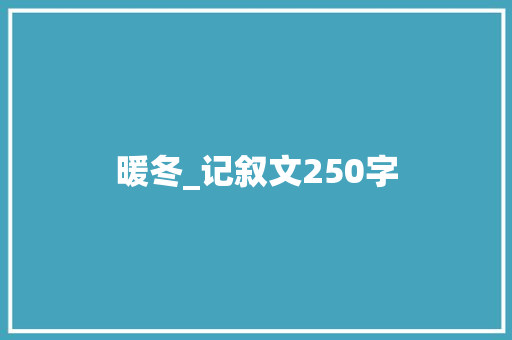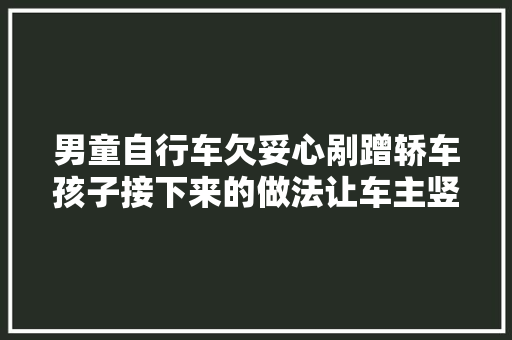这首歌,叫《心伤的打工者》。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听到第三句时,我便眼已润,接着一句更是让我泪线崩断,甚至于不能自控到曲终。
听完歌曲,我的大脑风云翻卷,那无奈的悲怆,那离去的酸楚,那断肠的哭泣,形成了赶不跑的画面,跳来闪去,令我难以释怀。

我找来纸笔,要把这歌词记下来。可我仍旧跳不出感情,再一听那曲调,便鼻子酸酸,双眼又模糊起来。
歌词写道:
过完了春节整顿行李,
离开了家乡要去外地。
孩子拉着我手在哭泣,
哭喊着爸爸你不要去。
叫一声孩子你别哭泣,
好好地听话就待在家里,
在学校读书专心地学习,
等到了年底我回来团圆。
啊!
我的孩子呀,
妈妈生病你照顾她,
六岁你就要当家,
孩子真是难为你了,
哎嗨嗨......!
有家的地方没有工打,
打工的地方我却没有家。
他乡容不了我的灵魂啊!
故乡安置不了我的肉身啊!
啊!
我的命运呀,
注定生平把工打呀!
为了生活没办法,
谁又乐意离开家,
啊!
我的人生呀!
长年累月把工打呀!
挣不到钱顾不了家,
我咋混得那么差。
挣不到钱,顾不了家,
我咋混得那么差,
哎嗨嗨......
这歌词并非文采飞扬,但却是活生生的真实。歌词的标点是我加的。说实在的,加标点时我很是伤脑筋,以为如何加,也难以表达歌曲的内涵和情绪。
这首歌,是一位农人工改编演唱的。他叫大勇,初中学历,在杭州一木制工厂打工。主持人说,一个初中生能写出这么好的歌词,真不大略。我以为,那哪是什么写出的歌词,那分明是他无数次与家人短暂相聚而又分离的悲鸣,是他那客居他乡思念家人而又重聚的喜泣!
是的,正是这样。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想起写歌呢?”他说:“小孩在老家,常常给我打电话,问爸爸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让孩子大了往后明白父母为什么不在身边,……”以是,这就有了那一次次的歌词里的场景——“过完了春节整顿行李,离开了家乡要去外地,孩子拉着我手在哭泣,哭喊着爸爸你不要去。”孩子拉手扯衣、哭哭啼啼,爸爸自然要安慰要叮嘱,“叫一声孩子你别哭泣,好好地听话就待在家里,在学校读书专心地学习,等到了年底我回来团圆。”这不正是他真实的历经吗?是,是印在贰心里的一次次离去的直白。
《今日热点》的主持人讲,这首歌一经播出,便走红网络,一夜间浏览量超过千万。
“这首歌为什么能走红呢?”他说,“可能是很多人有共同的经历吧!
”
这话是没错的。但想想也不全是,如果这经历是安平和愉悦的,会有一夜千万级的浏览量吗?恐怕未必。以是,这就绝不仅仅是共同的经历所致。
那是什么呢?我想,是歌曲拨动了那无数流落人受了伤的心弦。一幕幕的别离,妻子含情目送,孩子依依不舍。客居他乡的艰辛,晚间的孤影,无聊和凄楚。一曲悲鸣飘来,那不犹如泄了闸的江水?!
上亿的打工者啊!
别妻离子的心伤,别土离乡的无奈,伴随着凄婉的波折衷高亢的喊诉,也就变成了传播的网流。
我《走过六里桥》,见过那等待雇佣的打工者;我在避雨的大厦下,见过那在瓢泼大雨中骑行的外卖小哥;我在小区里空旷的地方,见过那几十人不等的保安军队。他们,是一个个在城市里拼搏的农人。在寒风中等待,在大雨中疾行,在清晨入耳训,他们心里清楚,“小孩哪哪都要费钱”,“挣不到钱就顾不了家呀”!
这首歌,那略带西北方言的发音,那略带西北风格的曲调,更是把农人工的凄苦表达的令民气碎。一声“啊,哦(我)的孩子呀!
”叫你随着他的呼唤淌下泪珠;一声“妈妈生病你照顾她,六岁你就要当家,孩子真是难为你了,哎嗨嗨......!
”这作为父亲的悲怆和爱怜,又叫人更加地泪眼连连。“有家的地方没有工打,打工的地方我却没有家。他乡容不了我的灵魂啊!
故乡安置不了我的肉身啊!
”再把农人工的内心苦闷和彷徨呈现在你面前。这与其说是歌,倒不如说是那农人工从心底飞出的哭诉。
这首歌,是成功的。由于他捉住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
这首歌,也令人开思,使我们更加严明地思考 “三农”问题。
稽核有知:农人,主体已成为农人工,这是广大屯子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人工,是一个相称量级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屯子集体所有制改革形成的一个分外群体,也是天下上独一无二的群体。屯子,地分了,一家一户,种地用不了那么多人力,也不赢利,而在屯子搞副业搞企业又不具备条件,富余的农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外出打工。一个打工者便是一个家庭,险些家家都有外出打工的,这就形成了广大屯子民生的一个基准面。
而外出打工,对付农人工来说,便是这样的抵牾状态:有家的地方没有工打,打工的地方却没有家;他乡容不了灵魂,故乡却安置不了肉身。
青壮年外出打工了,村落里剩下的基本便是老人、女人、残疾人和无法带走的小孩子。由此,不同程度的空心化屯子产生了,远处望去,村落里一栋栋像样的屋子,走进村落里却十屋七八空。
地,留给了老人和女人,种好种坏不主要,反正也不赢利,有一搭无一搭,无所谓。庄稼人,最不忍心的便是地荒着,那就种些树,留一点地种些口粮自己吃。
孩子们走了,村落庄也就少有了昔日的生气。接着是学校富余了,那就小村落的学校并到大村落去,好的教诲资源集中到了城镇,屯子的教诲也就随之失落去了昔日的热闹景象。怎么办,再亏不能亏孩子,要让孩子去城镇上学,将来好奔个好出路。于是就贷款交首付,然后是冒死挣钱分期付款,从此孩子父母天各一方。钱挣到挣不到,因人而异,可失落去了父母陪伴的孩子,学习不达标,生理问题多,教诲和发展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我打仗过不少打工者,他们很苦闷,也在时时拷问自己:“啊!
我的命运呀,注定生平把工打呀!
为了生活没办法,谁又乐意离开家?啊!
我的人生呀!
长年累月把工打呀!
挣不到钱顾不了家,我咋混得那么差。挣不到钱,顾不了家,我咋混得那么差”。
严明的“三农”问题,关乎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万世基业。
问题如何消化?出路又何在?无疑,振兴村落庄是光明大道。而振兴村落庄,最可借鉴的历史履历,是新中国的集体化道路。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等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赤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