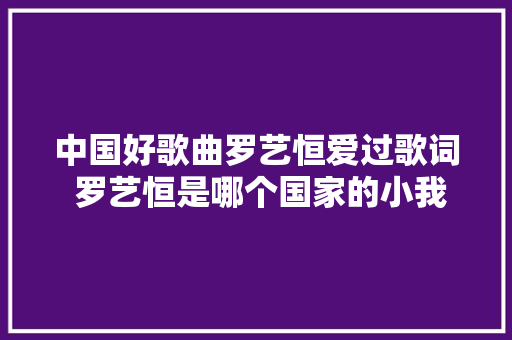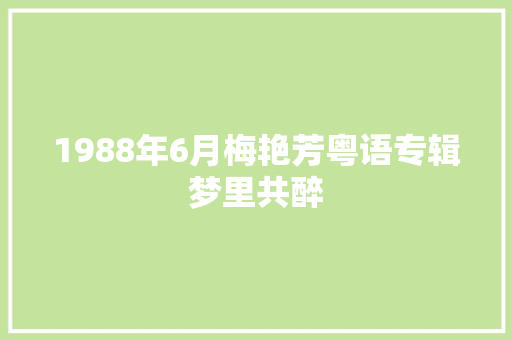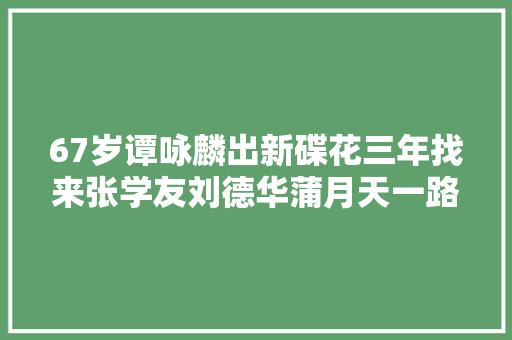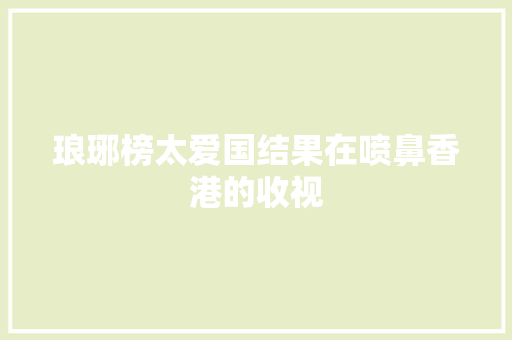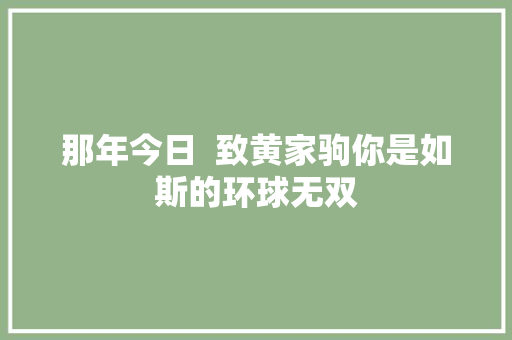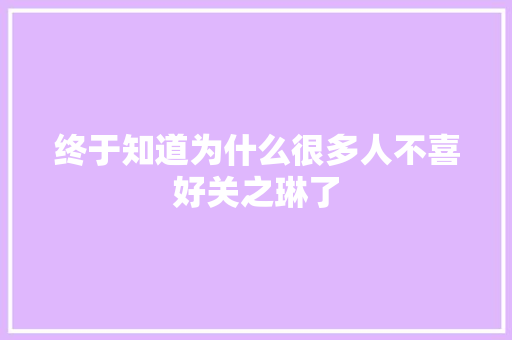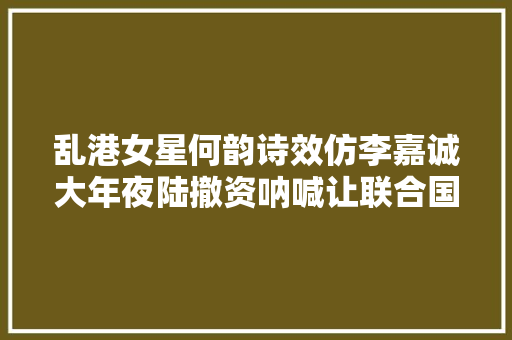今日连续分享黄霑2003年的博士论文:《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90年代的港歌像是都邑里的大漠孤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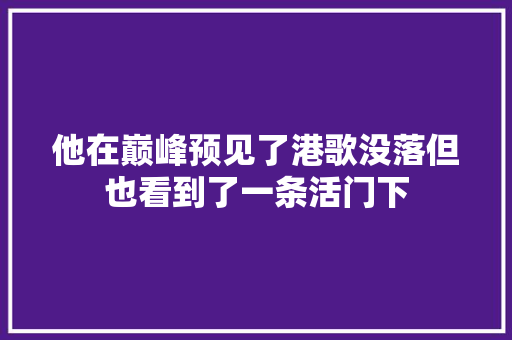
顾嘉辉黄霑,是金戈铁马,
林振强潘伟源,是羌笛红叶。
明明弹丸之地,音乐里却繁殖着一种与尘世苍凉共舞的伟大。
黄霑说,
那是由于粤语盛行音乐文化本来便是海纳百川的结果。
黄霑:《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不过,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便是能衰中见盛,盛盈思衰。
当红磡体育馆的演唱会场次和不雅观众人数年年攀升;
当90年代中期喷鼻香港音乐光碟年产一度达到1700万张,零售额达18亿港币;
当新一代天王天后与歌神校长的歌迷已然遍及环球……
黄霑依然在一片欣欣向荣中看到了束缚喷鼻香港盛行音告成长的“茧房”。
黄霑:《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夜夜笙歌式的内耗
不管喜和悲,卡拉永久OK。
幻梦都破碎,卡拉也会OK。
1990年的潘源良写下这首《卡拉永久OK》时,彷佛就已经预示了卡拉OK大潮对付音乐创作黄金时期的闭幕。
在K歌房里,主要的不是音乐本身,而是能不能让客人尽兴。人们拿着麦克风享受的,是低配版聚光灯下仿照出的“歌星”幻象,是借着歌词宣泄的感情快感……
1988年,全港第一家全卡拉OK酒廊"大亨廊"在铜锣湾开张。酒廊式的卡拉OK只有一个舞台,要上去唱歌须要先写好点歌小纸条,再排队等着上台。
港剧《大时期》里酒廊K歌名场面:小犹太和龙纪文共歌一曲《似是故人来》
其后的1991年,大亨廊的老板又率先引入了日本K歌房的模式。Big Echo一落地喷鼻香港,立时就成为喷鼻香港人除了家和公司之外的“第三空间”。有的人趁着午饭韶光来唱个十几分钟,晚高下班再连续来高歌;有的人乐意排上四个小时的长龙,只为求得躲进小屋自成一统的梦幻时候……
BIG ECHO:90年代初便进入喷鼻香港的有名日式K歌连锁店
卡拉OK家当乃至一度与喷鼻香港乐坛形成唇齿相依的态势。
新城劲爆颁奖礼从1996年起开始设立“卡拉OK歌曲大奖”;
Big Echo举办的大型歌唱比赛为乐坛挖掘新人,并且成功地为正东唱片运送了容祖儿;
用轰炸式的宣扬手段在店里反复播放《好心分离》,直至终极街知巷闻、歌手捧得奖杯……
人潮的猖獗涌动,很难不让成本动心。
卡拉OK越开越多,K歌房的老板们为了招揽客户,绝不惜啬地向唱片公司支付着高昂的版权用度。1998年,苏永康的一曲《越吻越伤心》被Big Echo的对家“加州红”以40万港元的价格买断了“独家试唱权”;2000年,Neway用5000万直接买下了英皇所有歌曲的版权……K歌行业的挥霍无度让深陷盗版碟困局的唱片公司创造了新的打破口,音乐创作的天平由此开始倾斜。
喷鼻香港K歌家当挥霍无度买断“独家试唱”的竞争模式,始于苏永康的爆款情歌《越吻越伤心》
琅琅上口的大路情歌成为唱片公司更乐意费钱制作和推广的产品。
此消彼长,那些更具备引领浸染和音乐性的创作希望很随意马虎就被K歌带来的钱潮所淹没。
黄霑:《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夜夜笙歌式的内耗,致使音乐创作、乃至歌曲的演绎办法都流于千篇一律。
K歌房里的流量港歌,逐渐不复惊艳;
而在K歌房练出来的新偶像,也逐步失落去曾经那些巨星们的独特风貌。
于是,在进入K歌热潮的第十个年头里,林夕写下了那首《K歌之王》:
/ 还能凭什么 拥抱若未令你愉快
/ 便宜地唱出 写在情歌的性感
/ 还能凭什么 假如爱不可冲动人
/ 俗套的歌词 鞭策你恻隐
从1990年的《卡拉永久OK》,到2000年的《K歌之王》,这席卷10年的K歌热潮下,人们倒是都会唱歌了,却彷佛不知道该怎么听歌了……
一场决一死战却注定失落败的内卷
谁能想到,“原创”这个看上去闪闪发光的词会成为压垮喷鼻香港乐坛黄金时期的一根稻草?
黄霑:《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1995年喷鼻香港商业电台发起的”原创歌运动“被很多人诟病为港歌黄金时期由盛入衰的加速器。
鼓励本土原创本应是好事一桩,可为何连黄霑这种喷鼻香港原创的基石人物,都对此颇有微词呢?
不得不承认,港歌的发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接改编欧美日的成熟盛行曲。80年人们对付中文盛行歌曲的需求日趋飞腾,”日曲粤词“的模式高效地顶住了这股彭湃的音乐消费潮流。
西城秀树、近藤真彦的作品引领日曲粤词改编热
媒体整理的部分“日曲粤词”代表作
但就像卡拉OK热潮异化了音乐创作家当一样,只管看上去繁荣一片,星光熠熠,但本土作曲、编创能力不敷的硬伤,依旧是一个潜在且正逐渐扩大的隐患。
此时,有个狠角色打算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她便是如今被不少港歌迷诟病的”中文歌运动“、”原创歌运动“的发起人,俞琤。
喷鼻香港盛行音乐“原创歌运动”幕后推手:俞琤
俞琤并非专业音乐人出身,而是作为电台DJ唱片骑士出道。
1982年,她发掘了15岁的林忆莲,成为喷鼻香港商业二台的兼职DJ;
同年她成为钟楚红的经理人,涉足电影圈;
1985年,俞琤力挽狂澜,将刚刚举办三年、根基不稳、影响力欠佳的喷鼻香港电影金像奖从边缘拉回,梅艳芳也由此有机会斩获1985年最佳女配;
1988年重返商台后,创立了喷鼻香港盛行乐坛四大颁奖礼当中含金量最高的叱咤乐坛盛行榜;创造了”拉阔音乐会“观点,以真唱、现场乐队伴奏、无伴舞的形式,力争还盛行音乐演出以本真,而非包装之下的偶像崇拜;
她是8090年代天王天后们直接或间接的幕后推手;与林燕妮、施南生、狄娜并称喷鼻香江才女;和吴君如、刘嘉玲、周迅互为心腹……
便是这样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空想主义大佬,于1988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在喷鼻香港商业电台先后推出”中文歌运动“和”原创歌运动“,全面贯彻俞琤”以港人利益为最大依归“的办台宗旨。
特殊是1995年的”原创歌运动“,商业电台对付”非港生“的歌曲进行了“零容忍”的全面封杀。商业二台,也便是叱咤903,全面转型为“全中文原创歌频率”。
1995年叱吒903的节目单
这环境,对付盛行音乐需求兴旺的喷鼻香港音乐市场来说,就像一个本来习气一日三餐加下午茶的人,现在让他改成一日两顿且过午不食,那两顿还不能去餐馆或点外卖,而是要自己动手做……
但问题是,自己做,彷佛吃不饱……
用一个数据就能一窥1995年以前能喂饱音乐刚需的量:
当红歌手,一年正常的发片量是在三到四张专辑旁边,八到九张的也并非罕见……这个发片频率,只能靠国际唱片公司在自己的环球版权曲库中找歌,再依赖重新填词翻唱来实现高效支撑。
而俞琤的原创歌运动,险些封杀了唱片公司这种“一鱼多吃”的模式,高效野蛮的生产模式被遏制,但也对当时喷鼻香港的本土原创实力显得过于自傲。
黄霑:《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在喷鼻香港市场赚不到钱的唱片巨子,开始将布局重心转向东面的那座小岛,台湾。俞琤鼓励喷鼻香港本土原创的空想主义,由此开始初露“好心办坏事”的端倪。
1995年前后,国际唱片巨子开始在台湾大刀阔斧地展开并购操持。
EMI百代在台湾设立了种子音乐公司,签下了张信哲,进而眼力狠辣地收购了在第五届金曲奖上狂揽十四项桂冠的点将唱片,得优客李林(及单飞后的林志炫)、张清芳、蔡琴、伍思凯等宝藏级唱将;
宝丽金收购福茂唱片,觅得一对“金童玉女”范晓萱、王力宏;
华纳依赖飞碟唱片,为林忆莲、林子祥、叶倩文等一众喷鼻香港歌手的国语唱片拓宽了两岸三地的中文市场……
台湾盛行音乐家当由于本身就有着原创民谣的深厚根本,创作题材丰沛,再加上措辞文化与大陆相通,国际唱片成本将台湾履历作为开拓大陆市场宝贵考试测验,台湾由此取代喷鼻香港成为全体华语盛行音乐的核心产地。
港歌的黄金时期,就这样,被台湾市场“截胡”。
声生不息,抑或是曲高和寡?上个世纪港歌的黄金时期,本便是来自上海的时期曲、传统粤剧、欧美日工业化流程制作的凑集化产物,是全体喷鼻香港社会自我认知、找到自傲后,自下而上的平民之声。
而到了90年代,这种“平民之声”开始陷入极致本土主义、自满感情时,音乐题材的想象力就开始收窄,加上专业创作力量与大规模市场需求的不对等,其原创实力不再足以喂饱日益清醒的华语音乐市场。
面对港歌的萧瑟前景,2003年的黄霑在他的论文结尾处,为港歌指出了这样的出路:
进入普通话市场。
黄霑:《粤语盛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喷鼻香港盛行音乐研究(1949-1997)》
港歌黄金时期留下来的那批最为宝贵的财富,不仅仅是字正腔圆的粤语发音,而是对付都邑心情、平民时期、小人物生存进取精神细致刻画的能力;是融贯中西的家当整合能力;是对精良音乐作品的鉴赏和传播能力……
这些才是把华语盛行音乐蛋糕做大时,最须要汲取的养分。
“辉黄组合”共谱的《强人》:看世中得失落,只记共你当年,曾经相识过
港歌,还没到办法终生造诣奖的时候。声生不息,不是曲高和寡,也不是偏安一隅。
是成为当代唱入民气的城市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