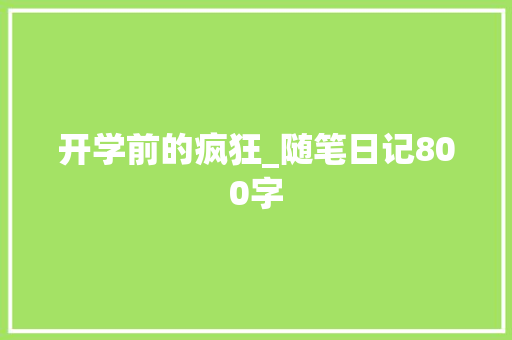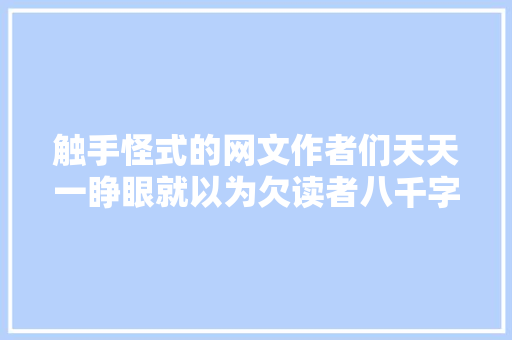当风注意灌输帆时,船会走。
以一条帆船为家,只靠风与帆的浸染——历时504天、航行28000海里,11月15日,54岁的翟墨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一直靠帆船环航北冰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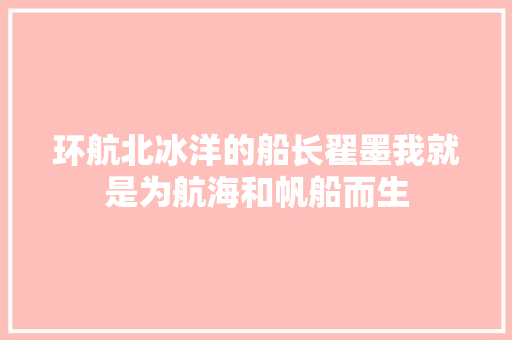
翟墨留一头长发,体格强壮,皮肤黝黑,符合人们对付航海家的想象。十余年前的2007年,他也曾发起并完成了一次帆船环球航行。此外,他还经历过南太平洋、中国海疆等多次帆船航海。
翟墨欣赏歌词“把屋子建在海上,我只有生平流落。”自认为航海与帆船而生。
那么,他的帆船航海体验是什么样的?以下是他的讲述:
环航北冰洋是最险象环生的一次航行
2021年6月30日,我和两名船员从上海杨浦滨江秦皇岛路码头启航,操持用4个月的韶光环航北冰洋。
我们的船叫“环球通号”,长25米,宽7米,带四面船帆,内部条件不错,有专门的驾驶室、客厅、寝室与厨房,只是厨房的锅碗瓢盆都要用绳子系着,防止在遇浪颠簸时摔得粉碎。随船带有斧头、医药箱、旗子暗记枪、防寒睡袋、卫星通讯设备等,也有书本与绘画工具。粮食多是煎饼、牦牛肉干等干货,带足了一年半的存量,那么在景象变故、船只被冻在北冰洋长久不能动弹时,我们不至于受饿。也会带些西红柿、喷鼻香蕉、土豆等常见果蔬,但航行中船只常会颠簸倾斜,很少有生火做饭的条件。
我卖力掌舵,出上海后,船只经东海、日本海入太平洋。2021年7月24日,我们驶过白令海峡,正式进入北极圈内。
这是一片俏丽但可怖的区域,天色灰暗,一望无际,50余海里的浮冰区像雷区一样,随时有冰面碰擦船体的风险。且愈往北,浮冰的体积愈大,等到过了格陵兰岛,冰山涌现了,像摩天算夜楼一样高耸。在不少关卡处,船只只能贴冰而行。
我的两位船员,一个来自厦门,一个来自俄罗斯,轮值12小时的班,替我在船头瞭望浮冰与冰山。而作为船长与舵手,在船上,我只能睡囫囵觉,眯不过两三小时,就要起来察看舵位与船只方向。在浮冰密集的地方,船速最低只有1节,也便是每小时1.85公里,比走路还慢。
也发生过几次危急:2021年8月25日,在格陵兰岛东岸,船只碰着了一次极地气旋,风速达十级以上,四面帆中的一壁没有及时收起,好在我急速将船帆绳索砍断,免有灌风翻船的危险。2021年9月中旬,同样在格陵兰岛附近,因与水底冰层相撞,船身像击鼓一样震撼,龙骨处发生渗水,所幸被自动排水系统化解。自进入北纬75度以上起,由于地球磁场的滋扰,船上的电子仪器通通失落灵,船只在目测估算中前行了三天,有惊无险。总结来说,这是我航海生涯中最险象环生的一次航行,期间,我与船员们当心翼翼、抱着不去世即是万幸的想法。
2021年10月下旬,我们已完成北冰洋环航,但景象变革超出预期,原定返航上海的通道已被冰封,我们只好连续往西,进入加拿大与美国海疆。这一绕道,将归航中国的日期延后了将近一年,直到2022年8月,我们才经古巴及巴拿马运河往上海驶去。
2022年11月15日,历时504天后,我驾驶着环球通号抵达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央码头,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实际上,我环航北冰洋的心愿早就结下。2002年,我在荷兰结识了一位叫做汉克的航海家,他年近七十,自称已驾帆船环球五圈半,唯独被北冰洋绊住脚,他的船在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交界处被牢牢冻住近一年,开春时,在俄罗斯破冰船的解围下才得脱身,无功而返。
听汉克回顾这起失落败经历时,我已有了两年旁边的航海履历,顿时跃跃欲试,认为北冰洋环航是我的航海奇迹中终要完成的一个梦想。
翟墨(右)与船员在北冰洋上,水天一色。受访者供图
这个蓝色星球就属于我
1968年11月,我出生在山东泰安的一个矿工家庭。在这样一座要地本地城市成长,我一度对海没有任何观点。
小时候,我随着父亲去山里的小河沟钓鱼,有时会在一旁用树枝和石块描摹父亲的样子。父亲便给我买来颜料和画板,送我去学绘画。
后来,我考上了山东工艺美院,逐渐养成了“画抽象的”风格。很多年后,当我独清闲大洋之上盯着海面起伏时,我会想到莫奈的《日出》、透纳的《狂风雨来临前的海景》。
毕业后,我先是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做起了拍照,又接着单干拍广告、拍实验电影,终极还是回归了绘画的老本行。
2000年,我去新西兰奥克兰办画展,创造那里是隧道的帆船之都,均匀每三人就有一人拥有一艘帆船。到了双休日,海面上的帆船一贯延伸到天涯线去。奥克兰的海是藏蓝色的,沙滩也是深色的;晴天时,海上的云触手可及,风景实在好。
不久后,我帮忙当地的朋友拍摄一部航海干系的记录片,认识了一位叫戴维的挪威航海家。戴维也是70岁的样子,面部线条粗糙,棱角分明,颇具海明威的气质。他说他为躲避台风季,暂歇在奥克兰,而此前他已驾驶帆船绕地球一点五圈了。
我十分惊奇,问他,航海是否须要执照?他说不须要,只要有一条船,乃至不用提前办理签证,我想去哪里都可以,在国外停靠上岸也只需大略办理通关手续。
要知道,地球上70%的面积被海洋覆盖。这意味着,只要我有一条船,这个蓝色星球就属于我。这强烈地吸引了我——我要自由地在海上航行,自由地穿梭于大洋之中。
因此,结束这场发言后,我急速请戴维为我挑一艘价格便宜、能够一人驾驶的帆船。一个月后,我们在奥克兰附近的一座小岛上找到了得当的卖家,我以折合公民币不到3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条船龄20余年的帆船。这险些是我当时所有的积蓄。
那条船长7米,宽不到2米,我为它取名“白云号”。
从小岛回奥克兰有年夜约五小时的航程,在此期间,原船主教我掌舵、升帆、调帆等航海基本技能。近岸时,我已经可以自行控船了。
而后我将奥克兰的出租屋退租,带着少许行李搬上了白云号。船舱空间不到十平方米,只能放一张折叠沙发、一个马桶和少许存粮。但这条船便是我的家了。
彼时,我对真正的航海尚一知半解,但已经按捺不住了。购船不到二十天,我就启航环游了新西兰北岛,又顺势进入南太平洋。我一边旅行一边连续自学航海,从指南针、航海图的解读,到判断风向、潮流、洋流等,不一而足。
磨练来得很快。当我行船到汤加附近海疆时,突遇低气压景象,下大雨,刮十几级大风,浪打到十几米高,船体倾斜有35至45度,像过山车一样颠簸。舱里的碗盆打碎了,我也跌了一大跤,把脚底板划了道口子。
这场风暴持续了两天,我自己缝了伤口,操作着船勉强前行,心想,我为什么要买这艘破船?如果我能安然地漂到一个地方,我就再也不航海了。
然而,在雨过天晴后的第一个黎明,海平线上涌现第一道曙光时,我仍旧忍不住欢呼,那种景致盖过统统壮丽的绘画。退缩的想法消逝殆尽。我又马一直蹄地往图瓦卢、塔希提岛等南太平洋各岛去,走走歇歇一年多,才回到中国。
从此,我的航海生活再无法停滞。在环航北冰洋以前,我已完成中国海疆、环球等数次航行。
2008年,翟墨在太平洋上航行。受访者供图
“把屋子建在海上”
航海给人什么样的体会?
在船上,大海是一种幽幽的腥味,是耳边模糊约约的声响。在北纬和南纬15至30度之间的海疆,风向最稳定,帆船航行起来最让民气驰憧憬。
多数时候,我喜好一个人航行,但很少感到孤独——一个人航海时要做的事情很多,保持专注,不雅观察风与海水的变革,险些24小时掌舵;我第一艘船“白云号”配着一支手工舵,我不得不在睡觉时用绳子将它拴在腿上,好保持航向。我的腰部也全天系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船体上,一旦落水,我可以顺着绳子爬回船上。
帆船上不宜沐浴,只有下雨天能接水冲冲身子,若用未经处理的海水冲洗,皮肤会黏腻。受伤更是家常便饭,骨折及暴露性伤口我都经历过。娱乐也很有限,除了安歇与开船外,我偶尔钓鱼,时常画些画。海每每是创作的主题。
2015年,翟墨驾船在亚丁湾海疆航行。受访者供图
小时候,我曾依托想象描述过大海,画上朵朵白云、海鸥飞行,还有高悬的太阳。真正出海后,我创造,大海远比这要丰富许多。比方说,南太平洋的深海是灰色的,近海、浅海则是碧色;南太平洋多有飞鱼出没,就像电影里那样,它们会成群结队地飞上我的小船。在北极圈那可怖的浮冰区里,我曾见到过聚拢于冰面的海豹、海象,有海豚在船舷边游过,还有鲸鱼在离船极近的位置喷出水柱。而当我在西伯利亚以北的喀拉海区域航行一周,竟没有见到一块浮冰——这在过去是绝不可想象的,正是在途中,我创造,环球变暖的效应正逐日加剧。
在这各类精神力量的加持下,航海所受的肉体的苦难已显得不那么主要了。
我2010年景了家,曾带爱人在日照与青岛之间航海,她晕船晕得厉害,自认不适船上生活,却不反对我航海。也有赖于科技,除了在北纬75度以上时断绝旗子暗记,别的的航海途中,我都能通过卫星通讯与家人保持联结。
目前,我的环球通号正停靠在上海白莲泾码头,我也仍在船上居住。我在陆地上没有房产,曾买卖过五艘帆船,现在的这艘环球通号上,压着险些我的全部积蓄。我操持,明年10月,独身驾驶环球通号去南极洲,用7个月旁边的韶光完成南极洲的环航。
“把屋子建在海上,我只有生平流落。”这是我很有体会的一句歌词。在海洋之上,我永久能觉得到自由的快乐。
新京报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正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