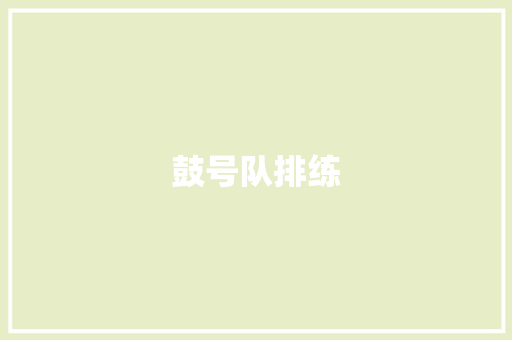儿时从记事起,常听邻居奶奶、大伯讲故事,但大多是似懂非懂,一些鬼、神仙的传说故事,潜入影象中,胆怯和心悸侵蚀童年的心灵,每当夜晚,这些莫名的、其状凶神恶煞的阎王鬼怪,每每在脑海中时隐时现。
后来上学了,也离开了自己的村落庄,学校所在地为一古集市,十天两次逢集。一次偶尔经由集市中的一片洼地,看到许多大人或坐或站,在悄悄地听大鼓书。容身听了一会,竟然入了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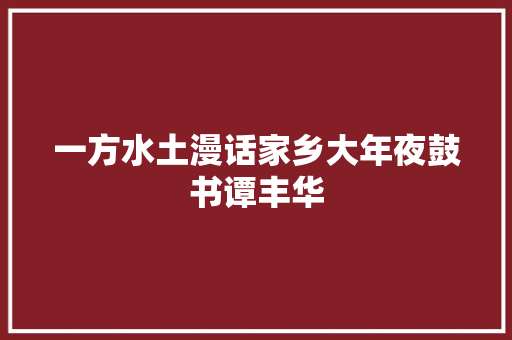
从此往后,有时放午学和同学就会结伴来到大鼓场,收零钱的帮人,免收孩子们的钱,这也催发我听大鼓书的兴趣。说书艺人喜逐颜开,让人听了一段还想听下段,为此我有时闹过迟到、旷课之事。老师的罚站批评也时有发生。回忆起来,自己也感到当时的无奈。文化贫瘠的年代里,小孩子一本小人书传遍全体校园,有时翻到残破缺页的程度,仍爱不释手。听听评书、扬琴、大鼓书,也算是当时最大的精神享受。
空隙时翻阅有关资料,对邳州的大鼓书多了一些理解,从而也增长了对家乡传统文化沦丧的担忧。
大鼓书紧张流传于邳州民间。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间,而兴盛于民国至建国初期。
据《邳县文史资料》第七辑,周绍俊文章记述,当时邳城、土山及大运河两岸,有一位云游羽士,怀抱鱼鼓,手执简板,带领十大弟子走村落串户唱道情,筹募捐款修缮寺院。他们所唱的曲调类似于后来的大鼓书,大鼓书的说唱形式是从道情中传承演化而来。
清乾隆末年,古邳有一名秀才夏大林,怀才不遇屡试不中,他便拜在十大弟子门放学艺。为了方便说唱,他改用了简板,板前端安了一个铜钩,便于拾取施舍泉币。后来他也立了门户,也收了十大弟子。这十大弟子中仅有三人成名。形成了邳州的三大门户,各门户竞争听众十分激烈,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书者,鱼鼓改成了大牛皮鼓,木简板改用铁犁铧,随着道具的改变,唱腔也变得高亢冲动大方,耐听。就此在古老的邳州大地上就涌现了犁铧大鼓。这种艺术形式随之植根于集市街头,村落庄民间。
铁犁铧用起来既重又不雅观观,往后又改用了钢板或铜板。鼓的造型也演化为扁形的大鼓。
以我个认识,说大鼓艺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艺人本身有些文学功底,善于咬文嚼字,说故事解经典,面对听众滚滚不停,腹中有说不完的故事,这类艺人常赶四集,在街市上有影响力、有市场。每每他支好大鼓咚咚咚一敲,听者大多慕名而来,纷纭而至。
小时候常听大人闲聊时议论,李保全博采众长,、潜心研讨,他的大鼓独俱特色。于这天日愿望,哪天能亲自看到这名艺人,聆听他的说唱。一次古庙会上,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李保全。只见他坐定支好大鼓咚咚一敲,那边艺人身边已空无一人。李保全却是气度非凡,他的唱腔憨实粗犷而不低,昂扬抑扬,欢畅而不乱,悲而不哀。唱到快板时,左手执板,右手叉腰,小帽子歪扣在脑尖上,小鼓棒插在脑后,一口气可唱十多分钟;他的讲解评说更是惟妙惟肖,人物形象在他的模拟下鲜活逼真,如在面前。讲到动情处,哀哀戚戚,肝肠寸断,令人潸然泪下。一次,他讲到《月唐演义》故事中,刀下留人这一情节时,故弄悬虚,刀举起后唱了一个下午,没见分晓,罢集了,来个且听下回分解,收起鼓架,散场了。
一名听书的老太太,回家后因未听到结局,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几天茶饭不思。女儿守在床前问娘,什么苦处折磨您?当老娘把街上听书的细节一说,女儿笑了,“娘,郭子仪已经救下那个女孩,她没事了。”“闺女,真的!
赶紧给娘做饭,我要用饭。”故事不知真假,通过此事可以解释,李保全说书之高明,致听者沉浸在故事情节之中、达到走火入魔程度。
另一类鼓书艺人,没多少文化,名气不大。无论从说唱演出形式上稍逊前者,在集市上没有多大市场,为了端这个饭碗,混个门派头衔,常常瞄准村落庄,唱晚场。
夏日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回到家里。微风驱散了白天的酷热,大人孩子纷纭拿着草蓆,蓑衣等来到十字路口这片空地,享受夏夜的安逸。一个《孟丽君》的故事,吸引了全村落男女老幼。已经唱了几天了,大家还是兴趣盎然,乐此不彼。
讲到动情处,朦胧的夜色中,可以看到女人停滞手中的扇子,轻轻抹眼泪;男人此时屏住了呼吸,悄悄地等待;老爷爷们的烟袋彷佛也忽明忽暗。显然,鼓书艺人的说唱夺走了大家的心。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视、电话、各种音响电器走进平凡百姓家,曾经盛行于民间,古老的鼓书说唱艺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屯子集市上唱大鼓者已绝迹,来去匆匆的赶集人多为买卖购物者,物质至上的本日,集市上再也看不到休闲人;村落庄的夜晚人们都躲在家中看电视。一些村落庄艺人,也弃艺到外地打工,熟习的鼓书说唱艺术仅留存在收音机里。
一次早上晨练,老远听到鼓声阵阵,一位操着苏北口音的艺人正在唱大鼓。我循声近前,晨曦中,电瓶车上放着收音机,一位老者年约古稀,一个人悄悄守在收音机旁,他沉浸在鼓书的说唱中,痴情的样子,像是在听,也像在沉思,我的心为之一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古老的鼓书艺术魅力,已经渗透到家村落夫的骨子里,影响一代又一代邳州人,它瓜瓞绵绵,生生不息。时期将这门民间艺术塞进我们的行囊里。这样,我们每向前行走一步,都会以为历史的负重。同时,我也衷心祝愿家乡这块地皮上呈现出更多的鼓书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