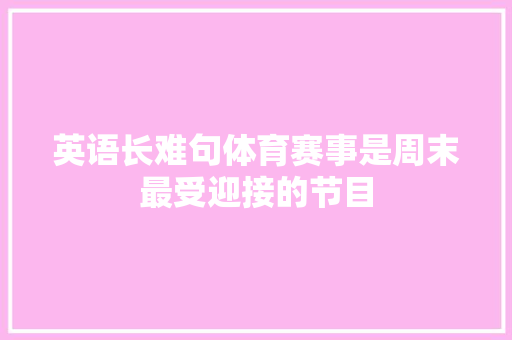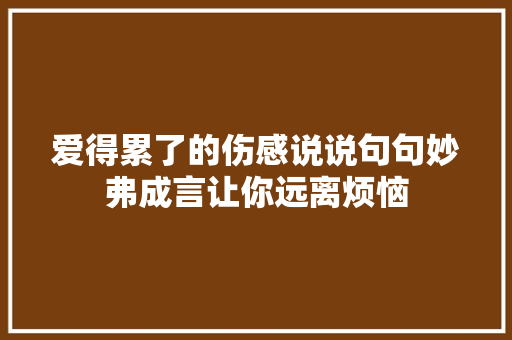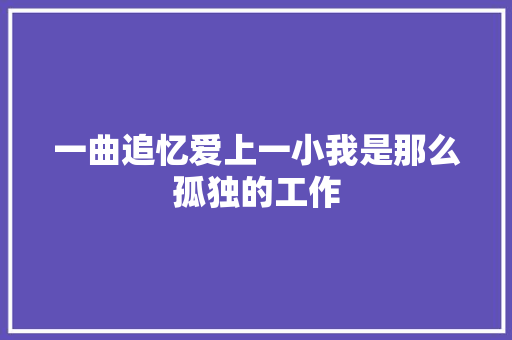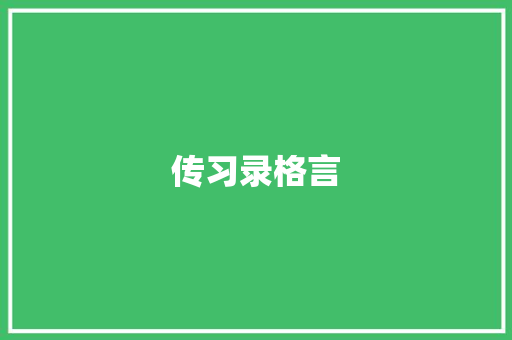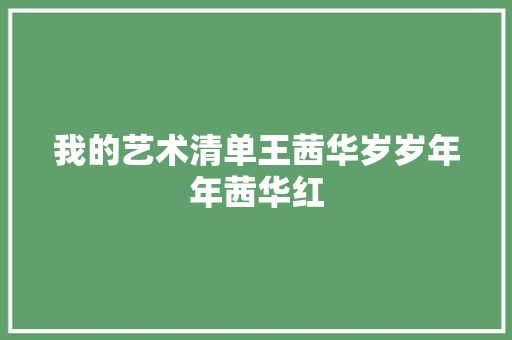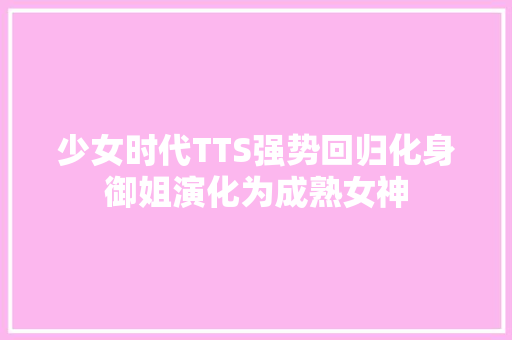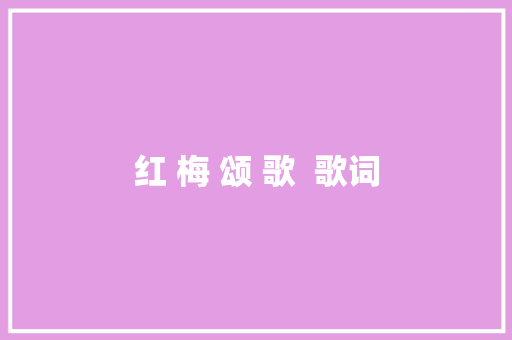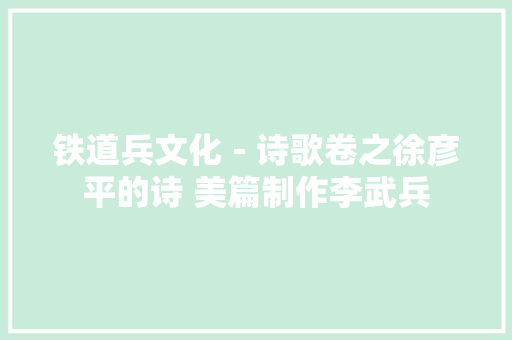刚还想说今年《乐夏》有点平淡,急速就被这一波朋友圈刷屏洗礼了。
一个个都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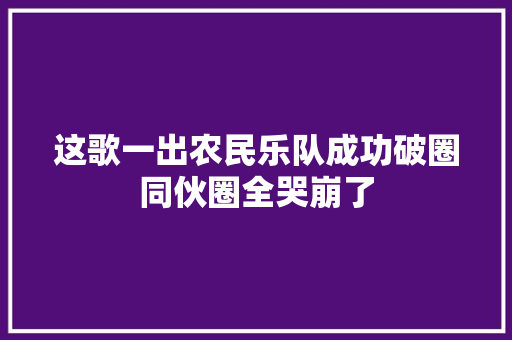
“打开,快听,我哭得弗成。”
一看,原来是《大梦》。
最近,这首歌火得弗成,在各大视频网站的弹幕里涌现最多的词儿:
便是“哭了”、“后劲有点大”。
不仅这首歌成为本期最佳,也成了这季《乐夏》的最有影象点的歌(之一)。
一首歌。
怎么就调动这么多网友的感情。
也还能让这个没多少人听过的农人乐队成功破圈,乃至,还登上热搜话题。
这首歌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魅力。
Sir一边打开了这首歌。
大梦 (Live),瓦依那;任素汐 - 乐队的夏天3 第7期
一边,再跟你们聊聊这场梦。
01
来自广西的瓦依那乐队与任素汐一起互助的这首歌,用7分55秒浓缩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平。
从六岁,到八十八岁,从幼童,到老年。
这首歌最扎心的是,在每一个人生节点之后,在面对现状的焦虑、纠结时,歌词都向虚空中,发出一句无力的“怎么办”。
仿佛是在诘问着命运为何如此坎坷。
也如实地描述着,当代人在当下生活中挣扎与不甘。
Sir试图在这首歌里,找到人们的共同感情。
创造,在这首歌的视频下,一条最高赞的留言戳中了许多人的心:
我与牛一样,虽然有着各自的缺陷,却有着相同的渴望。
牛的生平只图青草,我的生平只图温饱
怕。
无力。
不知未来会是如何。
只想一日三餐,得到基本温饱就可以了。
在历经“口罩”、“职员优化”、“薪酬构造调度”后,这也是许多人在时期阵痛下产生的共同感情。
就如伍佰在演唱会里发出的疑问,“你们都是25岁,为什么会听我的歌呢?怎么会呢?我写这些歌你们还没出生呢”。
而且你们才25岁,怎么生活有那么多痛楚呢。
人与人的感情,虽然并不相通。
但,痛楚,迷茫,都是生命的必经之路。
也难怪,大张伟在点评这首歌时会这样说:
没听懂这首歌的人,是牛逼的,由于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也没有身处生命的纠结之中。
如果有些人听完这首歌
完备也没什么被打动的觉得
我特殊为这帮人高兴
由于生活注定是无所适从的
然后如果有一些人听完之后以为
(生活)不就这样吗
了不起的人那都是
我们渴望回到一个体面、稳定的生活中,但,现实却并不那么如人所愿。
在《大梦》长达近10分的原版里,有几段在节目上被删减的歌词。
我已二十三 大学就要毕业,
看身边的人 逐渐地远去,
......
害怕谈恋爱 害怕找事情,害怕回家里,害怕去外地。
我已四十八 孩子已终年夜,
她在外玩耍 很晚都不回家
......
半生已过,仍不得解脱,该怎么办
我已五十八 早就白了发,
很多的地方 已变得不听话。
年小的孩子 常年在外地,年迈的母亲 什么已记不起,
担心不完,聚了又散,该怎么办
这与7分钟的《大梦》比较,更像是真实生活中的残酷,也是更现实的人生。
大学毕业时的迷茫,成家后的寂寞,中年后的“萎靡”,亲人的逐一拜别。
这便是生活。
歌词虽然在问着“怎么办”,但,它真的是在寻求一个办理办法吗?
在原版的结尾里,十八的歌词是“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
你只能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哑忍当下。
问题有时候本身便是答案
追寻的过程
它便是一种答案
显然,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但便是“没办法”。
那就受着。
活着。
“怎么办”是下决定前的缓冲,当年岁连续往前走时,生活也会见告你答案。
就如万能青年旅店的《十万嬉皮》里的歌词一样平常:“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师长西席,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已经是“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这也是生活。
严谨地来说,瓦依那并不属于“摇滚音乐”,而分类属于“民谣”。
但,它在这首歌里,所展现的生命力,凝聚的感情,却有了某种坚韧不摧的音乐力量,它所造成的冲击力,并不亚于摇滚音乐的叛逆与乖张。
在这首歌里,“希望”与“悲悯”,“痛楚”与“沉着”,交替涌现。
它展现的是一种厚重的,属于这个时期的宿命感。
以是,它也能一下就击中全民的心。
02
如《大梦》这样的歌,实在并不少有。
细数近几年的盛行音乐,如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法老的《亲密爱人2017》等,都因此“韶光”节点的办法,去记录一个普通人、普通家庭十几年、几十年的变迁。
再往前,如李宗盛的《阿宗三件事》,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林强的《向前行》也都因此小人物的故事,去与当下的时期共呼吸。
但,也有不少音乐不需如此对仗工致的歌词,去标记时期的变迁。
只要一句话,一声叫嚣,就已经把人拽入它所描写确当下的集体时期中。
80、90年代中国摇滚开始兴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人们生活碰着巨大变革,各种思潮涌入,摇滚成为这个时期中最适宜抒发奋怒、迷茫的最好渠道。
魔岩三杰,何勇的《姑娘 俊秀》里,替所有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喊出愤怒:“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窦唯的《悲哀的梦》,不解地质问着当下:“到底若何才算好不算坏,到底若何才能适应这个时期,我不明白,太多疑问,太多无奈,太多徘徊”;
张楚的《彼苍保佑吃完了饭的公民》,“只想能够活下去,精确地摧残浪费蹂躏剩下的韶光”。
无需太多阐明,音乐便是这个时期的最佳注脚。
一首属于某个时期、一个阶层、社会的音乐,会更加具有生命力。
再往前,1982年。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专辑里,险些所有的音乐都在描述着飞速变革的时期之下,乡愁与个人归属感的割裂。
像是,《鹿港小镇》里,他对路人的三次搭话:问“我”的爹娘可好,问“我”的爱人可好,末了,以游子的身份,想让路人见告他的亲人,台北并不是他的黄金天国。
但,刺痛人的,还是这首歌末了几句: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落去他们拥有的
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
子子孙孙永宝用 世世代代传喷鼻香火
家乡也已经凋零,故土从红砖变成水泥墙,子子孙孙虽然永传福祉,可这句话却变得格外讽刺。
你可以创造。
所有具有生命的、能出圈的音乐,都是在为时期与底层公民、普通民众而画像。
民众须要有人为他们歌唱,替他们唱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唱出自己须臾即逝又微不足道的人生。
你们该当还记得,在《乐夏2》里有两支格外出圈的乐队:五条人,两位穿着拖鞋,从城中村落里走出来。
以及九连真人,这几位从大山里走出去,为了生活而冒死的“阿民”们。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些乐队里脱颖而出,成为征象级的“顶流”乐队。
还是由于,他在唱着我们的歌。
他们用音乐阐发当下的生活,用平常生活的碎片,拼凑出这个时期下一个个活生生的小人物。
电影《大佛普拉斯》里,“面会菜”便是一道“不只彩”的菜。
监狱犯人家属由于太远没空去探视,会给店家寄钱,让他们送收拾给监狱里的亲人。
它虽然简陋,不只彩。
但,它却有着朴实的温暖。
这顿饭,也让肚财人生末了的一顿饭吃得如此温暖,而在此时,《面会菜》这首配乐,也让这一处,成为电影里最催泪的地方。
口哨,让这首本该沉重的挽歌,变得轻快了起来;没有歌词的吉他旋律,像是肚财平凡又一贯疗愈自己的人生。
贫穷却又想逆天改命的肚财,到去世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就连一根客人剩下的鸡腿,也是肚财本日的“好运气”。
他的去世亡,也如这轻飘飘的音乐,宛如在野外边随口哼的小曲,俏皮地飘了过去,只留下了一个白色的圆圈。
这首《面会菜》,也让“生祥乐队”被更多人听见。
在林生祥的作品里,有着这个时期难得的慈悲与对小人物的不雅观照。
林生祥除了《大佛普拉斯》,他的《菊花夜行军》《风神125》《阿成想种田》等歌曲,讲述的便是城市打工人,失落意地回到家乡,重新探求生活的出路。
正是这些在地皮与苦难之间成长出来的音乐。
才让我们这些灵魂流落的人,在他们的声音里,找到了归属。
03
刻画时期的音乐,也终将会超过这个时期。
它们所背负的,是对这个时期的解读;
音乐,是具有时期性意义的。
戴锦华引用过布里恩·汉德森的一句话:“主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通过这些从民间里出身的音乐,我们能够很快地走进某个时期的影象中去。
这种影象的连接、继续,让当下的人们感想熏染到安慰,产生面对苦难的勇气。
△ 《钢的琴》,开头便是一派没落东北重工业形象,在一直冒烟的烟囱下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
你会创造,在许多电影里,有一、两首极具时期风格配乐,成为电影插曲。
它并不是那么随意地就涌如今电影里,而是由于,它承载了一个时期的影象。
借了它的灵魂,放在了电影里。
贾樟柯,绝对便是这方面的里手里手。
在《小武》里,他插入了《心雨》《爱江山更爱美人》《霸王别姬》等音乐,他的原始想法是,想让自己的影片具有“文献性”。
以是,选择了那一年卡拉OK文化里,最盛行、也最具代表性的“俗”歌。
让这些音乐成为全体社会感情的一种反应。
“譬如,《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样一种很旷达的消沉,还有《霸王别姬》里头的一种虚脱的英雄主义,都恰好便是我在影片里想要表达的。”
选自《贾想 1996-2008》
△ 《小武》里,小武与妓女梅梅随着《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音乐舞蹈
作为时期背景,这些音乐可以这样堆砌。
但,在《江河故人》里,涌现了四次的《珍惜》,就不单单是时期的画外音了。
这里的作别,有很多重关系。
晋生、沈涛、梁子三人的分道扬镳,沈涛的父亲去世,沈涛送别儿子,儿子在国外与故土的分别……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人。
那便是张艾嘉饰演的中文老师。
由于这首歌本是属于她的。
这就要回到《珍惜》,虽然可以用在很多场景,但歌里唱的是哪种送别?
是朋友之间。
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的喷鼻香港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参考罗大佑的一首歌:“心腹生平拜拜远去这都邑。”
认识多年的朋友溘然间天各一方。
以是珍惜里才会唱“出息或有白雪飞”,喷鼻香港是不可能下雪的,除非朋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这种分别,是他们自己想要的吗?
以是歌里才会唱“愿望世事总可有转机”,是时期命运的年夜水将人冲散了,个体是无能为力的。
以是,当到乐与中文老师米娅聊起她来自哪里时,《珍惜》这首歌又一次响起。
而到乐问她,为什么来澳大利亚时。
她选择躲避这个问题。
当沈涛在音像店听到《珍惜》时,她听不懂,只以为好听。
她更不知道,歌里所唱的离去,正在另一些人身上真实发生。
这便是所谓的初听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
告别是如此的漫长。
它常常在我们还没故意识到要告别时,就已经开始了。
一首《珍惜》。
居然能把几代人,把超过时空素未谋面的人,贯穿在一起。
还有陈果在《榴莲飘飘》里的两段“改编”音乐的利用。
一是,在喷鼻香港从事了三个月性事情的小燕回来后,与她戏校的同学坐在铁路边消磨韶光。
个中一个男同学改了《婚礼进行曲》,将神圣的“婚礼”,变成了:
结婚了吧,傻逼了吧
一个人赢利,两个人花
离婚了吧,傻逼了吧
往后打炮要买单了吧
是对婚姻的不信赖?
倒不如说,也在那个时期里,都感到无所适从又惶恐的年轻人用这首邪性的歌,唱出了对永恒的嘲讽,对当下的歧视。
接下来,小燕也不甘示弱。
说,我也唱一首叫《原始社会好》。
飞驰而过的火车,一会,粉饰住他们的声音;一会,他们又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不会被时期带走,他们也不会完备勾留在那个时期中。
在这部电影里,有一首插曲《你我他她》险些与开头的《大梦》交相呼应。
你为什么要上学 你为什么要上班
你为什么要用饭 你为什么要睡觉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便是这样不想说
我为什么要饮酒 我为什么要唱歌
我为什么要欢笑 我为什么要做爱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便是这样不足格
“为什么”,“怎么办”。
间隔了23年前后,在不同时期里的人,却都还在问着相同的问题,这也是每个时期里,周而复始的终极命题。
从音乐走向电影,再从电影回到音乐,Sir仿佛看到了艺术之间相通的宿命。
在某种程度上,它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涌现、演绎,都还是在谈论着人们存在的共同命题,关于衣食住行,男女,希望,关于生活,关于生命。
说大,这些议题很大。
说小,实在这些题里,也只装下了几块碎片,一首歌词,一句为什么,但便是这些如尘埃一样平常的细节。
却包含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大梦》也好,电影也罢。
这个天下,须要有一处出口,让我们安顿绝不起眼的人生。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