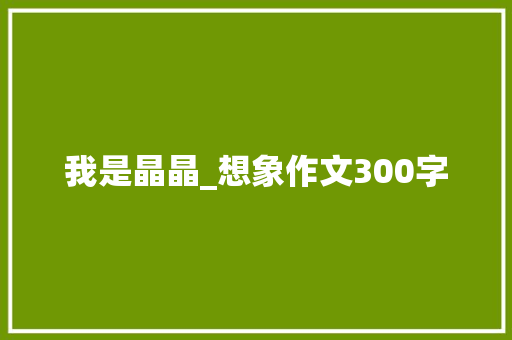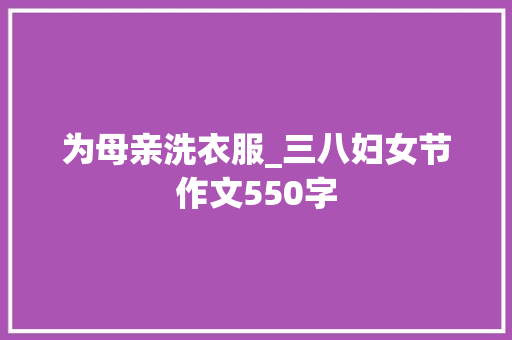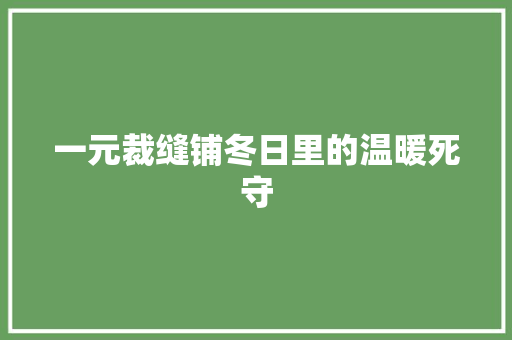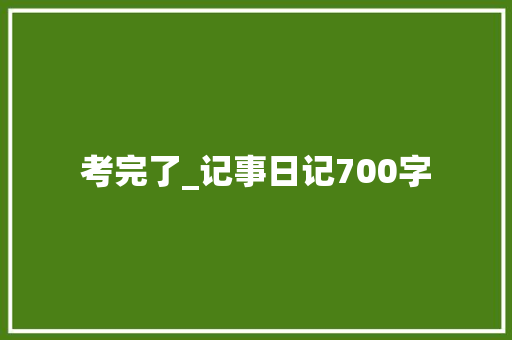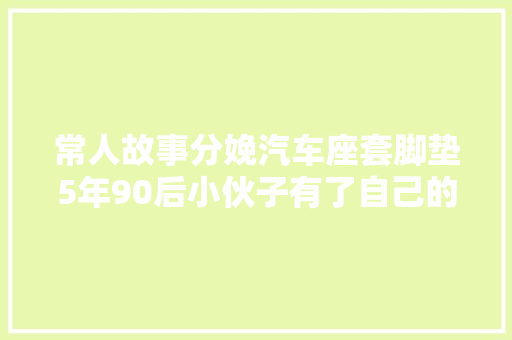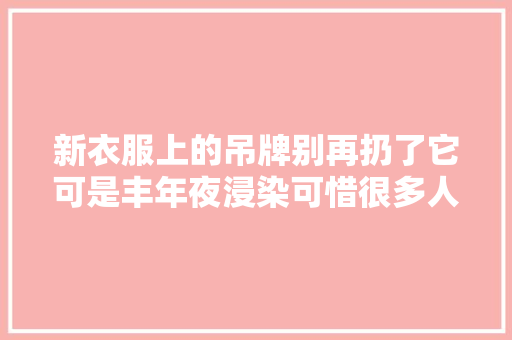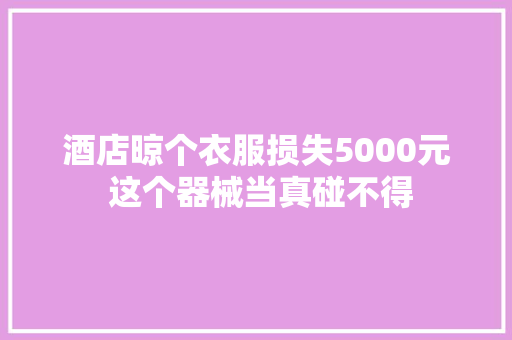秋季梅雨时节,我会想起老家的裁缝。
四十年前的老家屯子,成衣服装店寥若星辰,也绝少有人到服装店购买成衣。一家人的衣服,大略的家里妇女自己缝,轻微繁芜点的都由村落里的裁缝缝制。以是那时候老家一带险些每个村落庄都有自己的裁缝铺子和裁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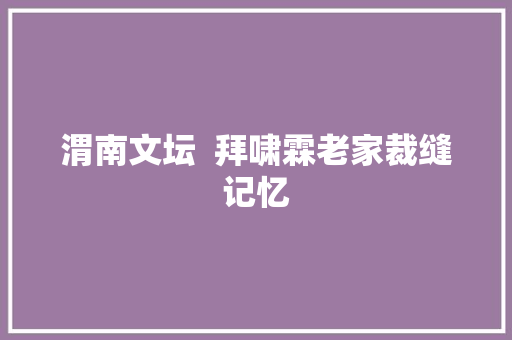
老家人的眼里,裁缝是斯文、手巧、怀孕手的能人,干净、体面、轻松,一天到晚都在屋里做(zou)活,不见风雨不嗮太阳,不受冷热不怕霜雪,比起每天头顶日头背朝天在土坷垃里讨生活的庄稼人,那切实其实是神仙般地营生,大家倾慕神往。
村落里那时的裁缝有两种,一种是大队裁缝铺里接活的裁缝,一种是在自己家里给人做衣裳,也应邀到主家做衣裳的裁缝。改革开放以前,只有裁缝铺子的裁缝,没有私人家里的裁缝,听说那时政策不许可私人做(zou)活,创造了会被当作“成本主义尾巴”。
起先缝纫机是金贵玩意儿,一个大队也就裁缝铺里有两三台,能当裁缝的人都是“人梢梢”(有能耐的人)或者家族背景不一般的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往后,结婚嫁女缝纫机成了像样的嫁妆,学裁缝的才开始多了起来。传说村落里最早的裁缝师傅是个逃难的河南人,周遭几十里带了几个徒弟。后来收徒弟教缝纫的,除了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咕咚”的“装花鬼”(假的),多是这些人的徒子徒孙。少数家里买了缝纫机的姑娘媳妇粗学个把月,紧张为自家做事;但大多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只会大略地用缝纫机缝些大略的衣裳,或者是破损衣裳的缝缝补补,手艺没办法和拜过师傅的裁缝比。以是村落里人对这些只会大略利用缝纫机,并不会裁剪衣服的女子媳妇缝制衣裳不叫“缝衣裳”,称作“踏衣裳”。不言而喻,家里人、巷里人认为女子媳妇只能踏动缝纫机的踏板,只会缝补衣服,不会有模有样地裁剪布料,算不得裁缝。
(一)
四十年以前,碰着秋日连阴雨的景象,庄稼地里的活干不成,或者收了秋有了空余韶光,母亲有时会请五队的“梅姨”到家里做(zou)衣裳。那是我们家从小到大一家人一年上档次的新衣裳,一样平常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穿。平时我们穿的衣裳,都是母亲和大姐手工缝制的。用的布料也是自己家里织的粗布,颜色都很单一,除了发黄的土白色,便是阳村落会上买的纸包包土“颜色”(染料)染的蓝色或玄色,一见水都会褪色,洗过两三水之后都会“潲色”,衣裳会发白或者发黄。
请“梅姨”到家里做(zou)衣裳前,母亲会根据当年的收成、我们姐妹几个的身材、身上衣服的新旧情形方案,大多先从柜里拿出家里织的粗布染好颜色,也到大队商店或者官池供销社看布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往后会到阳村落会上或者官池会上看布料,绝少到县城买布料。影象中第一次到县城买布料是大姐出嫁前为大姐置办嫁妆、买柜子、买衣服,捎带沾光也给我们兄弟几个买了料子。那时候老家一带买布料,不叫买布叫“扯布”。在供销社看好了布样,给业务员说“扯”几尺,业务员会拿剪刀在量好尺寸的地方剪一个小口子,两手捉住小口子两边用力一扯,“嘶啦”一声,一块布料就扯下来了,估计“扯布”的叫法就来自于此。
准备好布料,母亲会提前和“梅姨”说道(沟通)一次,说一说要做衣裳的每个人身高、胖瘦,我们兄弟几个一半年个子长得快慢,以及准备的布料情形,初步的想法等等,最主要的是和“梅姨”约定日期,请到家里做(zou)活。
“梅姨”来家里做衣裳的先一天晚上或者大凌晨,父亲会叫上大哥用架子车把“梅姨”的缝纫机及熨斗、剪刀、滑石粉、皮尺拉到家里,有时在前门的门房,有时在敞亮的厦子房。裁剪衣裳的地方,一样平常是几块木板,或者是厦子屋里的门板,放到板凳上临时搭起来,再铺上塑料布或者粗布床单就成了裁剪衣服的案子;做的衣裳少时,怕麻烦了就借用柜盖做裁衣裳的案子。
影象里“梅姨”是个干净利索的中年妇女,给人的觉得什么时候身上穿的衣服都合体新颖、棱里棱锃。上小学的时候“梅姨”的一个姑娘和我一个班,叫什么名字已经忘了,总是花枝飘荡的,穿的衣服是那时最为时髦的花洋布料子,样子很新潮,惹得班里的女孩子心里痒痒,艳羡其有一个巧手的裁缝妈,乃至有的女孩子在心里抱怨自己怎么不生在“梅姨”家里,有“梅姨”一样的妈;男孩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多看“梅姨”的那个姑娘几眼,多是忍不住地啧啧夸奖人家衣裳的“好看”,也不用除有的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梅姨”到了家里,会先看做衣裳的布料,母亲把准备的布料子全部拿出来,有土布和洋布,土布基本是白色、玄色和蓝色,洋布有的确良、卡其布、羽缎布等,颜色多是纯蓝、纯灰、纯黑,给大姐做衣裳的布料也大略,除了格子布,条纹布,很少有其它图案。看布料的过程“梅姨”会再次和母亲确认用什么布料给谁做衣服,上身还是下身,给谁做几身,然后便是相机行事。
“梅姨”量尺寸不叫量身体,叫“量衣服”,实际上该当叫量尺寸裁剪衣服。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院子中间,眼巴巴地等着“梅姨”按顺序叫“老大——老二——老三”。“梅姨”量身体时很轻巧,皮尺一下子横量,一下子竖量,身高、肩宽、胸围、腰围、胳膊、裤腿,边量嘴里边念叨数字,随手在纸上或布料上记下旁人看不懂的符号和数字。给我和弟弟一样的小孩的“量衣服”,“梅姨”有时也用手指“拃”量,拇指和中指在肩部或者背部来回腾挪,像弹钢琴一样,有时触碰到痒痒肉,我会不由自主地身体扭动,这时“梅姨”会说:“别乱动,立时就好了,不听话乱动你的衣服做坏了,看你过年穿啥。”闻言我会立时变得老诚笃实,纹丝不动,我可不愿过年没有新衣服穿。在“量衣服”过程中,有时“梅姨”也会没话找话的说几句,见到老大会对着母亲说:“一年没见,这娃长得像电线杆子!
”给老三量时会对母亲说:“你这老三长清秀得很,像个女娃!
”给我量衣服时对母亲说:“我姑娘说你这娃在学校捣蛋得很!
”……不知不觉中,“梅姨”完成了“量衣服”。
关于那时“量衣服”,我有个影象终生难忘。“梅姨”给我量尺寸的时候,母亲会反复地打发:“这碎的长得太快,袖子和裤腿要做长一点,尺寸放松泛一些。”“梅姨”只是微笑并不应声,母亲不放心又说:“最少穿个两三年不短、不窄”。“梅姨”终于忍不住说:“只要你娃没有白杨树长得快!
”这种尺寸下给我做的衣裳,袖子、裤腿最少得挽起两个半寸宽的折子。到折子全部放下展开时,一样平常胳膊肘、膝盖、屁股蛋的地方,都被我爬树、上墙、溜滑滑磨出了洞,缝了补贴。
之后“梅姨”会戴上深色的套袖,在案子或柜盖上展开布料,几番念叨与打算之后,拿起一尺多的短直尺,用鲜艳的滑石粉在布料上划横的、竖的、斜的道道、杠杠,确认无误后拿起厚重锋利的裁缝剪刀,“咔嚓、咔嚓”,三下五除二,手脚麻利地把整块的布料裁剪成形状互异的布片片。
我那时对“梅姨”裁剪衣服时用的剪刀和滑石粉特殊感兴趣。
对剪刀的兴趣,只是惊异于其与巷里人平时用的不一样:首先是剪子把的差别很大,家里的剪刀把是对称的,中间是直的,两边有弧度,“梅姨”的剪刀把一样平常是直柄,尾部有半寸波折,另一边只有能放进拇指的圆孔;其次是“梅姨”的剪刀规格要大一些,有家里常见剪刀的一个半大;最为突出的是“梅姨”的剪刀特殊锋利,剪布特殊地“快”,我特殊喜好听“梅姨”裁剪布料的声音,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层层的布料被剪出各种形状。
对付滑石粉的兴趣,我那时切实其实是痴迷,直至闯了祸。“梅姨”的滑石粉与学校里的粉笔不一样,滑石粉是薄薄的扁平椭圆形,在布上画出来的线条风雅清晰、颜色鲜艳,不像粉笔画出来的线又粗又壮,掉渣渣,颜色也不正。没事的时候,我会眼睛一刻一直地看“梅姨”手指轻巧的在布料上横、竖、圆、斜的用滑石粉划来划去,那些线条和颜色,在我的眼睛里像是梦幻。看得韶光久了,我莫名的产生了一种幻觉:自己拿着滑石粉在布料上划来划去。“梅姨”临时有事回家时,受幻觉的使令,我竟然神使鬼差的在新布料上画了许多横七竖八的彩色线条,“梅姨”的一盒子滑石粉险些被我挥霍完了。“梅姨”回来创造我的这一“精品”后,气的哭笑不得,把我的恶劣行径奉告了父母,结局自然因此我遭受一顿痛打而告终。
“梅姨”到家里做衣裳的那几天,我时候惦记着“梅姨”做出的衣服,想象衣服的样子,穿在身上的效果,大脑里来回都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放学的路上,坐在教室里,面前满是“梅姨”做衣服的影子,耳朵里总有缝纫机那嘀哒、嘀哒的声音;夜里梦见的也是“梅姨”坐在缝纫机前弯着腰、歪着头,有节奏地踏着脚踏板,针头像小鸡啄米似的带着缝纫线飞快地高下来回,布料行云流水般时而前行,时而后移……梦醒后,乃至还能闻到新布料与缝纫机油的味道。
(二)
实在请裁缝到家里“做衣裳”不是年年都有,只有收成好的年景,再便是碰着嫁女的年份,其它韶光做衣服大都送到大队的裁缝铺子。巷里人谁家有姑娘出嫁,主家会欢天喜地地把裁缝请到家里,好好“做”(zou)几天活,好吃好喝呼唤着,在门房或者院子的敞亮处搭上临时案子,把买好的布料整洁地码在案子上……裁缝一种一种料子,一件一件衣服,一丝不苟的为待嫁的姑娘做着嫁衣,姐妹、婶子、邻居一应人和裁缝说谈笑笑,全体院子里的洋溢着浓浓地喜气。
这是至今老家人最喜好回味、心情惬意的裁缝“做衣裳”场景。
除了“梅姨”,那时村落上的裁缝还有“跛子金金”、我学前班的老师“疙瘩士俊”的老婆、“瑛”的母亲,也有可能还有其他人,年代久远记不起来或者村落庄东边较远的一、二队我不太理解。
“跛子金金”我还算比较熟习,他和我四“大”(爸)年事相仿、关系熟习,常常到我四“大”家里串门子。那时我们巷东头的几个“碎怂”,看到“跛子金金”来了,喜好跟在他后面排成一排,模拟他走路一摇三晃,高下起伏,旁边摆动如在湖面上行船的样子,边学还边在后面指指戳戳、挤眉弄眼、捂嘴偷笑,以别人的身体毛病探求自己的快乐,现在想起来实在不应该。刚开始“跛子金金”创造“碎怂”们在身后排了一排子学他,扭过身子做出要驱赶的样子,恼羞成怒地骂一声:“碎怂,皮松咧!
沟子痒痒,想挨打咧!
”有时乃至会弯腰脱下一只鞋,拿鞋底子扔过来砸学他走路的碎娃娃。韶光长了,“跛子金金”对这些“碎怂”的行为也习以为常,不再生气,只是象征性扭头做出“吆鸡”(驱散)一样的动作,之后会满含微笑地连续前行。
村落里人说,“跛子金金”的腿不好,但裁缝活手艺好,信手拈来,只要你能说出来样式,或者能拿出来图片,就没有他做不了的衣服。乃至有的巷里人说,“跛子金金”不仅会做新式衣服,老式衣服也会做,老婆婆做的“盘扣”会做好几种。最根本的是他做的衣服好,常常会把外边的新格局带到村落里,缝的衣服针脚周详,线缝子端直顺溜。最为村落里人称道的是他裁剪布料一个钱打二十四个结,从来不摧残浪费蹂躏一点点布头布角,这在物质紧缺的时期深得大家赞许。碰到相好、对路的,“跛子金金”还会帮着把裁衣服剩的布头、布角裁成各种鞋面子,棉鞋面、夹鞋面、单鞋面,有大有小,精心打算。
“跛子金金”那时紧张在大队的裁缝铺子做衣裳,很少到人家里去做,也可能与他行动不便有关系。
有一年过年前,我随母亲“量衣服”,去过大队的裁缝铺子。
裁缝铺子在大队部以南东边的排屋子里,是那种人字形、两倒檐的大房,比一样平常的厦子房要宽、要高,有八九间房的样子,听说旧社会财东或者地主家里的后房(上房)才按这种规制盖。大队南的排子房路东、路西各有两排,门都朝南,路西是医疗站,路东是供销社和裁缝铺子。
裁缝铺子在供销社的东面,房门与厦子房的门大小差不多。房里面的纵深长的多,空间要比厦子房大。屋子里面靠东墙摆着一块与“跛子金金”肚子高低相称的木案板,案板的边缘被磨得光滑油亮,该当是年复一年拉扯、抚摸布料摩檫的结果。案板的左边摆着标志性的裁缝剪刀、皮卷尺、木直尺和滑石粉,右边是已经裁剪好待缝制的衣裳布料;案板的内左侧是码放整洁等待裁剪的布料,上面别着字条,标记着布料的尺幅、是非以及人名、日期;内右侧叠放着一些碎布料。案板的最右侧靠近窗户的地方是一台锁边机、一台缝纫机。“跛子金金”的脖子上挂着皮尺,手里拿着直尺,正用滑石粉在一块布料上有模有样地画着横的、竖的、斜的、半圆的线条,显然是在设计待裁的布料。
母亲和“跛子金金”几句大略的话语后,“跛子金金”尺随手走,一下子结果就出来了,一些数字和符号被他记在对面墙上。“跛子金金”顺便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半是笑脸半是威胁地说:“往后再不准学我走路,再让我瞥见我饶不了你!
”我这时大多会选择沉默,一声不吭。“跛子金金”会伪装生气地样子厉声问:“听见没?还学不?”我会细声细语地说:“不咧!
”闻言“跛子金金”会用两个手指捏一下我的鼻子,微笑着说:“只要你不学坏,不学我走路,过年担保让你穿上好看的新衣服!
”
“跛子金金”说的话也不假,一样平常来说屯子裁缝最忙的时候,便是寒冬尾月过年前的那一段韶光。那个年代,屯子人做一件新衣服,都是家里的大事。尤其是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给大人、孩子做件新衣服过年。有道是:“有钱没钱,不让小孩穿旧衣服过年!
”那时小孩子对穿衣服甭提有多愉快,小孩子最盼的便是穿新衣服。可新衣服做好了,一样平常都不给穿,要等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守岁时才能拿出来试一试,然后在火炕最暖和的地方暖起来,月朔早上才能暖暖和和、舒舒畅服、神气十足地穿在身上,昂首挺胸地走出家门,邻居由衷地一声夸赞:“哟!
看这衣服,穿在身上精神抖擞!
”对付小孩子来说,那种得意劲儿别提有多高!
无论大人小孩,过年穿件新衣服,图的是个喜庆。以是尾月里裁缝铺里的裁缝忙的是一塌糊涂,不分昼夜地赶着做活,想赶在除夕前把所有人家的新衣服都赶出来,不想影响送活的人家过年对喜庆的期盼和渴望的心情。但也会碰着做衣服的活太多,或者裁缝家里临时有急事,或者碰着不可预见的其它事耽搁了韶光,送活较晚个别人家的衣服大年三十做不出来,裁缝也要在三十晚上关门歇工。一样平常碰着这种分外的情形,裁缝铺子的裁缝会和委托做衣裳的人家提前沟通,商量好取衣服的末了期限,商量好哪些衣服必须在三十那一天取,哪些衣服无可奈何地推迟到大年的初五六。这时一样平常的顺序是小孩的新衣服先做,大人的衣服排到后面。裁缝也知道小孩子都在猴急猴急地愿望着新衣服,没有新衣服有的“麻糜子”(说不清)小屁孩会哭得去世去活来,闹得一家民气里不痛快酣畅。大人纵然过年穿不上新衣服,没有人会不要脸面地闹活。这中间也不用除有人一直地讯问、敦促裁缝惹得裁缝不高兴,或者有的人裁缝平时就不爱待见,或者比如碎怂学“跛子金金”走路得罪了人家之类的情形,裁缝心里不痛快酣畅故意把这一家人过年的衣服放到后面,乃至三十也做不出来。
总之那时听到“跛子金金”威胁不给我做过年新衣服的话,我都是老诚笃实、服服贴贴地边回话、边担保、边点头,一幅彻底屈膝降服佩服的样子。
(三)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村落里裁缝做的衣裳格局并不多,便是常见的那几种。据年纪大的人说,刚解放那些年还做过老式的对襟、右衽盘扣衣服和大裆裤,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都改成了新式衣裳。
新式衣裳男装不分大人小孩,多是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或者解放军衣服的样子,差别紧张是衣服兜兜,两个兜还是四个兜,兜在表面还是在里面,兜兜上面有没有帽檐、盖盖,听说五六十年代四个兜是干部的标志,两个兜是一样平常群众;女装的格局也不多,无非是老式的偏襟,新式的对襟,差别紧张是衣服的扣子,是老式的盘口,还是塑料的洋扣子,还有明光铮亮的金属“芝麻扣”。
裤子格局的变革也不大。男裤早期是大裆裤,开放往后也盛行过一阵喇叭裤,后来是直筒裤。去年回老家谝闲传的时候听一个做过裁缝人说,女裤经历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变革,早期村落里妇女穿的裤子是那种宽腰裤,裤腰一折便于用裤带系,没有开口也没有挂钩,后来女裤多在右侧面开口,裤腰用挂钩联结,向下与裤兜相融的部分是塑料纽扣或者“芝麻扣”联结。刚开始穿这种阁下开口女裤的时候,还闹出了不少的尴尬事:有的“铺稀赖花”(邋遢)的婆娘,常常会忘了扣裤子侧面的扣子漏出里面的花裤衩,大庭广众之下被人笑话,自己也害臊的满脸通红抬不开始;也有的“烂婆娘”伏天热了图凉爽只穿表面一条裤子,要么忘了扣裤子侧面的扣子,要么是“芝麻扣”常常憋开,露出白花花的沟蛋子,惹得几个不怀美意的“半大哈怂”,没事寻事地到院子转来转去,贼眼滴溜溜地胡瞅乱盯。得知原形后气得“阿家妈”(婆婆)和“外天人”(丈夫)“日天叫老子”地臭骂几天。
后来老家裁缝的没落,更多是社会经济发展、选择办法多元化、人们不雅观念改变的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与裁缝做的衣裳格局迂腐、跟不上时期发展也有关系。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阳村落会上和官池会上南方那些花花绿绿、格局新颖的时装逐渐地多了起来,有些布料子村落里人别说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最有代表性的是牛仔裤的料子——牛仔布,看着像以前的蓝颜色“劳动布”,但比“劳动布”厚实耐磨,颜色好看,受年轻人喜好。尤其是摆衣服摊摊的那些贩子,从南方贩来裤腿宽的像“蒲篮”(一种竹纪年夜口农具)的喇叭裤、沟蛋子包的牢牢的牛仔裤、花里胡哨的衬衫……等等那些见也没有见过,格局奇奇怪怪的南方时装,勾引得年轻人眼放亮光,心里痒痒,再也没有人乐意找村落里的裁缝做衣裳;逐步地各种价格低廉的劣质T恤衫、夹克衫、洋装,也挂在了卖衣服的摊摊上,乃至连玄色、深蓝色、灰色中山装会上也能买到,于是村落里人开始去阳村落、苏村落、官池赶会买衣服,后来到县城的阛阓买衣服也稀松平常了。
有一年回老家过年,看到邻居的衣服样子很时髦,但布料打眼一看就不怎么样。我问邻居:“裁缝做的衣裳质量好,还是会上买衣服质量好?”邻居说:“要说质量,还是自己找裁缝做的好,毕竟布料是自己买的,货真价实!
”我接着又问:“自己做的衣服质量好,现在咋不找裁缝做衣裳了?”邻居笑着说:“虽然会上买的衣服料子差点,没有找裁缝做的质量好,但会上的衣服花样多、格局新、价便宜。”其余一个邻居补充说:“会上买衣服方便,再不用摧残浪费蹂躏韶光去考虑扯布、靠裁缝韶光、等着量尺寸,衣服烂了或者“行门户”(参加红白喜事),想穿件新衣服,不用再心急火燎地等裁缝,只要想穿想买,到会上或者阛阓拿件衣服在身上试一下,只要样子新,不丢脸,大体得当,尺寸大一点小一点,都不是问题,紧张是省事!
”
卖衣服的刚开始冲击裁缝的时候,村落里年事大的人在市场上买的衣服尺寸大多不得当,不是太大穿着晃荡荡,便是太小穿得像耍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往后,屯子市场发卖的衣服质量和布料也逐步好起来,格局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受欢迎……在服装市场的冲击下,巷里人越来越看不上曾经穿过老样式衣服,到市场上买衣服的越来越多,找裁缝做衣裳的越来越少了,裁缝的活自然也越来越少了,乃至有的无活可干了。于是一些裁缝不得不转行另谋他路坚持生存,或者赶会卖衣服,或者开布艺店,或者赶集做窗帘,或者沉沦腐化为裁裤边、缝破损、换拉链的……还有一些裁缝彻底伤了心,卖了一应缝纫设备,彻底收摊不再涉足这个行当。这个中也有个别脑筋灵巧、思路开阔的村落庄裁缝,或者进城开服装店发展成了服装阛阓,或者走高端定制的路子闯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百里挑一。不可否认的是,老家的裁缝,在南方服装的冲击下无可奈何地没落了。纵然巷里一样平常人家里的缝纫机,也都放到了屋子的偏僻处,一年到头难得动一次,有的已经成了小孩子写字的桌子,有的落了厚厚的灰尘。
四十年后的本日,当我在城市边缘的市场,看到那些还在用缝纫机裁裤边、换拉链的摊位;或者在闹市的街道,看到各种打着纯手工制作、独家订制高档服装的广告牌,我会想到老家的裁缝,想到贺知章《咏柳》的诗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仲春东风似剪刀。”老家的裁缝,是那个年代知足村落里人日常穿着,给乡党生活带来丝丝温暖,像东风一样为老家人裁剪出美好的人,如今他们已经远去,模糊在影象里,成为那段岁月特有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