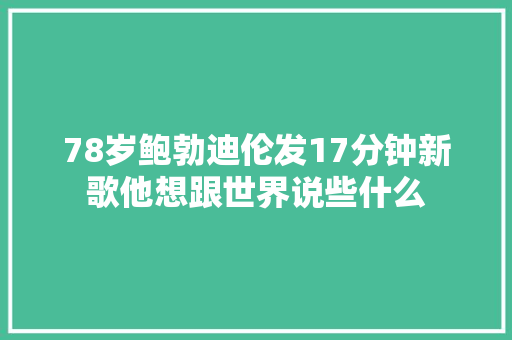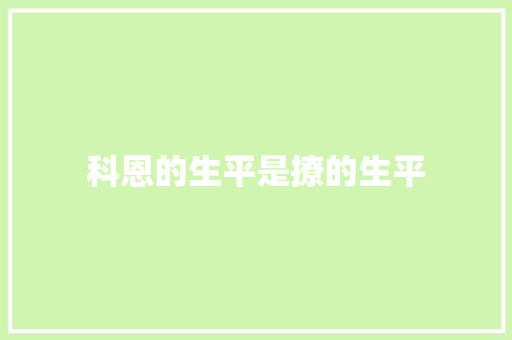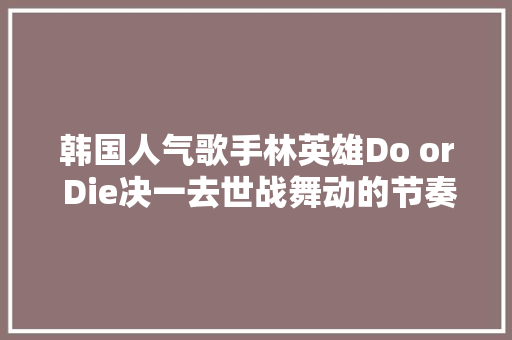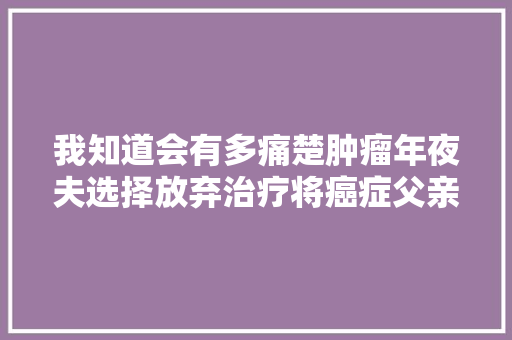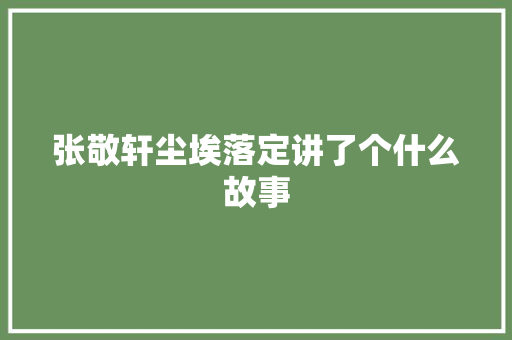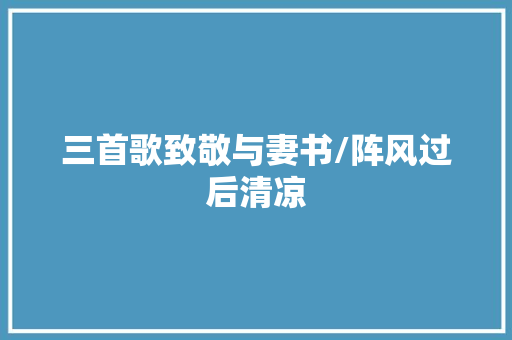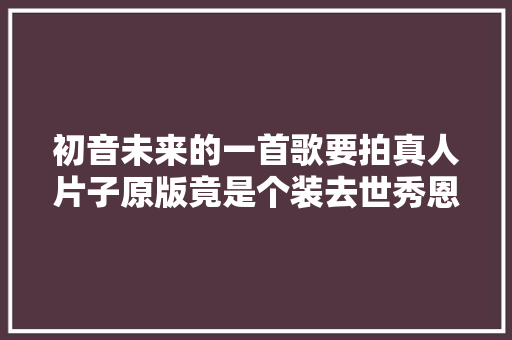原标题为“1980年代海内首译首发的鲍勃·迪伦诗歌六首”
昨天,瑞典文学院宣告美国著名民谣和摇滚艺术家鲍勃·迪伦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性表现”。这迥出很多人的想象之外,也难免引起争议。由于在很多人看来,迪伦毕竟只是个诗歌票友,而非专业墨客。但事实上迪伦已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很多年了,早在半个世纪前,他的歌就受到金斯堡、聂鲁达这样的大墨客的讴歌。也早有学者把他作为墨客来研究。

虽然鲍勃·迪伦在1980年代就为海内文化界所熟知,但由于大家紧张是把他看当作音乐家来看待,因此对的诗作译介很少。以至于获奖传来,大家能找到的译作很有限。目前,飞地书局"大众年夜众号推出周公度的27首译作,对付大家理解迪伦诗歌帮助很大。飞地声称这是迪伦“在海内首次且唯一揭橥的27首诗”,则是缺少考证的说法。事实上,早在1980年,鲍勃·迪伦就已经作为墨客在海内受到译介,在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彭燕郊师长西席主编的《国际诗坛》1988年第1期,就曾出推由白婴师长西席译的一组《美国民歌手波勃·迪伦的谣曲》,共六首。这可能才是海内最早揭橥的鲍勃·迪伦诗歌的译文。下面转发这组译作,以期对大家理解这位墨客有所帮助。
《国际诗坛》1988年第1辑(总第4辑)
美国民歌手波勃·迪伦的谣曲
白婴译
美国著名的民歌手及谣曲墨客波勃·狄伦,幼年在明尼苏达州铁矿区的一个小镇度过,十岁开始离家出走,前后六次。十八岁末了一次出走之后到处流浪,以卖唱为生,同时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他在六十年代越战期间所写的“抗议歌曲\"大众,记录了美国青年在苦难的年代里的失落望,悲痛和愤怒,这些歌词部分被编入《美国诗歌一百首》.可惜他作为民歌手的名气太大,把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粉饰了。美国作家洛德曼在六十年代后期访问智利墨客巴勃罗·聂鲁达的时候,曾经先容过狄伦的谣曲,聂鲁达对它们非常欣赏,还操持译成西班牙文。1973年越战结束之后,狄伦仍旧连续灌录唱片,可是曲词已逐渐流于媚俗, 有些还带有宗教的传道色彩,失落去了早期那种纯朴清新的气质。此处译出的都是较早的作品,选自1987年英国出版的《1962—1985年狄伦的曲词》。
(上图为墨客自绘的漫画像)
让我去世在自己的脚步声里
有人说去世神快到来到这里
可是我不要躲进地底
我也不要去世得伛伛偻偻
我走向宅兆时要昂着头。
让我去世在自己的脚步声里
然后埋进地底。
谣言说有战役,而战役作为生活的意义
早已经消逝在风里
有人相信来日不会太长
他们不学习生活而学习去世亡。
我不算精明,可是我看得见
有人要把我蒙骗
如果战役来到,去世亡处处
在去世于地底之前,让我去世于这个国度。
世上总有人制造恐怖
他们长年累月评论辩论战役的可怖
我读他们的演说,我从不回嘴
可是,老天,请让人们听到我卑微的歌
如果我有宝石、财富和皇冠
我要收买天下,把统统改变
我要把枪炮和坦克抛进大海
缺点的历史该当修正。
让我喝山上流下的清泉
让野花喷鼻香渗入我的血管
让我甜睡于你翠绿的草地
让我安详上路,带着我的兄弟。
去看你阳光残酷的乡土
看山坑和峡谷流泻的瀑布
内华达、新墨西哥、亚利桑纳、爱达荷
让每个州深深印进你的心窝。
而你将去世在自己的脚步声里
然后埋进地底。
许久以前,远地之外
鼓吹和平与兄弟爱,
唉,多大的代价!
许久以前有人实施过
而他们把他吊上十字架。
在许久以前,在远地之外;
这种事不会发生了,
不会了,这个时期。
在许久以前,
奴隶戴着枷锁,
锁链在地上拖曳,
那是林肯的期间,
奴隶的头和心沉得低低。
战役中炮声乱轰,
天下充满血腥。
人的尸体遍布
海岸边的泥泞。
一个人有许多财富,
一个人过得像天子,
一个人永久饿肚子
另一个人在街上求乞。
一个人去世于子弹,
一个人去世于利刃,
一个人目睹儿子伏法
而去世于破碎的心。
人在斗兽场相互残杀,
人们伸开血口欢呼,
那是罗马期间。
眼和心都已经麻木。
唉,多大的代价!
许久以前有人实施过,
不会了,这个时期,还会么?
开动的火车
一列开动的铁火车驶过岁月的长路,
火箱充满痛恨,煤炉充满恐怖。
如果你看到它血红的车身,听到它的吼声,
那么你会听见我唱歌,而你知道我的姓名。
你可想过它装运若何的痛恨?
你可见过它乘载若何的人?
你可想过要把它截停?
那么你会听见我唱歌,而你知道我的姓名。
当他们灌你的耳,洗你的脑,
你难道听不厌恐怖的说教?
你可提出干涉干与题而得不到回应?
那么你会听见我唱歌,而你知道我的姓名。
我不知道世上的领袖是否理解
他们给我造出的这个戾气的天下。
你可由于想这问题而睡不安宁?
那么你会听见我唱歌,而你知道我的姓名。
你可讲过或者在心里揣测
你的邻居受了骗而走上错路?
狂人的疯话可曾害你犯精力病?
那么你会听见我唱歌,而你知道我的姓名。
爱屠戮的匪贼可曾迫得你发狂?
说教和政治可曾使你昏头转向?
焚毁的公共车可曾烧痛你的心灵?
那么你会听见我唱歌,而你知道我的姓名。
约翰·布朗
约翰·布朗出发到异国的地皮打仗。
妈妈为他多么骄傲!
他穿着军服,器宇轩昂,
他的妈妈满脸堆着笑。
“儿啊,你多么漂亮,我喜好有这样的儿子,
我喜好看你手里拿着枪。
听主座的话,你会得到许多勋章,
你回家的时候,它们会挂在墙上。\"大众
火车开动,妈妈提高声音,
把向邻里散布:
“我的儿子出发了,他是个军人。”
她要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有时接到信,她就让邻人们着,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她把穿军服带枪的儿子夸了又夸,
这便是所谓美妙的老式战役。
啊!
美妙的老式战役!
然后,信少了,然后,完备没有了。
断绝了十多个月。
末了得到关照:“令郎退役,
请往火车站欢迎。”
她满怀愉快,在车站到处张望,
却找不到她要接的大兵。
直至所有人都散了,才看到儿子,
可是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哎,他的脸扭歪了,他的手没有了,
一具金属架支住他的腰。
他用陌生的声音逐步讲话,
而那面孔,她竟没能认出他的样貌!
天啊!
乃至认不出他的样貌。
“儿啊,见告我,他们把你怎么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容貌?“
他吃力地讲话,可是动不了口,
妈妈别转头,透着心伤。
“妈啊,你难道忘了
当初认为我从军最好?
我在沙场的处境你不知道。
你在家里……只管骄傲。
“我在沙场上想,老天,我在干什么?
我在杀人,或者为杀人而捐躯。
仇敌走近的时候我最心慌,
由于他的脸跟我一样。”
啊!
老天!
跟我一样!
“在火光和硝烟里,我禁不住想
我只是傀儡戏里的小兵。
提线终于在炮声和烟雾里断掉,
一颗炮弹便轰掉我的眼睛。”
他转身离开,妈妈仍旧惊魂未定,
他靠金属架撑持站稳。
转身的时候,他唤妈妈走近,
一把勋章落进她的手心。
答案飘在风里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真正配称为人?
鸽子要飞过多少海洋
才找到沙滩打盹?
大炮要轰多少次,
才可以永久封禁?
那答案,朋友啊,飘在风里,
答案飘在风里。
人要抬多少次头
才看得见浩浩穹苍?
人须要多少耳朵
才听得见世上的哭声?
人要见过多少尸体
才发觉太多去世亡?
在冲进大海之前
山能有多少春秋?
在得到自由之前
人能够存活多久?
为假装一无所见
人能够转多少次头?
一场凶暴的雨快要来了
啊,你到哪儿去了,我蓝眼睛的儿?
啊,你到哪儿去了,我的小宝贝儿?
我在十二座多雾的山边跌倒了,
我走过、爬过了六条弯曲的公路,
我踏进了七个悲哀的树林中间,
我经由十二个去世海的边沿,
我闯进了坟场口一万里,
而一场凶暴,一场凶暴,一场凶暴,一场凶暴,
一场凶暴的雨快要来了。
啊,你看到什么了,我蓝眼睛的儿?
啊,你看到什么了,我的小宝贝儿?
我看到新生的婴孩被野狼围住,
我看到一条空荡无人的宝石路,
我看到玄色的树枝不断流血,
我看到房间里许多人拿着染血的铁锤,
我看到白色的梯子浸在水里,
我看到一万个人用破碎的舌头讲话,
我看到孩子们手里握着枪和利刀,
啊,你听到什么了,我蓝眼睛的儿?
啊,你听到什么了,我的小宝贝儿?
我听到雷声隆隆发出警告,
听到足够溺死全体天下的波涛呼啸,
听到一百个鼓手用燃烧的手擂鼓,
听到一千个人低声讲话而没人理会,
听到一个人喊饿,听到许多人发笑,
听到一个墨客唱着歌去世在沟渠里,
听到陋巷里一个小丑伤心哭泣,
啊,你碰上谁了,我蓝眼睛的儿?
啊,你碰上谁了,我的小宝贝儿?
我碰上一个小孩站在去世去的小马阁下,
我碰上一个白人溜一只玄色的狗,
我碰上一个年轻的妇人全身着火,
我碰上一个少女送给我一道彩虹,
我碰上一个男子被爱情所伤,
我碰上另一个男子被痛恨所伤,
啊,你准备干什么呢,我蓝眼睛的儿?
啊,你准备干什么呢,我的小宝贝儿?
我要不才雨之前再出门,
我要走进最黑的森林,
去许多人空动手的地方,
去毒子弹滚进水源的地方,
去家屋毗邻湿润肮脏监狱的地方,
去刽子手永久蒙着面的地方,
去充满丑恶的饥馑,去灵魂被遗忘的地方,
去颜色漆黑,去空空如也的地方,
我要讲出它,思考它,评论辩论它,呼吸它,
要从山上反响它,让统统人看得见,
然后站进海水里,直至开始下沉,
可是我开始唱之前会熟习我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