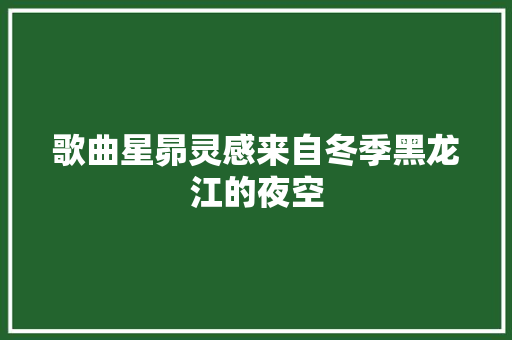果真清承明制?
一些清史学者及其拥趸,在论述清朝制度时常会言及“清承明制”的论调。这些“不辨黍麦”的二流学者们,真的是清朝统治者的好帮手。
清朝统治者为了强调自身的政权合法性,才会不断地言及“清承明制”的虚假事实,就像“匡复明室”那样荒诞不经,然而便是有很多人对此笃信不疑,对此笔者也无可奈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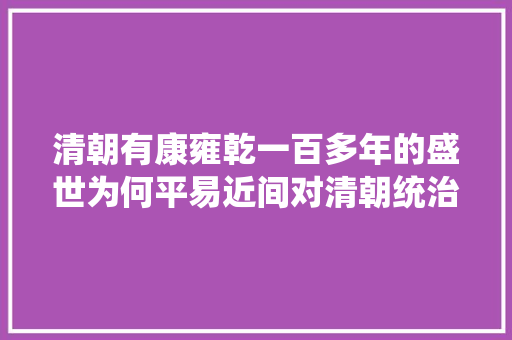
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循名以责实,便可创造,清沿明制,名同实异。
如晚明期间内阁权侔君主,而清朝也确确实实的继续了明朝的内阁制。然而此内阁非彼内阁。清顺治帝期间权力的最高机构,则属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期间则是政出南书房,到了雍正期间则另设军机处,用机要秘书的形式代替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至乾隆初期则已形成定制。这一制度一贯到宣统帝逊位的一百七十多年间,一贯是作为满洲中心集权制度的核心的。
而军机大臣无非属于君主或者僭主的奴才总管,而汉人中除了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曹振镛诸人之外,很少有能预闻军机的。就连延清廷六十余年寿命的汉臣之曾国藩,生仅得协办大学士之虚衔,李鸿章位列首辅二十余载,至去世仍无军机大臣的头衔。
许身为国,如此二公者,尚不能预闻军机,遑论其他汉臣了。
满汉之大防,直至清亡仍见其效应,可叹清主苦心经营继承三百年的祖宗大法,竟成了清亡的助推器。
慈禧曾有言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比较于民间百姓去世活,满洲集团更在乎的是世袭特权的万世无疆。可曾想过,把和颜悦色推向了去世亡的深渊,你满洲特权将如何存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然而固执迂腐的权贵们,早已被肉糜堕落了头脑,这些知识对付他们而言便是不敷以闻的。由于“本朝以武定天下”的迂腐思维,依然霸占了决策层的大脑,不顾时局变革,焉有不亡之理呢。
满尚书与汉尚书在这个帝国里,满清的权力构造屡有变革,有两点却是始终不能与时俱进。其一,是政府组织的满汉双规制。其二,是军事组织的八旗驻防制度。
就像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明沿宋制一样,在部分历史学家眼里清也一定是承明制的。这样看似很有根据的论断,实在也逃不过一个臆断想当然。
的确从清廷官职划分而言,明朝的内阁六部制,在清朝得到了延续。但是我们拿着放大镜细细研究其详略的话,就会创造事实并非如此。清廷六部制度,我们以礼部为例,则会创造清朝在官职设置上,有一官两职的征象。
即,礼部尚书,设满尚书一人,汉尚书一人,旁边侍郎的话也是满汉均占一位。这样打算来,一个礼部其紧张领导便有六位之多,而且一个大原则便是同级官员中满人均为汉人上司。
这便是,以满驭汉的原则。
于此,也可一窥清廷冗员之多。
满洲官员的产生办法,但问血统或战功,不问识文断字与否。而汉员的产生办法,照例是由科甲出身。且不说某些部门如内务府、理藩院等,不容汉人问鼎外,即如内阁六部九卿,阁首与司员,也是血浓于水,功阀大于才学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征象,帝国的各大省区的巡抚,总督以及六部阁首,竟然永劫代的涌现了白丁在位,能臣作辅的征象。
通过上述征象的剖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鸦片战役期间与英军打仗,满洲大员要用女人的月经布、人畜粪便、狗血、鸡血等装神弄鬼的办法去对抗英军的威力无比的大炮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幅员辽阔的大清,却只能任蕞尔小邦宰割的屈辱过去了。
满员奴才监督汉员,蠢才制约能臣的古怪征象,彷佛封建往后便偃旗息鼓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诲的汉人们,对付满汉双规制,当然已经看出个中毛病了。清朝的这种内满外汉的统治方针和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汉臣们本着为君父分忧的生理,切言时弊,指陈内满外汉的陋习,认为任命内外大臣该当摒除满汉成见,然而这种敢于触及内满外汉的人事传统,除了招致满洲大君的无情弹压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广开言路,是每一个继位之君,必定上演的重头大戏。
所谓新君继位,咸与维新是也。
满汉混血的嘉庆继位之后,快刀斩乱麻似的清理了朝中的和珅集团,接着又下了一个求言诏书,只可惜嘉庆大君并没有明帝那般的大襟怀,上书言事的奏折,纷至沓来。然而生性敏感的嘉庆大君却借此治了不少敢言直谏大臣的罪。下诏求言的是你天子,结果因言入罪的又是你天子。事后,嘉庆大君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自己求言纳谏之心不变,尔等臣工要体察君父的良苦存心。
事实上有了前车之鉴,敢言直谏的大臣少了太半,而歌功颂德,虚与委蛇,欺上瞒下的投契者倒是多了起来。以是有清一代,没有言官。
历史又何其残酷,而又何其相似。
嘉庆的继统之君道光帝亦与乃父乃公一样,叮嘱消磨对付英夷的文武钦差大臣,一贯就用的是满洲权贵。如“主抚”的用琦善,“主剿”用奕山等。以是直到曾国藩启用之前,满洲大君对付弹压叛乱一贯仰仗的是满洲军事集团里的权贵子弟。
毕竟汉人終属外人,其心叵测。
在官修史学中,满汉之别已然不见其踪迹,代之而起的则是满汉领悟的政治精确。但是如果以政治精确的不雅观点来研究那段离你我不远的史实,总会有龊龌难符之处,而若依以满驭汉,满汉之大防来看待史实问题的话,是不是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觉得呢。
在满洲大君的眼里,大陆只是他征服的地区之一,作为征服者他要时候保持征服者的特权以及社会优胜性。满洲大君除了是汉人的天子之外,他还是蒙古人的大汗,藏人的活佛。
这些浩瀚的身份认证下,其所包涵的社会代价以及历史信息是丰富多彩的。
满洲大君首先是要担保皇族,宗室的地位身份,其次才是满洲集团的社会特权,再次则是国家,末了才是附属国。这便是满洲大君们世代相袭的天下不雅观,这种天下不雅观和儒家的家国天下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家国天下的一圈圈的外延性的同心圆。
唯一的差异在于,汉人并不是他们紧张关心的,满洲军事同盟集团,才是国之根本。
下面完备引用一下朱维铮师长西席的一段话:
就史论史,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制度,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论著把稳,是很奇怪的。起因或因忌讳民族问题。然而清末孙中山,章太炎等鼓吹“排满革命”,与后来的大汉族主义乃至中原中央的反历史论调有可比性吗。
然而“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子虚乌有的圣心垂爱,在民众的心里却是始终乐意相信圣断如炬的。除了越无知越无畏的蠢货,稍愿知中国知识的读者,至少会花点韶光读一读《东华录》。如果连如此大略的编年史记都没有耐心读完,那么彼辈无论在网外网上论史,只可视作胡言乱语,似无疑义。
如前文所述,满汉之大防这一政治策略始终贯穿于清廷三百年的统治的。一如国师恩格斯所言,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他既然已成为专制主义者的中心集权系统编制的有效形态,便不可能随着满清的垮台而很快闭幕。
它会借尸还魂吗。这是一个差异于传统史学而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满清治下的国中之国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始终要给自己留一个退步。不容汉人问鼎的化外之地。只管满洲第五大君嘉庆帝是满汉混血,这并不妨碍他们政策的制订,并遵守之。如他们将关外之地的东三省,视为龙兴之地。清廷绝不容许汉人出关谋生,直到光绪末年山东菏泽境内黄河决堤,不得已山东人才大规模的迁徙关外龙兴之地。除了天灾之迫不得已,实在最紧张的还是王朝末期,官防松弛。若是在康雍乾之壮大期,恐怕“闯关东”,就连“下江南”都会禁止的。
毕竟流民即是流寇,这一不安定成分,维稳是大于民众去世活的。
还有便是本日的宁夏自治区等与蒙古接境的地方,同样不容许汉人在此拓荒,多添一户人家。其目的便是要把汉人和蒙古人隔绝来,不许二者相互打仗。同样也是到了光绪末年才得以解禁。
再如今日的新疆地区,也被满洲大君们视为禁脔,不容汉人置喙的,他们要把此一天然牧场作为满洲人的衣食之地的,不容许汉人往那里去。直到了左宗棠平定回民叛乱之后,禁令始驰,汉人才能到新疆去。由于满洲的私心自用,才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了些许禁地,不容汉人及其他民族前往。故而在欧美日诸国涌现了所谓的“本部十八省或者要地本地十八省”的荒诞说法。然而就传统历史而言,并非如此。
在满洲人眼里,蒙古为其亲族,故蒙古贵族多有封亲王、贝勒、贝子等显爵的,而汉人至多得爵于侯爵即止,纵不雅观满清三百年历史除了曾国藩封侯之外,又有几许人得封。
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汉人居于第三,满洲虽未堂堂皇皇的实施四等人制,但是如此的区分,其实学到了元朝君主的统治精髓。
故而借用钱穆师长西席的一句话可以明言:清代文化制度,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本日之再称道的。
参考资料
1、朱维铮《重读近代史》《走出中世纪》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落》
3、美 欧力德《乾隆帝》
4、社科研社《不客气地说,许多人喜好的不是历史而是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