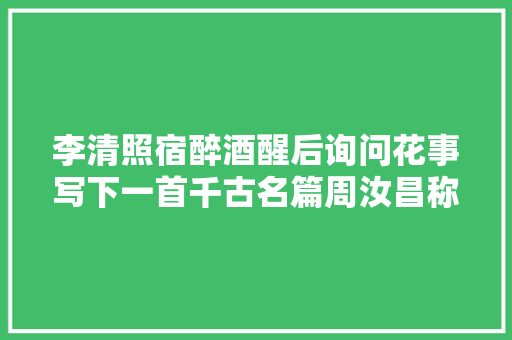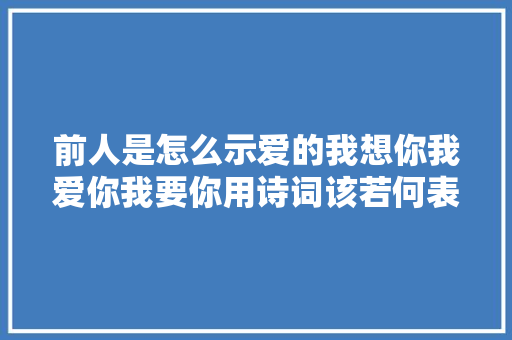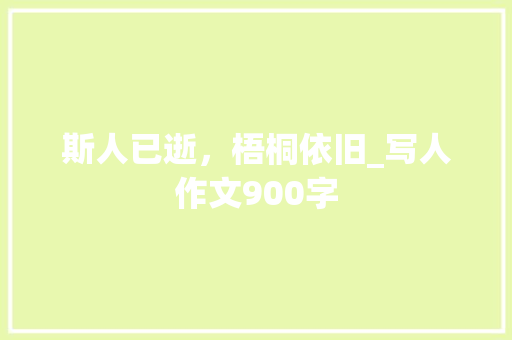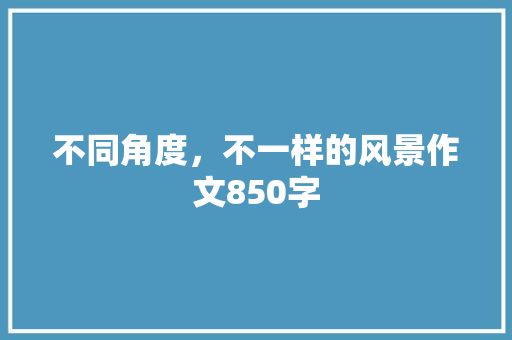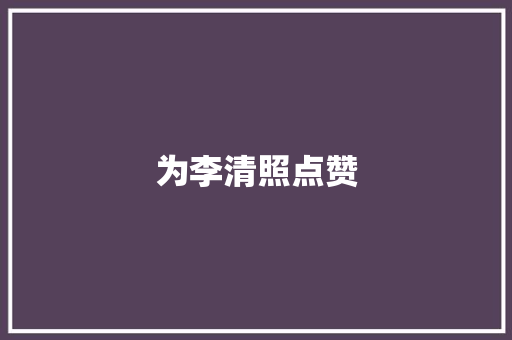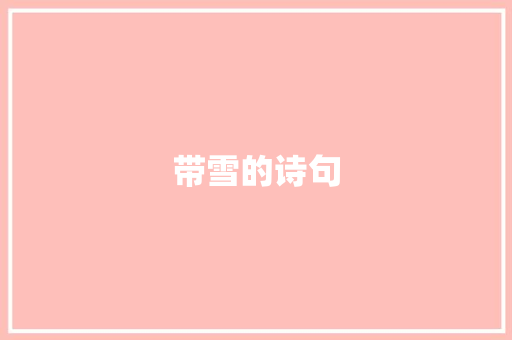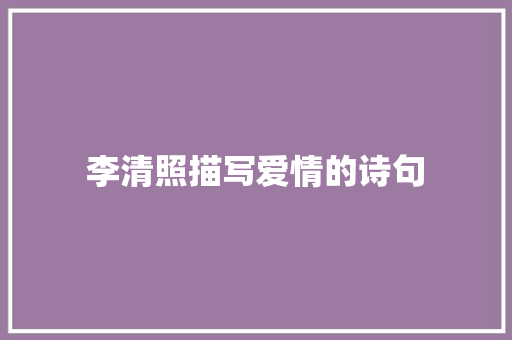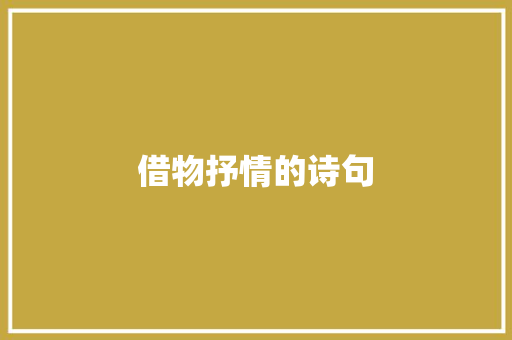本期话题
李清照的《如梦令》是一首非常幽美的小词,可是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它究竟好在哪里。在央视的“经典咏流传”上,歌手蔡琴改编了李清照的这首小词,她用什么办法将这首词改成幽美的盛行歌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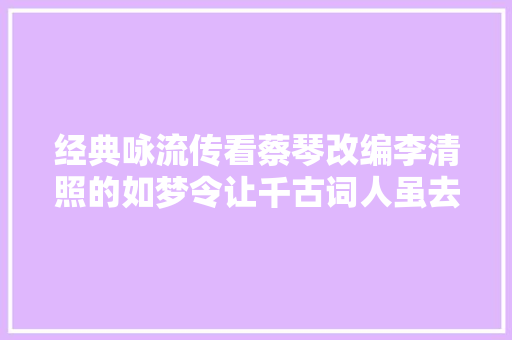
这是电影《七小福》中最让我感慨的画面:七个京剧班出身的少年辞别了师傅余占元,坐上这艘小船,漂流于茫茫大海、滚滚波涛之间。那西沉的斜阳余晖将尽,就像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京剧在披头士和时尚交际舞等当代盛行文化的冲击下日渐衰落,只能蜷缩到白发老人的影象中去一样。
七个少年在临别时对余师傅说:
“我们已经决定去拍戏了。”
“拍戏?拍戏有出息吗?”
当师傅下意识地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少年们想到出路,仍是烟水迷茫,只得答道:
“反正都一样,试试嘛。”
而终极的结果,众人都知道,他们成功了。洪金宝、成龙、元彪……,七小福的奋斗足迹险些填满了一代喷鼻香港娱乐文化的历史,他们年夜胆地放弃了一个出身于农耕文明时期的京剧艺术,转而投入当代工业文明下新兴的电影家当,创造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奇迹。可在他们的成功背后,京剧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实在跟七小福幼年学艺的京剧一样,也是属于某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影象。当属于这个时期的页码被翻了过去,文化的辉煌也将注定春水东流,一去不回。
作为一个长年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我很钦佩乃至感谢像“经典咏流传”这样的文化节目的良苦存心,但实话实说,看过了节目中演绎的许多作品,它们都遗憾地没能给我留下多少印象。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古典诗词的节奏、韵律不一定能够和当代盛行音乐的形式完美合营,削足适履的觉得总在不经意间就跳了出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期和文化的隔膜让我们无法走进古人的生活,以是当我们拿起发话器唱出那些诗句的时候,我们更像是隔着一层去唱别人家的故事,难有感同身受的共鸣体验。
看节目的这种遗憾和失落望时常困扰着我,让我感到悲观:可能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唤醒属于唐诗宋词的辉煌影象了。乃至我们终极可能不得不像七小福对京剧那样,与它相忘于江湖。但是,当蔡琴蔡姨妈登上“经典咏流传”的舞台,唱起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我才创造,原来枯杨生稊、老树新芽的奇迹是可能的。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蔡姨妈说,“李清照的词用字都很白,很大略,但她能写出很博识的境界来”。我不太乐意用“博识”来形容这首词的境界,由于它不像《楚辞·离骚》那样洋洋千言,意象密丽,构造繁复,给你一种不明觉厉的高等感。
《如梦令》的高等感是其余的一种类型。它不是摆在台面上的,而是隐形的。就这么简大略单的40个字,明白如话。可如果你要站在讲台上以这首词为话题坚持讲它10分钟,我相信许多人都会犯难,哪有那么多话可说?这实在便是李清照的高等感——你知道她写得好,但你说不出她究竟哪里好。
德京剧作家莱辛曾经写过一本名叫《拉奥孔》的书。书中写道:
艺术家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中只能捉住某一顷刻。尤其是画家,他只能从某一不雅观点利用这一顷刻。他的作品却不是过眼烟云,一纵即逝,须耐人长久反复玩味。
——《拉奥孔》
莱辛说,比如一个画家吧,他和不雅观众沟通的媒介是静态的图画。如果画家想讲一个完全的故事,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可能须要许多帧胶片的合营才能讲述完全。可是画家在讲故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胶片”,他必须从这无数连贯的“胶片”中挑选唯一的一帧。这帧图一旦展现在不雅观众面前,便能供不雅观众从此遐想开去,补足故事的情节。为了达到这个效果,画家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手里的那一帧图只能表现故事达到高潮前的那一刻。像古希腊雕塑拉奥孔便是利用这种创作理论的典范。
拉奥孔,这个古希腊传说中的人物由于向特洛伊城的同胞透露了希腊人在木马中暗藏伏兵的秘密而被希腊保护神阿西娜派出的巨蛇缠绕、绞去世。雕塑家阿格桑德罗斯将雕塑的形象定格在巨蛇刚刚爬上拉奥孔和他两个儿子的身子,三人因此发出呻吟微叹的时候。
这样一来,目睹这尊雕塑的不雅观众会进而遐想到巨蛇缠绕上了他们的脖子,令他们发生发火声嘶力竭的惨叫,并在这个想象中随着人物命运的起伏而臻于感情最紧张的高潮。也便是说这尊雕塑让所有看过它的人都更愉快了起来。
可反过来,假设阿格桑德罗斯的雕塑表现的是巨蛇缠上了拉奥孔的脖子,惨叫已经响起,那么不雅观众随之而来的遐想就只能指向人物的倒毙、僵硬,这将让他们的感情随着剧情的落幕而下滑到谷底。感情在看完这尊雕塑之后随即下行,以至熄灭,不雅观众会认为这样的体验枯燥乏味。
像《如梦令》这类篇幅短匆匆的小令,当词人用它讲故事的时候和画家作画面临的困境实在是类似的:词人能利用的画面数量极其有限,而李清照的第一帧画面彷佛就选错了。由于她说:“兴尽晚回舟”——《难忘今宵》都响起来了,再往下还让读者看什么呢?
但我们不要忘却,这是一首大师的经典。大师的手笔便是这样的出人意料,当我们误以为统统都已结束的时候,精彩才刚刚开始。女孩子将回家的船误划进了芙蕖丛生的河湾,她迷路了。
“争渡”,吴小如师长西席在《诗词札丛》中阐明说,那便是“怎渡”。该怎么渡出去呢?该怎么渡出去呢?当她一迭声发问的时候,归家的心切、迷路的发急已经令她五内焦煎。
可她没有想到,迷路的她实在是闯入了“别人的家里”。已经在夕阳下歇息了的鸥鹭被这个卤莽的姑娘吓坏了,嘎嘎叫着,腾身飞了起来。当姑娘看到鸥鹭飞远的时候,她是什么表情?她可能被自己无意间当了这一回不速之客的遭遇逗乐了,于是忘掉紧张,笑出了声来。
我们的遐想一旦随着笔墨的指引抵达了笑声,感情就会随之达到高潮:这样随兴而至、自由清闲的生活该是多么的美好!
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被早起的闹钟、出门时的斑马线和红绿灯、事情间里的小隔板和员工守则约束得去世去世的。每一条规矩都像一把枷锁,把我们固定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逼仄的位置上,难道你不神往像《如梦令》里说的那样,让自由带你去追寻生活的奇遇吗?
在讲台上站了这么多年,常常有学生问我,老师,学文学有什么用?我总是对他们说,它能让你在身体被桎梏的时候,至少保留精神和想象的自由。别见告我说这样的自由“没有用”。如果这没用的话,那二十几个男人在草地上抢一个破皮胆子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心甘情愿为梅西的亿万年薪买单?
话题再说回到这首《如梦令》。在大多数人的共识里,这首小词是李清照结婚前后,旅居汴京,回顾故乡生活的作品。一个年轻的女子提及少女时期的快乐生活该是一种什么口吻?它让我想起了1985年齐豫在滚石唱片公司推出的一张名叫《反应·三毛作品第15号》的专辑,个中收录的一首歌——《七点钟》。
作家三毛的填词讲述的是她的初恋:一个慌里慌张的少女,一个初恋的约定,一次两个人的旅行:
是我是我是我
是我是我是我
七点钟 你说七点钟
好好好 我一定早点到
啊 明明站在你的面前
还是害怕这是 一场梦
是真是幻是梦
是真是幻是梦
车厢里面对面坐着
你的眼底 一个错愕少女的倒影
火车一贯往前去啊 我不愿意下车
不管它要带我到什么地方
我的车站 在你身旁……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大学时期。唱片里28岁的齐豫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那种青春飞扬的唱腔,惊喜和激动的口吻让我在许多个喧华的夜晚成功地抵御了室友们无聊的闲谈和闹哄哄的游戏声,带着对校园爱情的憧憬恬然入睡。
2003年的冬天,我在成都小天竺街的盗版碟商店里花了一块钱买了一张齐豫的唱片——那是一年前齐豫在喷鼻香港红馆举行自己从艺以来的首个个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45岁的齐豫在红馆又一次唱起了这首《七点钟》。只是曾经那种令人悸动的天真烂漫的唱腔失落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舒缓而温顺的倾诉。
如果说曾经的齐豫唱出的是一个20岁的少女对生活的憧憬,那么走近知定命的年纪,经历过岁月磨洗、坎坷淬炼的她,面对生活,自然会多一份从容和淡然。只可惜,年轻的我听不懂齐豫这种心境和创作风格上的转变,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齐姐姐的嗓音退化了。
如果没有当年那个小小的教训,本日听到蔡姨妈唱起李清照的《如梦令》,我或许还会将同样的怪罪错加在蔡姨妈的身上——这首蔡琴版的《如梦令》节奏太过舒缓,词中的少女已经在惊叫“争(怎)渡,争(怎)渡”,蔡姨妈的唱腔仍是一片娓娓而谈的意思。
去年的8月3号,我坐在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央听蔡姨妈的“好新琴”演唱会,当蔡姨妈唱起那首邓丽君的名曲《如果我是真的》:
如果流水能转头
请你带我走
如果流水能接管
不再烦忧……
我险些哭了出来。网上有同好说,在其他城市的巡演中,蔡姨妈唱完这首歌曾经失落声落泪。或许是歌词触动了她内心深埋的情伤。但是那一天,当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蔡姨妈却没有哭。她像一个温暖而和蔼的父老娓娓地讲了一个沉淀在回顾里的悲哀的故事。
蔡姨妈曾经说,经历便是艺人的财富。歌声唱出的是生活的酸甜苦辣,能少得了哪一种?如果说那首《如果我是真的》唱出的是蔡姨妈的悲怀,那么这首《如梦令》唱出的便是她的快乐,只不过这是一种人到老境、看淡风云的恬然之乐。
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把稳到屏幕上的歌词涌现了一个俏丽的“误会”。李清照原词的第一句,据唐圭璋师长西席《百家唐宋词新话》说,当作“尝记溪亭日暮”。“尝”也便是有时的一次回顾。但蔡姨妈的歌词写作了“常”——一遍又一遍,常常地回顾。
这不禁让我产生了错觉,仿佛这首《如梦令》不是易安居士青年时期的手笔,倒更像是老年之后追忆前尘时所作。假如这样,它难道不应该像45岁的齐豫再唱起《七点钟》那样云淡风轻,滤去生活的苦涩,只留下回顾的温暖吗?
李清照给了《如梦令》一帧画面,而蔡姨妈也给了李清照一帧画面。画面里的李清照从青春年少走向桑榆晚景,一千年前的词人彷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她就活在那个舞台上……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
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欢迎分享转发,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 THE END —
笔墨|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