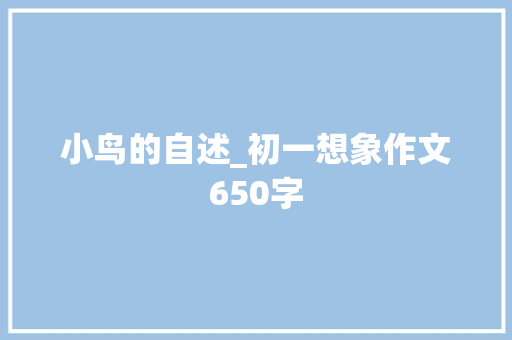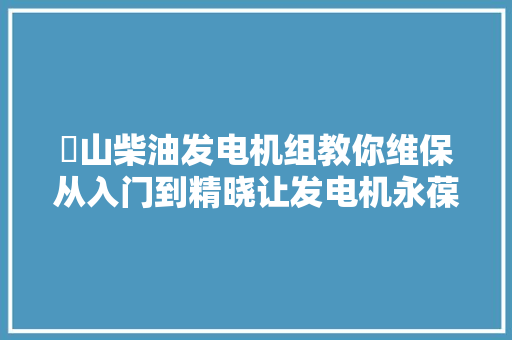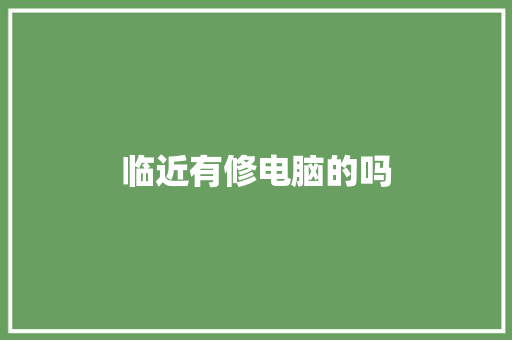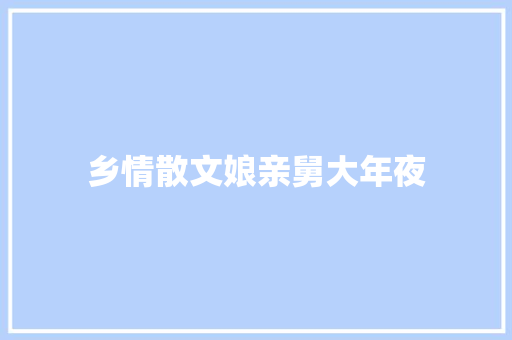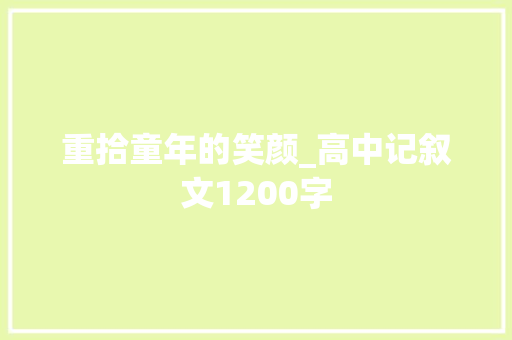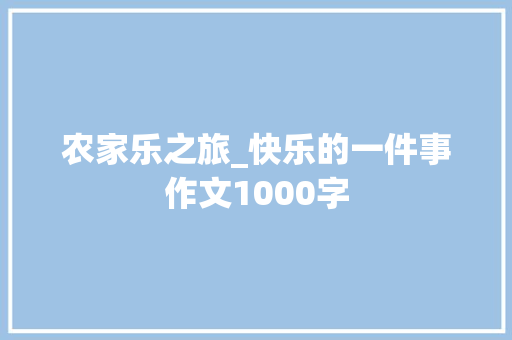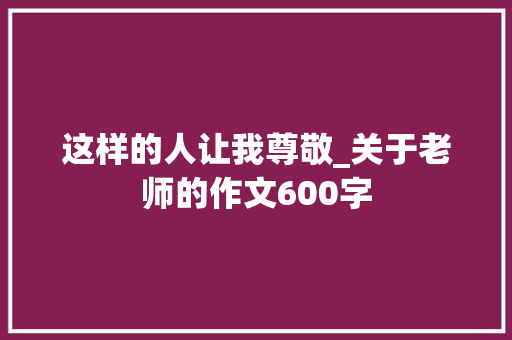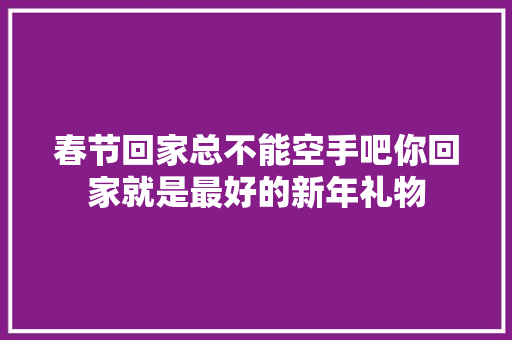本日的推送中,郭玉洁将讲述她与这个书系有关的故事。这是一份超过十年的影象,同时也是对读者的一份回答——《单读》从何而来。这篇文章同时收录于《单读十周年特辑(下册)· 在世界的门外》。
《单读十周年特辑(高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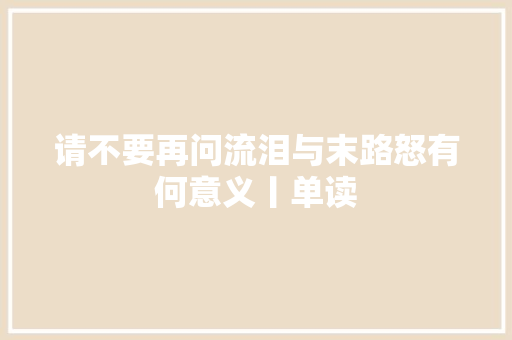
吴琦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19-12
《单向街》和我的“真情政治”
撰文:郭玉洁
梁实秋写徐志摩时,有一段话:“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团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现,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札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畅不置。”他说:“我数十年来奔忙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畅。”
读到这段笔墨,我有点惊异,一个以过度的浪漫气息和对俏丽女性的迷恋留在历史上的墨客,像夹在电视屏幕里一样的人物,谁能想到居然这么热闹有生气、敏于交际?再想想,当然如此,当代史上才子何其多也,如果不是这种性情魅力,林徽因和陆小曼怎么会喜好上他?
我急速想到了许知远。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这样, 每每成为座中焦点,诙谐、年夜方,能讲段子,也长于自嘲。他反应奇快,把稳力常常转移,因此很难进行持续深入的交谈,但也因此,绝对不会记仇——他早就忘了。
有这样令人倾慕的性情,许知远便不但是作家、媒体人,他善于联合各种人和资源,一起干事。“单向街”的成立、壮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合纵连横的激情亲切与能力。
我们认识,是在 2005 年一起创办《生活月刊》时。同一年冬天,单向街图书馆在圆明园开业。紧张发起人许知远、于威,也正是《生活月刊》的卖力人。书店间隔市区太远,刚开始还生僻,我们一样平常打车去,到圆明园东门下车,从戴红帽子的旅游团中穿过,右拐进一个角落,经由一排屋子——听说以前是陈兵的营房,后来成了各种艺术事情室,最里面那个大院子,便是“单向街”。院子里一地碎石,深一脚浅一脚,四处散落的桌子,是用镜子做的面,反照着白惨惨的天空和几棵枯枝,显得景象格外冷。推开门,屋里是狭长的一条,像街道一样,一边是满墙书架,另一边是空空的白色宜家沙发,我们便是当天仅有的顾客了。等春天一来,统统变了。一桌一桌蓝色的天空,绿色透明的叶子,院子里满是人,半躺在帆布椅子上,大树下两三个人手拿麦克风,谈最近出版的书,谈长久以来的思想变迁。在当时的北京,“单向街”首创出了一片公共文化空间,年轻、开放,充满活力。我和书店并没有物质上的从属关系,但是精神上非常投入,没事就往圆明园跑,有幸亲自参与了这一空间的成长,却全然不用担忧书店的盈亏问题——基本上是亏的。
单向街书店圆明园店(单向空间前身),正在进行的一次沙龙活动。
2009 年,我离开《生活月刊》,彷佛想写点东西,又彷佛只是在游荡和谈恋爱而已。一次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和知远用饭,他邀我一起做一本 MOOK(杂志书)。我很犹豫,由于实在厌倦了编辑这份吃力不谄媚的事情。知远却永久那么兴致勃勃,他说,你不是总嫌《生活月刊》都是图片不重视笔墨吗?咱们做一本都是笔墨的!
这句话说服了我。的确,我常常抱怨,媒体上图像泛滥,刺激也迎合感官,却削平了读者的思考和感想熏染能力,让人们变得
虽然是书,却每辑都要有主题,要针对当下,有批驳性。这是我们都认同的。那第一辑做什么?知远拿出了互联网不雅观察家尼古拉斯·卡尔的文章《谷歌把我们变蠢?》,当时,关于互联网,乐不雅观主义是主流,卡尔却提出,信息的碎片化,使得人们失落去了深入思考的能力。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知远写了卷首语,同时,我们约采访了一些网络时期的弄潮儿,封面题为《最屈曲的一代?》。互联网时期中终年夜的一代,真的是万众期盼的“新人”呢,还是屈曲的一代?当时很多人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说道,走着瞧吧。瞧到了本日,我真希望他们是对的。
《单向街 001:最屈曲的一代》
许知远 主编
凤凰出版社
2009-8
《单向街》的版式很大略,参考英国老牌文学杂志《格兰塔》,一张图,一行字。栏目分类也很大略,专题、宣布、随笔、访谈,唯一分外的是“沙龙”,取自单向街书店举办的演讲。第一期“沙龙”,是戴锦华老师讲墨西哥游击队领袖——蒙面骑士马科斯。
第一辑出版之后,有来采访。当时市情上涌现了好几本 MOOK 形态的书,有《读库》《鲤》,还有即将出版的《合唱团》(《独唱团》)。问,和其他竞品比较,你以为《单向街》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总不能说笔墨很主要吧,毕竟,笔墨是全人类的发明。情急之下,开始思考《单向街》的定位。个中最主要的维度,自然是主创者的气质,《读库》主编老六是六零后,《鲤》的主创是八零后,而《单向街》的几位主要参与者都是七零后。在我看来,六零后生于新中国,怀抱20世纪80年代,就像最早学会的一首歌,此后所有的曲调都从此变换而来;八零后,已经全面拥抱了商业时期;而七零后在这两种代价不雅观之间,无可拥抱,茫然四顾。我说,我们是不彻底的、疑惑的一代,这疑惑,并不是北岛所说的:“我——不——相——信!
”那种疑惑,带感叹号的疑惑背后有武断的相信,我们的疑惑是面对统统话语轻声地说:“真的吗?”是半信半疑,还不能决定自己该当相信什么。
现在想起来,这种表述并不准确。七零后的很多人, 一点儿都不疑惑,他们迅速投入了刚刚卷起的互联网浪潮,并且创造了本日令人线人一新的天下,腾讯、网易、搜狐、京东……本日这个消费主义、“霸占性个人主义”的天下,正是我们这代人绝不犹豫地建立起来的。疑惑的、茫然的,只是少数人而已。但我乐意站在这疑惑、茫然的人群之中,在时期的变迁中,决心创造自己的、另类的答案。
答案从何而来?从我们生活的现实之中,从无数人的心灵中来。在各种文体里,我最看重长篇宣布,只管以文学的名义,宣布常常被轻视,很多人认为它低于小说,低于这低于那。我却以为这是轻浮势利的意见,宣布有着坚硬的质地,敲击社会构造,打破生活的次元壁,努力描摹陌生人,它的意义,远胜于大部分小说。
可惜,宣布太昂贵了,出版很难支撑。虽然我们坚持从版税中拿出最大一笔,给当辑的原创宣布,但仍旧无法覆盖为此付出的韶光和精力。幸好,那还是没有微信"大众号的时期,很多媒体的宣布,都还不为人所知,包括我们自己的文章在内。这些文章,成为前几辑《单向街》的大部分内容。
第二辑的专题,是我和几位同事在《生活月刊》时所做的一组人物宣布: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陆续涌现的四位先锋话剧导演。封面题为《先锋已去世?》,大概意思是,这些导演或是在商业中失落去了先锋性,或是已逐渐边缘化, “写下这个耸动的标题,是希望呼唤每一代人当中不甘平凡者内心的冒险精神,来为这个天下添加新的可能,而非加固其庸常之处。”
开第三辑的选题会时,我说,想做一组和性/别有关的文章。“性/别”一词来自台湾学者何春蕤,既指性别,也包含与性干系的各种议题。当时,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性/别干系的活动,但是这些话题始终居于台面之下,主流媒体不屑一顾,很少有负责的宣布和谈论。我说,这些话题很主要,也很前沿。知远听了,面露难色,犹豫了少焉说,我以为这个不好。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个……不主要。
我愣住了,有一下子没有说话。脑筋里闪现的都是曾在历史上读到的句子: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同盟会忽略女性革命者的付出,删除了政纲中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一怒之下,冲进会场打了宋教仁两个耳光;20 世纪 80 年代的女作家痛楚地创造,男性只是想把女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无数女性被同一阵营的男性战友背叛,由于女性的问题,不主要。
我说,属于一半人类的问题,你以为不主要?迫切间,有点哽咽,大概还流了泪。
知远彷佛被吓到了,他默默地,没有再说话。
在回家的路上,我接到知远的电话,他说,我想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他又说,实在我们是一样的。我说过,他一贯是一个善良、年夜方的朋友。
过了多少年,在一次有关性/别的公开活动上,我讲到了和知远的那次对话。它对我影响至深,它让我明白,男性知识分子对付女性问题的忽略,不仅来自长久的履历,而且有知识、话语的装扮,非常强大。更进一步,不但是男女之间,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都有不合和差异,如何对待这些不合和差异,才是磨练我们的时候。
一位男性不雅观众举手,他问,你刚才说,许知远他不同意你那个选题,你还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呢?
我感想熏染到他的歧视,一丝愤怒往上升。没有压抑这丝愤怒,我说,我在详细的生活中,为自己的理念抗争了,而且我成功了,我做了自己想做的题目,你呢?如果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不同意你,你会去抗争吗?现场一片沉默。
我常常堕泪,也常常愤怒,我器重这些动情的少焉, 那不仅是私人情绪而已,更联系着我们的空想,我们关怀的人和天下。我称之为“真情政治”,这种“真情政治”使我们免于变成犬儒、冷漠、自私的人,使我们的公共生活鲜活、富于人性,也使我们拥有真正的爱和友情。
郭玉洁,媒体人,专栏作家,前《单向街》(《单读》前身)主编。
2010 年 12 月,第三辑《繁芜·性》出版,封面是一个类似阴核的图案,专题文章有苏丝黄的《性之重量》,李银河的《后村落女人的性》,马家辉的《自拍有理,春照无罪》,林奕华、田沁鑫的对谈《都邑里的情与欲》,关锦鹏的访谈《拍女人戏的男同道》,也有何春蕤的访谈《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再翻看目录,我真希望自己是更成熟的编辑,但是当时,只能做到如此了。
第四辑《他乡》交付印刷之后,我负责地以为,自己不是很好的编辑,难以坚持一本书的长期出版。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情由,我离开了北京,去台湾读书。我在《单向街》的事情告一段落。
2014 年,再回来的时候,《单向街》变成了《单读》, 重新启动,更好的编辑,更好的设计,更有规律的出版周期。我加入了“中午”,又出版了同名的杂志书,在序言里,我写下一段:“天下仍旧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本日中国最紧张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万万千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该当学习讲故事。长久地瞩目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授予普通人肃静,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这段想法,是从当年的《单向街》延伸而来的。貌似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是我想,我和本日的《单读》仍在同一篇文章之内。
图片来自网络
2020 年,《单读》探求订阅读者,探求会员,探求名誉出版人,进行中!
《单读 23 · 破碎之家》已经上市
它又意外地应景了